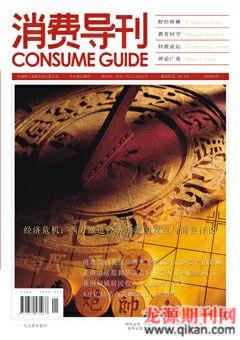中国社会中法律的作用之思考
[摘 要]法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本文拟通过对古代社会中主要的法律观念,统治阶级对法律的态度,古代社会的性质等不同角度的分析,说明古代中国社会中法律的作用的非主导性,从而指出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既要尊重、利用传统,又要突破传统。
[关键词]法律的作用 礼治 多元混合秩序
作者简介:高丽霞,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主要研究方向:法学理论,民法学。
一 、引言
春节期间,某市为保证春运的安全,做出规定:客运车一律不许超载,超载一人,罚款五十元。为此,还在主要公路段设立关卡。但该市客多车少,客运司机更是见利而妄为,把整个车厢塞得水泄不通。为应对检查,避免被罚,客运司机往往几度要求乘客上下车,分批运过关卡,劳民伤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司机和乘客们在关卡的不远处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执法人员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好像超载的危险只在过关卡的那一瞬间存在。事实上看来,对司机而言也确实是在那一瞬间有危险超载即被罚的危险。这不由让人想起“秋菊的困惑”和“山杠大爷的悲剧”,这些都是法律在起作用,然而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本文将初步探讨法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困境,并粗略的谈谈如何改善法律作用的发挥。
二、法律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
法律的作用,是指法律对人的行为以及最终对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国家权力运行和国家意志实现的具体表现。为考察古代社会中法律的作用,本文拟从以下主要的法律思想观念、统治者对法律作用的期待、法律和人民、法律职业和社会性质等几个角度展开。某种制度的出现,往往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考察法律在古代社会中的起源,一般能洞察法律在当时的作用。关于法律的起源,《尚书·尧典》:“帝曰‘皋陶!蛮夷滑变,寇贼奸究。汝作士,古刑有服,五服三就”[1]。可见,法只是被看作是镇压的工具,主要表现为刑。 “命令、禁止,顺我者赏,逆我者刑,这便是三代之法的真诠”[2]。到了先秦诸子当中,法家主张法制,用法律来治理整个国家,但只在刑赏二字。“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故刑戳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3]法之作用即在赏以劝善,刑以止奸。相反,儒家却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到了汉朝,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大量渗透到法律之中,之后在中国的法律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是德主刑辅,重视礼的作用。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法律只是握在手中的一种统治术,“攻用法,守用儒,退用道”。秦王一统天下后,焚书坑儒,大量适用严刑峻法,结果官逼民反,二世而亡。因此,秦之后的汉采取修养生息的政策,重视对人民的教化。法律“只用于对付野蛮人:无视道德和社会的人、不可救药的罪犯、异族以及对中国文明有不同看法的外国人。”[4]从法律和人民的生活上来看。荀子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守之,众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5]于是有“刑不上士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这并不是说士大夫们能够为所欲为,只是即使他们有越轨行为也不用法律来调整,而是用所谓的礼,“所以士大夫以家法约束子弟,对违法者以家法惩治、扑责”。[6]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更是视公门为畏途,不愿涉讼。一般而言,在审案中,问官动辄用刑,逼取口供,饱受皮肉之苦。据说,即便是为众人称颂的明朝官员海瑞,也是惯用酷刑,公堂外常常或跪或吊数人。此外,胥吏衙役都以讼案为生财之道,一打官司就索取种种规费。例如清代,“原告需交纳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送稿纸笔费、出票费、铺堂费(即开庭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如果是命案,并有命案检验费。”[7]这样一来,许多人会因为一场官司而倾家荡产,因而许多人宁可忍气吞声而对讼事望而却步。但在古代中国,家族中的族长权威特别高,族中有族法,由族长来执行。族长可以通过族规或自己的意志来判断是非曲直,酌定处罚。“族长可以责令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罚款、加以身体刑、在饲堂打板子、开除族籍、送官究办,有时甚至下令处死。”[8]对于族外的纠纷也一般是通过邻里、里老及地方绅士来调停解决。
从古代中国的法律职来看。我们知道,罗马司法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对当时和以后社会发挥的巨大作用,很大程度得归功于当时许多著名的法学家。法律职业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个社会法律的发展和作用发挥意义巨大。但在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自汉朝以后,地方行政官兼任当地的司法官,而行政官自身又没有受过法律教育,都是通过学习四书五经后参加科举做官的。他们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判起案来当然是一套一套礼俗伦常,法律的因素少之又少。在两汉、魏以前,专习法律的人地位很高,而且做大官的不乏其人。但是随后法学衰弱,“唐、宋试士虽有明法一科,为六科之一,但不为时人所重,所重者为明经、进士两科,进士尤甚。明清以八股取士,更无人读律。”[9]学习法律的人地位很低,政治上无出路不可能做大官,因此为人所轻蔑。学习法律的人只能从事以下几种职业:书吏、刑名幕友和讼师。其中刑名幕友的出路相对好一些,但“幕之为学,读律而已”,对于法学的发展并无多大贡献,且他们只是辅佐官员办案,常常看州县官的脸色行事。讼师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律师,他们“熟悉条文,并善于舞文弄墨,巧妙的运用条文,怂恿人打官司,以不正当的手段从中取利,往往无中生有,虚构或增减罪情,颠倒黑白”[10]。
从中国的国家性质上讲。“国家不是什么公共权力,而是一族一姓施行其合法武力的恰当形式,所以国家并未取代氏族组织,而是与之融合,互渗,形成一种严密的上级控制系统,以求保持一个可能不稳定的系统的稳定”。[11]可见,中国国家形式的出现便是氏族之间相互征战,征服的结果,而不像古稀腊那样,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为维护社会秩序、人之自由而建立的公共权力。“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更形象的道出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宗法性,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皇帝便是一家之主。下面的各个家族,家庭又形成许多小的整体,家族家长拥有很大的权力。同时,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礼治社会,“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12]主要靠礼来维持社会的秩序。
法的作用分为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规范作用是指对人的行为的调整,主要表现在:指引作用,评价作用和预测作用。社会作用是指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整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它是经过法律的规范作用而产生的,主要表现在:确认一定的社会利益关系;调节社会生活中社会利益;恢复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制裁、制约;通过对社会关系、利益主体及其权利的确认,理顺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的关系和各项具体活动,从而组织一定的机构、活动和社会关系;以法律的纲领性、超前性特点为基础,引导社会关系朝预定方向发展。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德主刑辅,注重礼治的古代中过,法律的规范作用是微弱的,往往也是备而不用,离人们的实际生活很远,在社会作用方面也是狭隘的,对整个社会的组织、整合和引导作用微弱。
三、法律在现代社会中之作用的困境及对策
上文通过对法律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大致描述,得出了法律作用在当时的狭隘性和非主导性。既是在今天,如果我们认真的看看早已通过的《破产法》在经济生活中被实际履行的状况,了解一些类似于秋菊的困惑和山杠大爷的悲剧,看看广袤的乡村社会里那种“无法”却又井然有序的情形,我们对那种宏伟的法治建构论可能会有新的认识。“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有差距。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13]也许我们的立法者可以大笔一挥,制定某条法律,废除某条法律,但是根植于整个民族深处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更改过来的,它的变化是缓慢的演变过程。中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虽然近年来旧的乡土社会已慢慢走向现代社会,但是并没有“完全彻底”地蜕变出来。此时中国的社会秩序结构是一种“多元混合秩序”,“同转型和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相伴随,当代中国社的社会秩序形态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况。我将它概括‘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守法秩序等组合而成的‘多元混合秩序”[14]
在这种多元混合秩序结构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呢?我觉得我们首要的就是认识我们自身。“中国人们一般是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法律制定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时以是否合乎情理为标准。他们不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按照大家所受的教育,各方都理所当然地准备在自己的错误,疏忽或蠢事中寻找纠纷解决的原因,而不是归咎于对方的恶意或无能力;因此恢复和谐往往并不困难。”[15]这种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法律的消极作用的描述,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之中仍然可以不时地发现它的缩影。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了解我们的社会现状,我国的法律传统,充分利用本土的资源,立足于本国来立法;同时也要有一定突破,不能完全迁就于传统,毕竟传统的东西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的不断现代化,旧的许多传统将会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我们的法治建设注定要忍受着痛楚并谨慎地前进。
参考文献
[1]梁治平:《法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80页
[2]梁治平:《法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81页
[3]梁治平:《法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83页
[4][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 漆竹生译 1984年11月第一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487页
[5]《荀子·富国》
[6]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407页
[7]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408页
[8]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410页
[9]瞿同祖:《瞿同祖法律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413页
[10]瞿同祖:《瞿同祖法律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415页
[11]梁治平:《法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79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49页
[13]梁治平等著:《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14]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4页
[15]转引自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