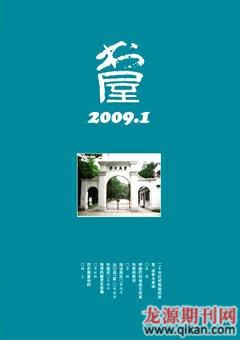韩石山歪解鲁迅一例
桑永海
几年前,在《文学自由谈》看到韩石山一篇文章,说鲁迅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一段话是“污秽的文字”。当时以为那不过是好发酷论之人又弄出点响动而已,就没当回事。却不料,几年过去,这个响动越来越大,从纸面响到大学讲堂,从内地响到沿海,韩石山谈鲁迅往往都要拿阿长这段话来说事。前不久,他在同济大学中文系演讲,又言之凿凿地说:中学语文选了《阿长与〈山海经〉》,“内里有一段话,你们听听”云云,好像韩石山真就抓住了鲁迅一个什么把柄似的。果真如此吗?鲁迅关于阿长那段描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真有必要说一说来龙去脉了。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我国百年以来难得的散文经典《朝花夕拾》中最为感人的一篇。阿长,就是在百草园给少年鲁迅讲神话故事的那个保姆。她出身卑微,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不识字,却有一颗纯朴的心,给小鲁迅买来了“三哼经”(《山海经》),让迅哥感念不已。据周作人日记,阿长的一生,经历了洪秀全的太平军(“长毛”)活动的全过程,所以她常给迅哥讲“长毛”故事。散文中有一段对话,阿长说当年“长毛”把门房的头砍掉太吓人了。迅哥不以为然,说我不是门房,我不怕。阿长说,小孩和好看的姑娘也要抓去的,去当“小长毛”。迅哥顶了她一句:长毛不会抓你的,因为你长得也不好看。于是就引出了一段阿长反驳的话:“哪里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吗?我们也要被掳去。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要我们脱下裤子站城墙上,大炮就放不出来了……”
就是这最后一小段阿长反问的话成了韩石山的“把柄”。他说,这“对妇女是人格的慢侮,对少年是心灵的戕害”,“这样污秽的文字,你让教员在课堂上当着那些少男少女怎么讲?勉强讲了,你让那些少男们对他们的少女同学怎样的感想?仅仅因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将此篇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人,其无儿女乎?”
好家伙,连鲁迅带教材编选的专家,甚至语文教师和中学生,全都一竿子扫了。韩石山表面来势汹汹,奇怪的是:他为什么对历史背景一字不提?为什么上下文意、语言环境和人物性格他一点也不联系?为什么只孤零零凭空拎出“脱裤子”一段话?不说别的,单是这样锻炼周纳的手法,就很不厚道。
一个正常的、有一点历史知识的读者,今天会怎样看这段话呢?很显然,这就像“义和团”兵丁回忆他们当年所谓的“刀枪不入”和“女阴御敌”一样,也好像经历了“文革”的老人闲时给子孙讲他们当年手举“红语录”天天跳“忠字舞”一样,都是那个特定时代很平常的历史细节。阿长为了表明自己是“有用的”说出的一番话,我们今天读去,表面看滑稽可笑而且愚蠢,细加思考,不是只觉其诚朴,感其可怜,赞其天真,叹其愚昧,而憎恨那个时代的专制和愚民吗?何“污秽”之有!而小孩子迅哥听了,夸赞她“却不料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也和他得到《山海经》时一样,确是怀着无尽深情的。这样蕴藏着多重内涵的大异其趣的文字,这样举重若轻、摆脱任何俗套的别样表达,让我想起俄罗斯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嘉尔曼》。我们只能感叹这是近乎神性的天才。
那么,学生和语文教师对《阿长》一文是怎么看的呢?一位中年教师说得好:“这可不是平铺直叙的课文,有嚼头,有教头!”有些老师把阿长的相关背景交给学生讨论,引发研究兴趣,学生甚至会发出你意想不到的高见。有的学校统计,读过《朝花夕拾》的学生(此书是教育部推荐书目),《阿长》一文居于该书“学生最喜欢的榜首”!韩石山断言那段话要让学生想入非非,只不过是招供二十一世纪中国又冒出一个假道学而已。以己度人,却又扮出杞人忧天的样子。这样作假,连小孩子都烦的!
也有给韩石山那段颇具迷惑性的高论鼓掌的。有篇博文说:“一些小的地方,最能看出他的精细,也最能见出他的尖锐。”此“小地方”,即韩某痛斥阿长说的一段话也。是的,“小地方”,却见出了真问题,让我们见识了韩石山是怎样在鸡蛋里挑骨头,贬斥鲁迅的。虽“精细”而“尖锐”,无奈他那大前提全错了——阿长其言,就散文艺术来说,放在全篇中看,决非“污秽”,实为妙文、奇文。
还有一篇颂扬词叫《壮哉!韩石山》,也是以韩石山呼吁语文课本撤掉《阿长》为由头而赞颂他:“为什么会有深切的社会责任感?为什么会有那种严峻的批判精神?在回答中文系学生提问时,他只说了六个字:有智慧,有担当。”请问:韩石山到处说教“少不读鲁迅”,是哪家的“责任感”?他面对阿长那段话,指鹿为马,是哪门子“批判精神”?至于他自鸣得意的六个字,从“阿长”一事来看,只不过是歪解鲁迅的“智慧”,消解崇高、哗众取宠的“担当”。
在《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一文中,韩石山于类似的“小地方”耍的这样把戏,还真不少,《阿长》只是其中一例。如果连阿长那段话也是“这样污秽的文字”,韩石山先生是不是更有必要上书教育部,在中学禁止“青春期性教育”,禁读《红楼梦》呢?美术系是否也要像当年孙传芳那样,禁止用裸体模特?
由《阿长与(《山海经》)》的前前后后,我想到一个问题。许多论者都强调读鲁迅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这话自然是不错的。但就我自己阅读鲁迅和教学的经历,我感到,在鲁迅的接受上,受众的阅世经验固然重要,另外,是否有点悟性,青少年是否有颗童真之心,也同样重要,并且二者是可以互补的。如果片面强调阅历这一点,势必压抑青少年对鲁迅的接受。像《阿长》这类散文,青少年那样的赤子之心、好奇之心,犹如一个“直通车”,比较容易进入鲁迅心灵中去的,甚至文中一些大人不易理解的鲁迅笔法,孩子们倒没有太大障碍。相反,一些学者文人,或心灵生出老茧,童心泯灭,或养成了某种心理定势,或别有偏见,倒是很难理解和走近鲁迅的。
至于韩石山非要在鲁迅和胡适这两位文化巨人中贬一个、赞一个,只能让国人想起“不是要、就是”的“文革”思维模式,就不仅仅是歪解鲁迅的问题了。正如沪上一位学者、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是“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矛头所向“是现代中国少数值得珍惜的传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