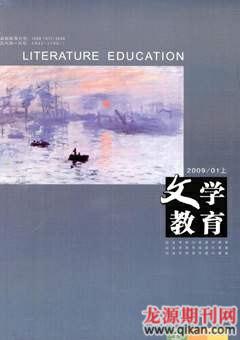从《归园田居》看古代农民生活
组诗《归园田居》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反映了诗人辞官归田之后的农民生活。在这组诗中,陶渊明以细腻的感情、多变的笔调描写了农民的种种生活,酸、甜、苦、辣,品出农村百味。世人也多称赞陶渊明由仕而农、由腾达显贵到无名贫困的坚贞情操,说他的诗刻画出了一个由仕而农、“荷锄而归”的老农形象。确实,从陶渊明的笔下,我们领略到了不少纯朴的农村气息和质朴的农民气质,也看到了他的坚贞和不屈。但是除此之外,从这一组诗中我们还可以略窥古代农民生活之一二。
“少无适俗韵”一诗中写到的“开荒南野际”。诗人刚从官场退下来,虽没有如以前般的殷富,但还是有一些家底的:有一个书童,有一个开门的仆人,还有心爱的小妾相伴。他虽也开荒,但多为仆人所做。但是农民,尤其是贫农,却没有如此好命:他们没有厚实的家底,更没有仆人,他们必须得凭借自己的双手和体力,起早贪黑的去“开荒”。不过从此诗的下文看,农民虽累,却仍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情趣在里面:“依依墟里烟”写出黄昏中家家炊烟绕梁的情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更是以动写静,突出了农村安详、平静的图景。这也许就是诗人想要隐居农村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世俗中交际的压力,没有官场上尔虞我诈的黑暗。
但在安详、平静的生活中也掩藏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天灾虫害便是其中之一。“野外罕人事”一诗中写到“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不独诗人有此担心,农民亦有。虽然旬子早已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但人类毕竟不能控制自然现象,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很有可能使整个村落颗粒无收、饿殍满地。即使桑麻已长,土地已广,但在天灾面前,任何东西都是渺小的,人还是只能屈从。同样的意境也可从“种豆南山下”一诗中看出。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有些学者把这归咎于陶渊明不懂农事之故。但除些之外,天灾虫害同样可使“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与“开荒南野际”相呼应,不仅写出了自己劳动至夜深的景况,更是对农民生活的一种直白:艰辛、劳苦,又不得温饱;付出的劳力与收获的成果不相匹配,生活的重担与天灾的压迫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们却无力抵御,只能“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用各种祭祀活动期盼来年的好收成。
压在农民肩膀上的重担只有天灾虫害吗?不,还有人灾。诗人归隐之时,正值东晋王朝走向没落之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互相争权夺利;军阀连年混战,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苛捐杂税日益沉重;再加上东晋末年的天灾,给社会特别是农村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诗人的家乡浔阳被“洗劫一空”,人民“流离失所”。“久去山泽游”一诗即是诗人通过凭吊故墟,真实地反映了战乱后农村残破的现实。“荒墟”一词既写出了诗人眼前的情景,使诗人的心情由愉快而变得沉重。“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以今昔作对比,构成了一幅伤心惨目的图画,“一世异朝市”更是点出了农民颠沛流离、漂泊无定的景况。现实的黑暗造成百姓的痛苦:农民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被土豪劣绅占为己有,农民翘首盼望的庄稼被充作军饷和赋税,使无家可归、无黍可食、无衣可穿。和平宁静的农村转眼间变成了一片废墟,“死殁无复条”。政治的腐败导致经济的萧条,而经济的萧条导致农民的低贱的愿望被破坏殆尽,怎能不引起农民战争?
“怅恨独策还”一诗直接写的是诗人劳动之余的生活情趣。以清浅的山泉洗脚,以好酒好菜招待邻人,一派悠闲自得。但在这悠闲的背后,却是作者沉重的叹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与不屑,对统治者的失望与痛恨,对农民的同情与理解。以清浅的山泉来反衬黑暗的现实;以与邻把酒言欢来反衬浑浊的世俗交往。“欢来苦夕短,已至复天旭”一句,以乐观的态度来笑对生活的磨难。这既写出了诗人对现实的嘲弄,也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大优点——笑对人生,生生不息。
俞晶晶,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