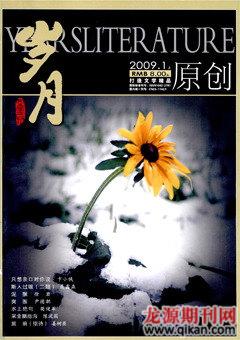花牛车打我家门前过
郭宏文
“花牛车”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山屯里的人对大客车的叫法,就像管摩托车叫“屁驴子”、管自行车叫“洋车子”一样。那时的汽车,几乎都是单一的深蓝色,唯独大客车的车身上带有彩色的条块,因此,山屯人管它叫“花牛车”就不足为怪了。花牛车打山屯里经过,我们这些小小子们常常追着喊:“花牛车,真不赖,没有车头跑得快。人坐里,货放外,不是亲戚别下来。”
我们那个山屯,坐落在一个长长的、深深的山沟沟里,山屯很小,小得仅有二十几户人家。山屯人祖祖辈辈视土地为命根子,盖房子、圈院子生怕占了好地耽误种庄稼,都是见缝插针似的绕着山边选房场。山屯的新老宅院,没有一个建在土质肥厚的耕地里,都在依山朝阳的地方零散错落地分布着,东西看不成行,南北看不成趟,没有大屯子的气派。
就是这么一个小山屯,偏偏有一条省级公路打这穿过。如果没有这条路,我们那个小山屯简直就是个憋死牛的地方。这条沙石路就在我家门前,虽叫省级公路,但在我记事时,路上行驶着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鞍山钢铁厂分矿山拉锰矿石的车。那些车还是早些年从苏联进口来的,日日“隆隆”地往返着,每辆车路过,都会扬起浓浓的沙尘,那沙尘宛如一条狂舞的长龙,久久不散。
有时,我们这些小小子们戴着艾蒿编成的圆圈小帽,手里握着青蒿杆编的匣子枪。趴在路边的沙堆旁,等待拉矿车的到来。一阵“隆隆”轰响之后,我们端着“双匣子”,一起冲进沙尘之中,像电影中的游击战士一样,冒着“硝烟”向远去的“敌车”射击。几个回合下来,我们的形象,就被各自的大人们狠狠地骂成了“土驴子”,弄不好,屁股上还要挨上两脚。
有时玩过了头,我们就开始作妖了,就真的把拉锰矿石的车当成了“敌车”。我们藏在山坡上的荆条丛中,每人的身边都摆着一堆硬硬的、不大不小的黄土坷垃。拉锰矿石的车路过的时候,我们中的“头儿”就一声令下,黄土坷垃就被“嗖嗖”地撇出去,打得拉锰矿石的车“叮叮当当”地响。开车的司机会无奈地一个急刹车,吓得我们这些“土八路”赶紧往山上跑。下车的司机知道车挨的是土坷垃,没啥事,对我们只是吓唬吓唬,根本不去追。别说,这虚张声势的吓唬,对我们这些山屯的孩子来说,还真的管用。这样的游戏,我们就轻易不敢再玩它了。
在这公路上跑着的汽车中,最吸引我们的,就是一天只能见两次面的花牛车。那辆花牛车是从一个叫“锦西”的城市通往一个叫“六家子”的农村的往返客车。我常常呆呆地站在家门口,望着花牛车来去的方向,默默地想象着锦西那座城市该是个哈样呢?我想,那里一定有高楼,有火车,有新华书店,有动物园……那里的人们一定都骑洋车子,都戴手表,都吃大米白面,都喝自来水……想着想着,心里就不免萌生一种想坐花牛车、想到锦西那座城市看一看的念头。于是,我就打心眼里羡慕那些坐花牛车的人。然后,我就暗暗地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坐花牛车,一定要到锦西去看一看。
那年初冬的一天,花牛车偏巧在我家的门前爆胎了,坐车的人都下了车等着司机换上备胎。那辆花牛车是从锦西方向开过来的,坐着三十多人。我赶紧从家里跑出来,悄没声地溜到了蹲在路边等着换车胎的人群前。我感觉,那些人的相貌都像锦西那个地方的人,在我的心里,似乎只有具备了和锦西那个地方的人相同的条件,才有资格坐花牛车,才有资格到锦西去看一看。
忽然,我看见人群中有一个妇女,给一个比我小不多少的女孩子扒一个金黄金黄的像苹果似的东西,里面的瓤儿一瓣一瓣的。小女孩一定是那个妇女的女儿,很是乖巧地吃着她的妈妈给她扒出来的瓣瓣。我那时都七岁了,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东西。花牛车换好了车胎开走后,我像宝贝似的捡起了那个女孩扔下的红皮,忙三火四地就跑回了家里。
母亲告诉我,那是橘子皮,橘子、香蕉都是南方产的水果,很好吃。我问母亲,那些南方产的水果,锦西都有卖的吗?母亲的回答是肯定的。捡回那个橘子皮,我和妹妹经常闻一闻,那香甜的味道,就是特殊得很,咋闻也闻不够。于是,我就对妹妹说,等哥哥长大了,一定坐着花牛车到锦西去,买回几个与坐花牛车那个女孩吃的一样一样的大橘子来,让你好好尝尝。跟妹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禁不住地直咽口水。
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年夏天,我突发奇想,在家门前的公路边,卖起了井拔凉水。我把我们家的木头小饭桌搬出来,拎一桶刚刚从我家深水井里拔上来的哇凉哇凉的井水,摆上一个带把的搪瓷缸子。我在一张图画本的纸上,用蓝色的蜡笔写着:过路人喝水,一杯一分钱。我把这张纸,用石头压在木头桌上。这一被山屯人看成是小孩过家家似的举动,第一天就开张了,买水喝的人,就是坐花牛车的人。那天,那辆花牛车在我的小木桌前停下来,下来的人,都是想喝水的人。那些人大大方方地掏出钱来,买我的井拔凉水,还不住地说好喝。喝完了,还怪怪地望着我,说些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卖东西,实在是有意思之类的话。那一天,我竟奇迹般地卖了一毛七分钱,我成功了。
以后,我又把家里的黄瓜、李子啥的摆在公路边,来吸引花牛车停下来,让坐花牛车的人买我的东西吃。有的时候,我摆出的东西还真不够卖,也有的时候,摆出的东西是咋拿出去的,还得咋拿回来。不知不觉中,我家门前的公路边,成了我们那个山屯的小卖场。如今,那里已经是我们那个山屯的小卖部了,过往的车辆还常常在那里停下来。
一九七六年的正月初四,那辆日日从我家门前路过的花牛车,在我们那个山屯的头道沟,发生了令人惨不忍睹的劫难。那一天,正是我爷爷六十六岁的生日。我们家,还有叔叔家、两个姑姑家,总共四个家庭的二十多口人一同相聚在爷爷家,给爷爷过六十六岁的生日。大家正在喝酒吃饭时,就听见有人喊花牛车在头道沟翻车了。喊声就是命令,我们一大屋子的人马上都撂下了碗筷,一齐向不远处的头道沟跑去。
头道沟路边的深沟里,那辆花牛车车轱辘朝天停着,哭声、喊声撕心扯肺。当时,我的父亲是我们那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叔叔是人民教师,大姑父是一个国营工厂的工人,老姑父是另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在劫难现场,他们主动地扮演起了抢救伤员指挥者的角色。
车倒扣着,遇难的乘客几乎都是头朝下地揻在车厢里。我的父亲声嘶力竭地喊着,指挥着参加营救的男人们采取各种措施,快速进入车厢去营救遇难人员。女人们负责在车外接送并照顾伤员,我们这些孩子们则给女人们当帮手。
车上已经有人死亡,现场到处是鲜血。可我们这些头一次见到那惨景的孩子们,也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子邪劲,在忘我投入抢救战的大人面前,丝毫没有胆怯。我们甚至在公路上排成了人墙,所有拉锰矿石的车都被我们截下拉伤员,不拉伤员的车,一个也不让过。
当花牛车里最后一个男伤员被救出来时,整个救援过程历时一个多小时。除六个人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外,救出的四十多名伤员都被及时送去了医院。当花牛车的单位赶到时,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了。
我们这一大家子二十多口人,几乎是人人带着血迹回到家里的。在这场一个多小时战斗中,我们这一大家子是绝对的主力军。男人们是好样的,女人们是好样的,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是好样的。我的父亲喊哑了嗓子,大姑把呢子大衣给一个女重伤员穿走了,我则是截车孩子帮的头头。那一天,爷爷说他过了一个最有意义的生日。
也就是那一天,十四岁的我忽然领悟到,坐花牛车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我真的有了能坐花牛车的那一天,一定要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