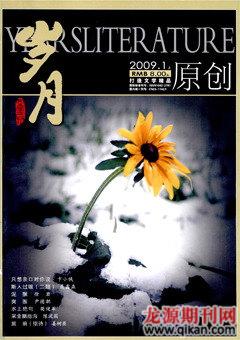私人情感与道义担当
王 迅
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无疑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主流,叙述底层,展现农民、打工仔和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现状,几乎成为很多作家所共同追求的叙事法则。有学者将底层叙事命名为“新左翼文学”,并认为它承载着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表达了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体恤和关怀之情。在我看来,每个文学现象的出场,必定存在着它一定的合法性,当然,底层文学也不例外。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社会群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与断层。这样,“底层”、“弱势群体”等名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然而,很多作品反映底层,仅仅是凭借作者猎奇的想象,从社会中最阴暗、最酷烈的现实中寻找叙事资源,把弱势群体的生活渲染得痛苦不堪,或者写“底层的陷落”,借以表达对社会苦难的关注,却是当前小说创作中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样的文学想象是否有力量,或者说这样的叙事模式是否有效,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从人物来看,卞小侠的短篇小说《只想亲口对你说》写的是一个从东北来到城市的打工妹,如果把它归入底层叙事也未尝不可。但当我读完这篇小说之后,在小说的叙事向度上却明显地感受某些异质性因素的存在。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才使得这篇小说与当前流行的“底层叙事”有了明显的分野,也使底层叙事获得了文学思维逻辑和表达体系理所应当的健康性与合法性。
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兼主人公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廖晨星,与女主人公可可的邂逅成为他人生的一个界碑。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光环中,是生活的幸运儿,是全家人引以自豪的资本。但当他因为失恋醉酒之后与可可不期而遇并与之发生关系,不幸地感染上了被称为第一癌症的艾滋病。残酷的现实与幸福的过去所形成的反差使廖晨星几乎无以面对生活。可贵的是,在这里,作者并未顺着这个思路,去叙写男主人公暗无天日的生活,或报复社会的行为,或颓废的生存状态,而是相反,廖晨星如何寻找可可,又如何去拯救可可的整个过程成为小说叙述的密集地带。很明显,这种反转式的叙述使小说传达给读者的,并不是一味的悲苦、阴冷和绝望的信息,而是道义、责任和拯救等光明的喻示。
在小说中,叙述者廖晨星始终是在场的,贯穿着整个叙事,而可可虽然也是小说的主人公。却没有承担中心意义的叙事功能。显然,这样结构设计,是作者别具匠心的有意安排。可可中场的缺席,成为小说叙事充满了艺术张力的构成元素,这种悬念的设置,又大大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故事的结尾,作者在小说的叙述上又一次使用反转的手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意外情节的设计上。女主人公可可最终说出,她也是被朋友所害才染上艾滋病的。为此,她决意报复陈家的人,但陈家的人的纯朴善良以及他们对可可热情周到的款待,深深地感化了她,这直接导致了可可情感空间的升华。最后,当可可得知。尽管她曾经严重伤害过廖晨星的身心,但廖晨星却能超越个人的情感,千方百计甚至千辛万苦地寻找她,其目的并不是实施报复计划,而是想唤醒她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这使得她的心灵再一次获得净化。
小说在叙事结构上也显得别有意味,故事之门由罪恶(廖晨星不负责任的性行为)所开启,到廖晨星决绝的寻找,高尚的拯救行动;这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小说的副线是女主人公被害,试图报复社会,以至差点坠入罪恶的深渊。在小说中两条线交织并进,使整个叙事在道德的向度上朝着相反的方向滑动,构成一个对称的反讽结构。而可可最后的死,表征着道义、责任的潜在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它足以使人抵制并摆脱主观私人情感的左右,从而使心灵获得净化,获得崇高。
尽管文学不同于哲学,不是思想史,也不是道德史,但却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精神产品,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见之于精神活动的产物。人类历史进入到哪个时期,那个时期社会经济如何发展,意识形态如何多元化,这些外在的因素也许决定着历史语境诸种复杂的可能性,但文学是一项崇高的心灵的事业,这条艺术的内在法则是永远无法被颠覆的。心灵的质量决定着一个作家的真正价值。一部文学作品的道德水准有多高,它所显示出思想质地如何,这些看似学界和文坛老生常谈的文学命题,不一定是我们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照见一个作家内在人格的高下。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推崇卞小侠的这篇小说,它也写到男女情感,但却不同于那些沉迷于自己个人情感小天地的书写,也相异于那些堕落、溃塌的下半身写作和身体写作,卞小侠的叙事使我们看到文学事业所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看到了文学伟岸的身躯和闪亮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