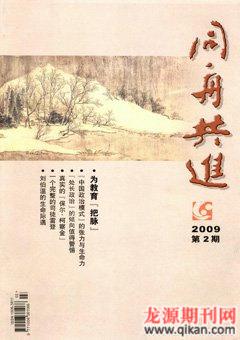陈序经最后二十年的浮沉
张晓唯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围绕“全盘西化”问题展开大论争,岭南大学青年教师陈序经(1903~1967)持激进立场,一时间名声大噪。那场笔战只是陈序经亮相学术界之始,此后他北上任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西南联大时期担任法商学院院长,乃联大院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已成美谈的关于他宁肯不做院长也不肯按规定加入国民党一事,显露出这位学人的鲜明个性。陈序经终其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即使1949年后颇得中共领导周恩来、陶铸等人的赏识器重,即使友人力劝他加入民主党派,他却始终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他平生也未涉足宗教团体,但后来出掌具有教会背景的岭南大学,竟成为该校创办以来首位无教籍的校长。陈序经的“清高”自守,加之他的敢言和“优容雅量”,颇得高级知识分子的好感和信赖。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先后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和南开大学副校长,被赞誉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难得的大学校长”。亦因如此,他为极左的政治氛围所不容,以致由波峰跌入浪底,终于消失在“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之中。
【临危受命接手岭大】
1948年8月,陈序经正式出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初为代理),时年45岁。此前,他担任南开大学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等要职,为张伯苓校长倚重的中坚力量。有分析说,张伯苓甚至考虑在自己因出任考试院长不得兼任校长的情况下由陈序经接任。可是,张伯苓几经权衡之后,同意且催促陈序经返回岭南就任校长一职,这可能是时局使然。当时国共两党逐鹿中原,平津高校隐然成为“第二战线”,办学读书均非其时,比较之下南国还相对平稳。陈序经在大变局到来前夕返乡办学,竟使原本平平的岭南大学骤然“灵光一现”,却是他本人未曾料想到的。
陈序经,海南文昌人,当时籍属广东,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最初任教的学校就是岭南大学。这是一所建校较早、历史繁复、亦中亦西的私立高等学府。
仔细算来,陈序经担任校长近4年,前14个月尚在国民党治下,后一阶段的两年半则已是新中国初期。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广州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政治中心,有段时间政要云集,其中亦不乏向本地文教人士示好者。蒋介石、何应钦或邀宴或要求来校园暂住,陈序经均巧妙地加以回避和婉拒。中共进入广东初期,执掌粤省文教工作的是著名学者杜国庠,陈序经对之尊敬有加,并与广州市市长朱光将军以及杨东莼等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当军管会查出学校出纳处违规存有金条,欲拘捕相关职员时,陈序经却挺身而出,表示:“他是出纳员,我是校长,要逮捕,就逮捕我。”肃反期间,校内地下室发现枪支,一时间风声鹤唳,陈序经调查后行文陈情:枪支为以前学生军训时所用,多为一战时旧物,已锈蚀为废弃物云云。一场风波得以化解。
其实,岭南的创办人乃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在纽约设有“岭南大学基金会”,属于私人捐募性质。美国基金会对岭南大学提供的资金支助,往往换成金条以求保值,为了避开当时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学校用金条到香港兑换港币以发放教职员的薪酬。陈校长的人望,他的诚恳与平易,他的积极主动,加之岭南大学的“硬件”设施,以及时人对于局势的各自判断,形成了众贤汇集岭表的难得一见之景观。
【岭大办学的得意之举】
当年岭南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卢永根先生,在一篇纪念陈序经校长的文章中写道:“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后挥师南下的时候,不少名教授和学者对党的政策存在疑虑而纷纷南下,准备经香港转往台湾或外国。就在这个时候,陈校长毫不动摇地坚守岗位,以自身的行动和礼贤下士的风范,把一批来自北方的名教授罗致到岭大,说服他们留下来,使他们成为广州解放后的学科带头人。广东省的多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来的,在医科领域尤为明显。”
所谓北方的医学专家,实际上主要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关键人物是著名的医学放射学专家谢志光教授。陈序经出任岭大校长刚刚两个月,就利用回天津办事的机会,数次赶赴北平拜访谢志光,恳切相邀,几次相谈后,谢欣然应允,并带来一批协和的名医。他们南下任教岭大医学院,谢志光出任院长,使得该机构盛极一时,雄踞海内。外科专家司徒展晚年在美国撰文忆述:“岭大医学院开办在各学院之后,自1948年声誉骤然公认为全国当时最佳者。”岭大医科的兴盛,乃陈序经办学最得意之举。
不仅如此,陈序经还聘请了陈寅恪、姜立夫、王力、陶葆楷、张纯明、吴大业、陈永龄、容庚、梁方仲等多位著名学者来岭大任教,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师资水平。数学大家姜立夫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教授,与陈序经有同事之谊,他本来已到台湾,但不适应那里的生活,陈序经遂邀他来岭大任教,设立数学系,请他做系主任。陈序经与陈寅恪相识于1934年,两人共同参加一个在南京举行的会议,会后北返列车中相谈甚欢,后又在西南联大共事,彼此相知渐深。陈寅恪与胡适同机飞离北平后,一路南来,事先与陈序经联系,表示愿来岭南大学“避风”。陈序经复电欢迎,随即电汇一笔充足路费。寅恪先生如约抵穗,而其家人却到了香港,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陈校长亲自赴港劝说调解,终于将陈家接回康乐园妥为安置。
人们赞誉陈序经“不但是个学者,而且是个很有远见、很有组织能力、很能团结人的教育家”。他的办学能力突出表现在“识才”与“容才”这两点上。凡遇稍有资历的教师前来求职,他首先要了解该教师是长期从事学术工作,还是以谋官做官为主。对于后者,他认为必不能专心致志于教学,十之八九必婉谢。而对于所聘教师的学术经历、治学特点及教育背景等,他几乎烂熟于心,每每提及,如数家珍。识才不易,容才更难。居高位或具有权力资源之人,能够真正做到“不忌才”实属难得。陈序经对于教授学者们不搞宗派,不分是否“海归”,只要有才学者,他都很敬重。曾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法学家端木正评述道:“陈校长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最成功的道理就是能尊重人。他说过,他当教务长也好,当校长也好,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每位教授在我决定下聘书的时候,已经是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如果我不信任他,就不请他。”
像多数旧时大学一样,岭大的行政系统精干而富于实效。陈序经聘用冯秉铨、任锐麟两位资深教授分任教务长、总务长,前者乃哈佛博士、电子物理学家,口才好,善交际,教学方法高明,深受中外师生佩服;后者是上世纪30年代即来岭大任教的加拿大华侨、神学博士,曾经兼任广东国际红十字救灾会工作,忠于职守,富有才干,社会活动能力强。此二人在陈校长短暂而光耀的岭大办学生涯中作用重大。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他是岭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美国教授富伦先生。在陈序经看来,富伦乃外籍教授中最有真才实学者,他还是美国基金会在校内的代表。对于新校长的若干举措,富伦不仅理解,而且支持配合,二人间的友谊与日俱增。1949年6月,即陈序经履职将满一年时,富伦在向美国基金理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对陈序经的治校才能大加称赞,尤其提到:“在政治动荡之际,他处事不惊,使得全体师生能面对变迁保持平静,令人赞不绝口,而广东一些人却惶惶不可终日。”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随后开始,反美浪潮汹涌而至,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师纷纷离去。富伦是最后一批撤离的美国教授,离别康乐园之际,陈序经一人前来送行。此时,岭南大学前景黯淡,教育部已经召开了“全国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真正的“社会变迁”才刚刚开始。
【院系调整后的“赋闲”与“出山”】
当初有些人动议,将岭南大学迁往香港,遭校长陈序经否定。他的理由是,如此完善的一所大学迁移异地,谈何容易!而他内心则认为,国民党腐败失去江山,取而代之的共产党应当有希望。抗战时期陈序经在南京、重庆曾见到过周恩来,他对这位中共领袖印象不差。江山易手后,他拥护人民政府,与粤省主政者也建立起融洽关系。但是,他担任岭南大学校长的后半段,总的感觉是危机四伏,精神压抑。除了“思想改造”的政治压力外,过去办学的一些有效做法行不通了。他自述:“政府命令停止使用外币,本校若是使用了是违背政府命令。校长是学校负责人,做了违法事情,坐牢或任何处分,校长是最先一个。假使不用外币,教职员工的生活又必有了很多困难:有段时间人民币从五百元兑换一港币贬至五六千元兑换一港币。私立学校校长在经济上无办法,就做不下去。”私立学校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本来生龙活虎的陈校长也愈加无可奈何。他甚至后悔自己离开南开而来岭南的选择,在一份“检查”中他写道:“我曾经将这个意思向杜(国庠)厅长说,他劝我勉为其难做下去”,“可是在精神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始终是感觉到痛苦”。
1952年春,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拉开帷幕,岭南大学与其他十余所具有外国教会背景的大学一并被取消。岭大取消校名后被并入中山大学,其原有的医、农、工、法、经济各学科被调整出去,只有文理二科进入新的中山大学,而康乐园变为中大新址。对于如此“大动作”的学科调整,陈序经内心不无保留,但他配合工作,并无外在的抵触。从这时开始到1956年的4年间,陈序经没有担任任何实质性的行政职务,被安排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做一名研究教授。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已通通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化”取消了学科,研究历史乃唯一选择。好在他对古匈奴史、东南亚各国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等均有兴趣和学术积累,默默耕耘成为他这4年的主色调。自1952至1966年间,陈序经撰写书稿约250万字,计有《东南亚古史研究》8种、《匈奴史稿》、《西双版纳历史释补》及《中西交通史稿》等。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如此成果,其勤奋与毅力令人唏嘘不已。据其家人介绍,他养成了早睡而凌晨4时起来写作的习惯,多年不辍,即使日间肩负繁杂公务亦是如此。
海外报章对陈序经离开校长职位长期“赋闲”有过失实报道,一些朋友于是劝他出国另谋出路,国民党人士也来信鼓动他“脱离铁幕”。对此,陈序经平静处之,他自信平生教书办学,从未涉足任何政治活动,共产党不会难为自己,仍安心作学术研究。问题在于,陈序经虽无“官职”,但威望与影响仍在,原岭南大学的教授乐于与他接近,听取他的意见,甚至有一稍嫌夸张的说法:陈寅恪唯陈序经之言是听。如此一来,已经实行党委制的大学权力机构感觉遇到了挑战,必欲“纠正”而后快。某位学校领导用暴君的姿态对待高校知识分子,以致连很有涵养的陈序经也私下忿忿抱怨:有的人不仅要用脚踩在你的身上,而且还要用脚踩在你的鼻子上!
1956年对于陈序经来说是个转折点,先是被评为一级教授,后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还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和广东省政协常委。这一变化,与那段时间知识分子整体处境的改善有关。据传,主政广东的陶铸某次进京汇报工作,周恩来总理特别提起广东有一位能聘到一级教授、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教育家陈序经,应当向他学习知人善任的本领。后来,陶铸与陈序经几乎结为莫逆之交。还有一个背景不可忽略:当时东南亚华侨筹建新加坡南洋大学,在全球杰出的华人学者中物色校长人选,陈序经的呼声很高,反映出他在华侨社会的声誉和影响,此事对中共高层不可能没有触动。
再次担任校长(副职),陈序经意识到自己是十几所被解散的私立教会大学校长中极少被重新启用者,但此刻履行职责的情形与以往主持岭大已明显不同。上有党委会负责思想政治和干部人事,各位正副校长各有分工,只要各安其职即可,全不似私立校长独自当家的劳顿与风险。陈序经分管基建、房管和卫生,几年间增建了体育馆(临时会堂)、生物楼,还扩建了学校医务室。但他上任刚刚几个月,“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陈序经一向以“敢言”、“好辩”闻于世,颇有所谓“一士谔谔”之概。可是在1957年“鸣放”时,他却显得比较谨慎,发言很迟,那篇发言记录稿《我的几点意见》6月间发表在《南方日报》时,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事态转折已非常接近了。他的发言温和含蓄,但不失锋芒。其中谈到:高校内泛政治化现象严重,学术与政治不分,一些党员用搞政治运动的经验,硬套到高等教育上;一些党员做事往往不讲法律和制度,一些干部与其说是违法乱纪,不如说是无法无纪。他在发言中强调,高校如果不要党的领导,是很难想象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党的领导,而在于如何领导。曾有报纸点名批评这个发言,而陈序经在反右运动中竟安然无事。据知情者透露,陈乃“内控右派”。由此或可推断:中共高层在对陈序经的使用问题上存有分歧,而对其肯定者居于上风。
【出掌暨南大学】
粤省政治区位特殊,从清代中后期的“十三行”到现代的毗邻港澳,加之沿海侨乡居多,流动性与开放性明显,其主政者需要灵活应对,为官也就比较开明。当年陶铸作为“中南王”,肯于善待陈寅恪、陈序经等人,显示出他过人的眼界和气魄。1958年,为适应华侨子弟的入学要求,新暨南大学在广州成立,陶铸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份兼任该校校长。其间,他多次访晤陈序经,探询办学方策。经过几年草创,学校初具规模。1962年底,陶铸执意卸去兼任的校长一职,坚请陈序经接任。这样,年近花甲的陈序经便开始了一段暨大校长生涯。
自1963年至翌年上半年,作为暨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主要致力于两件事:一是提高教学和学术水平,二是建设校园。他筹划自外校调入一批骨干教师,几经努力,仅小有所获。社会组织形态已然变化,过往的成功经验如今难以奏效。他秉持教育管理要有“优容雅量”的想法,亲自登门造访暨大每一位教授,亲自接待返乡来校探访的侨生家长。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对教职员工从不摆校长架子,每每清晨乘小车远道来校,途中遇有本校人员必定招呼上车,以至校长的乘用车被称作“小巴士”。他在任期间,暨南大学作为一个特例成立了校董事会,廖承志为董事会主席,成员包括费彝民、王宽诚、何贤等海内外知名人士。陈序经的亲和力不仅在校内大行其道,也不断扩延到海外人士中,无论相识与不相识,人们愿意与他商谈各类办学事宜。在不长的时间里,学校增设外贸系、东南亚研究所,筹办医学院,增加图书仪器,扩大海外学术交流,华侨子弟回祖国读书的人数明显增多。
陈序经办暨南大学有声有色,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在极左年代里,却无意中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还在他上任暨大校长之初,上边即有责难声:“为什么找一个党外人士做正校长?”
【在南开的最后岁月】
1964年6月,中央突然下达调令:陈序经转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调离广东。陈序经不明所以,也极不情愿重返南开。他求助于陶铸,陶铸坦言此次自己也是爱莫能助,反而劝他北上就职为宜。究竟是何原因促成了此项调动?陈序经与粤省高级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及与海外人士的互信合作,在一些人看来,已事实上形成与党争夺知识分子、与党抗衡,影响恶劣,有人甚至贬称他为“土皇帝”。其实,此类“反映”在极左和封闭的政治环境里始终存在,当然构成一种推动因素。不过,事态突然生变,应与高层的直接介入有关。近年香港一刊物载文披露: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某位领导对陈序经在香港出版一系列历史著作,怒斥为“无组织行为”,其收取稿酬是“变相贪污”,严令“此人永远不许担任正职”。在可靠的档案文献公开之前,姑且将这一说法存录于此,留作参考。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之初,陶铸上调中央,党内尚有人指责他任用有大量海外关系的陈序经,欲借以阻挠陶的升迁。
1964年9月,陈序经怀着无奈的心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天津南开大学。世事难测,转了几圈又回到了原点,旧人已零落,而新人反将旧人当新人,他的内心难免感到苦涩。当时南开已有六位副校级干部,他是第七位,只能分管卫生之类,实际上无事可做。遇见西南联大老友、历史系教授郑天挺,郑问他现在做些什么,他答说练习烹饪技术(自作伙食),可见其初返南开之境况。“文革”初起,陈序经作壁上观,以为与己无涉。岂料严冬时节狂飙突起,他被揪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美帝文化特务”、“黑线人物”等罪名汹涌而至。随后被抄家,住房遭强占,夫妻二人被赶至仅几平方米的一小屋内安身,还被责令不断地写交代材料。陈序经身体一向强壮,此时却急转直下,听力、排尿均出现障碍,1967年2月16日终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年仅64岁。
长歌当哭,总在痛定之后。像陈序经这样的学者型校长、才华横溢的教育家,却被狭隘的偏见、俗陋的嫉贤妒能所戕害,时代和民族的悲哀莫此为甚。陈序经的学养、经验和操守,值得后人尊重和感念。可是,他因遭遇高校的厚重壁垒而不得尽展其才,则是必须痛切反思的一个制度性课题。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