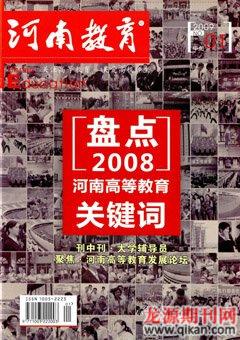文化决定中国
李 林

谈到文化,学术界流行“文化圈”或者“文化区”这样的概念。目前,世界上主要有“西方文化区”“东亚文化区”“中东文化区”等几大文化区(圈)。大家会问,难道“文化区”或者“文化圈”的划分仅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吗?显然不是。比如,澳大利亚非常接近南亚,可是它却被划分到“西方文化区”。更为蹊跷的是,非洲是一个完整的大陆,但是北非和中东同属一个文化区,而中非属于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区,南非却又被划分到“西方文化区”。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惑:这种文化圈的划分依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再把文化区与世界主要宗教的分布作一个比较,就会恍然大悟:这种“文化区”的划分依据主要是宗教信仰形态。就是说把同属于这种宗教信仰形态的国家、民族或者地区统一划分为一个“文化区”。
目前,世界上流行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有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例如说印度教、道教、神道教、原始宗教。至于儒家学说,我认为应该称“儒学”而不是“儒教”。那么,形成文明生态,决定宗教之间差异性以及信仰特色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价值感”,或者叫“价值观”“价值取向”,它是文明生态的“原动力”——正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才形成了文明生态(人与人之间行为方式的不同,关键也在于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价值感”由“正向价值冲动”和“负向价值冲动”组成。正因为各种正负价值之间的取舍、对抗才形成了一种张力,才决定了人的价值感(价值观),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态。
一
目前,世界文明存在着一个“三极结构”,就是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基督教文化区和以中东北非国家为主的伊斯兰教文化区,还有随着中国的掘起,重新被提升为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相提并论的一个儒家文化区。上述三个主要的文化区,形成了目前世界文明的“三极结构”。当然,世界上同时还有其他文明形态,即便是中国文化,也包含有许多形态。例如中国有“齐鲁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吴越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等。即使大体相同的文化区,内部也有微小的差别。比如,在对殡葬的处理上,西藏一些地区流行天葬,中原地区则崇尚土葬。可见不同的文明形态、风俗习惯,反映出价值取向的不同。
我们首先分析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基督教认为“罪感”是人类最大的负向价值。《圣经》里说:“罪是致死的病,必须根除才可救药。罪像不止息的旋风,像不稍歇的火山,像从精神病院里逃出的狂人。”每一个基督教徒在教堂里做完祷告,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上帝,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基督教认为人类所犯的一个最大的罪过就是亲手把来拯救人们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本来是作为拯救者“基督”的形象显现的,而我们不但没有接受他传授的福音,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人背离了上帝、背离了福音,这在基督教看来就是最大的罪。从价值感上看,基督教的“罪感”更多的是偏重于人性的本质,就是说人性天生就是偏失的、人是带着罪感来到人世的。基督教既然念兹在兹地审视人性中的“负向价值”——罪感,它必然会提出一种“正向价值”来拯救这种罪感,这就是“爱感”。《圣经》中说:“爱是上帝的本性。”只有“爱”才能救赎“罪”。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没有爱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罪感”和“爱感”形成了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价值张力,也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原动力。
二
我们再来分析伊斯兰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伊斯兰教认为人生最大的负向价值是“恶感”。《古兰经》中说:“安拉造化种种善事,而魔鬼则造化种种恶事。”所以,《古兰经》教导穆斯林“即使你不能尽善,也要劝善,即使你不能完全戒恶,也要止恶”。一个合格的穆斯林“应该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伊斯兰信徒应该是“为了人类的福利而被教化的优秀民族,你们要劝善止恶,并坚信安拉”。由此,我们发现基督教的“罪感”和伊斯兰教的“恶感”已经存在微妙的差异(这种微妙的差异可以看做文化基因的不同),就是说“恶感”更偏重现实世界的不公正,而“罪感”更偏重于人性中的缺失。正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差异才导致两种文明生态的不同、文化基因的不同。伊斯兰教既然对作为负向价值的“恶感”如此关注,它必然会提出一种正向价值,这就是“义感”。“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的本义就是“正义”,所以《古兰经》中说“正义会指引你们步入乐园”“不义者必在永恒的刑罚中”。穆斯林“除非因为正义,你们不得干犯真主的禁令而杀害一人”(当然现实中很刁诡的是,人们往往以正义的名义去杀人,这是另外一回事)。伊斯兰信徒对于现实世界中的“恶”表达出一种断然的不接受、对于非正义的行为表现出一种激烈的反抗,因为他们坚持“义感”。“恶感”和“义感”形成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取向。
三
我们最后分析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的内部又存在一个“小三极结构”——由占主流的儒家文明和作为辅助的道教文明与佛教文明共同构成的。两千年来,这三种文明形成了中华文明主体结构的三角形支撑。我们分别来剖析儒、道、佛三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儒家指出人生的最大负向价值是“耻感”。儒家教导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甚至说“无耻之心,非人也”,就是说如果人没有羞耻之心,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人。儒家的“耻感”和基督教的“罪感”、伊斯兰教的“恶感”又有一种微妙的差异,即“耻感”更偏于对作为社会纲常的道德伦理关注。中国人骂人,比较严重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太无耻了”。儒家正因为对于“耻感”这种负向价值的关注,所以要提出一种“正向价值”作为指归,即“德感”。“耻感”和“德感”构成了儒家的一种正负对抗的、二元张力的价值取向。在中国,表彰一个人的最大礼遇就是说他道德高尚。“夫子之德至大,天下莫能容。”这是颜回对孔子的评价,所以在中国夸赞一个人说他有“德”是最好的褒扬方法(与“无耻”对等的就是“缺德”)。儒家把“德”与“耻”两者并提作为一种价值对应关系,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又表现出一种文化基因上的差异。
对于道教文明,我更愿意用“道家文明”来表述,因为中国的宗教(建制性的宗教)并不那么明显。道家所关注的“负向价值”是“逝感”。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死与生与?天地并与? 芒乎何之?忽乎何适”,就是追问个体生命究竟要归根到哪里。对于道家而言,“终有一死”的生命对人最大的价值伤害:“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正因为道家基于“生命只能被动地被时间侵蚀而毫无作为”的特别关注,他们才会尽量延长生命的旅程,所以道家追求与日月齐光、与天地并寿。道家的负向价值是“逝感”,其所建立的正向价值就是“乐感”(或者称“悦感”)。道家认为只有体悟大道的人才懂得去追求人生极乐、一种艺术化的生命,所以“乐感”就是道家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
对于佛教,他们认为人生最大的负向价值是“苦感”。佛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所以,佛教必然要提出它的一种正向价值来对抗这种“苦感”,就是“寂感”。“寂灭现前了无所得,是所谓涅空寂之理”,佛家所谓的“涅”,就是说把人内在燃烧的欲望熄灭掉。“涅”在梵文中的原意就是“蜡烛的熄灭”,用来指代人生境界。当然,大乘佛教又提出了“悲感”的价值主张,就是“普度众生”,那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四
上述五种主要文明生态,就是世界主要文化区的文化基因图谱。正是文化基因的不同和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才导致了文明生态的千差万别。我们作完世界主要文明生态的价值取向的比较,再来看它们之间的文化衍生形态、文明冲突会有什么样的规律。这里才真正进入“文化决定中国”的核心。在这里,我借助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思维方式——五行思维。“金、木、水、火、土”作为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基本力量,其相生相克的关系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是中国思维的“元结构”,实质上也是中国人的心灵结构。中国古人的智慧就在于不但找到了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而且使这五种元素之间组成了一种紧密的、相生相克的深刻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的组合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与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我们作一个数理推理就知道,至少要有五种元素才能组成事物的相生相克关系,这就是中国智慧的高明之处。恰恰是“五行思维”的发展,才使得中国从宗教崇拜中脱离出来。因为中国殷商时期还处于多神教时代,“五行思维”的成熟,使中国人一下子从多神教生态跃进到人文生态,“以人文化成天下”的基本精神也恰恰是中华文明没有断绝的文化基因,而其他文明两千多年来仍处在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衍变过程。
运用“五行思维”这一中国人思维的“元结构”来比附我们所分析的五大文明生态,就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儒家文化的表征可以用“土”来表示(当然你也可以用A、B、C、D、E中的一个来表示,但是,既然祖先给了我们“五行思维”,我们就以“五行思维”,来作一个比较),因为儒家说“有土斯有民”“土者,万物之所滋生也”……中华民族是崇拜黄土的民族,所谓社稷,就是国家的象征,“社”乃土地之神,“稷”乃五谷之神。“土”的文明形态的优点是以社会群体道德伦理至上,注重同一性,抑制个性,对异质文化有包容性,很少有排他性,但是“土”的特性决定了若国家内部不团结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会迅速没落。道家文明的表征可以用“水”来表示。道家主张人应该像水一样追求自如的、无拘无束的精神自在。道家以生命的原始生态为终极归依,注重身心和谐的生命质量,同时追求实用主义的智慧,崇尚个体逍遥、有审美的诉求。但道家过于崇尚无为,忽视了群体的精神。佛家文化的表征可以用“木”来表示,佛家追求一种静止的状态、一种独立向上的生长力量。它过于看重自我解脱,所以佛家最大的价值追求就是像树一样生长到最后“修成正果”,它过于看重自我解脱,出世的倾向浓厚,忽视利益的驱动,虽然重视内省和反思,但是行动力弱。因为追求静止的力量,没有攻击性,同时就会缺少进取精神,相对也比较追求自我价值、而对群体价值有所回避。目前最强势的基督教文明的表征可以用“金”来表示。基督教(金)的文明生态使西方文化追求精神的高贵,而其高贵的另一面就是威严肃杀。“金”一旦被拉长成为一个“剑”,它就既具有极强的团结精神,也有可怕的攻击精神。“金”型思维讲究规章制度、崇尚直线形的科学逻辑,因为“金”的边际很精确。因为“金”的属性是最难兼容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对其他文明生态情感上很难兼容),所以容易形成单一价值形态的政体,如西方整个中古时期就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就非常有攻击性。后来,他们才发明了一种政治制度叫“三权分立”(因为它的价值诉求有单一性倾向,所以必须分开才能制约)。伊斯兰教的文化表征可以用“火”来表示。整个中东地区,在很早之前流行的就是拜火教,其思想源头是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就是崇拜火的力量。此地区诞生的《古兰经》亦强调说“我已为不义的人预备了烈火”。伊斯兰教的信徒追求正义,最反感外来力量的压制,但是容易过于强调力量,缺少柔韧的忍辱精神。
五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得到世界五种主要文明生态的关系表。通过这个关系表,我们对世界上目前发生的各种文明冲突,对中国历史的更迭兴衰演变,就会一目了然。如从这个世纪开始,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我国的道家文明会跟着复兴,并在西方大行其道。道家的这种文化形态是“水”性的,而当“金”与“水”相遇的时代,就是说西方国家会对我们道家文化中一些修身养性之道都会喜欢,这是不同文明的文化基因结构决定的。
虽然,我在前边表述了几种主要文明生态相互冲突的内在关系,但是我必须指出:单一(或单边)价值观是文明生态发展的最大危害。我认为单一的宗教体系内没有真理,单一的价值体系内没有信仰。所以,我们要以一种包容的、开放的、博大的情怀和视野去打量和接受其他文明生态。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生态都有它生存的价值,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我们民族主义的态度来攻击其他文明。
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基因结构何在?中国传统上有儒、道、佛的文化精神,分别代表“入世”“顺世”“出世”的价值主张,所以中国的文化基因是“入世”“顺世”“出世”并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中华民族不会有暴烈的民族性格、不会有偏执型的人格、不会有攻击性的国家意识。“五行思维”还提倡“以和为主”的文明生态,就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其中的关键是“五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与”,可见“五行”之生克关系的实质并不在于对立、服从、垄断,乃在于“和”。“和”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所呈现。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应该重新振奋其精神气度,文化的崛起将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重要保证与核心体现。自重并珍视自身的文化传统,我们的自信心就会提升。
(作者系清华科技园文化专员,本文为作者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学院“国际文化交流节”期间的讲座)
责编:思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