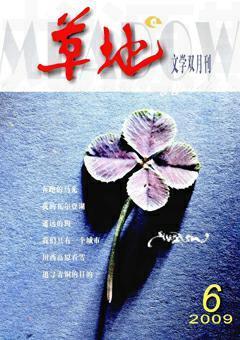遥远的狗
梦 非
那只狗哭泣的时候,一轮月亮正从东边的山峰后升起,银白色的光像扫帚一样从西北面的荒山上挪动下来。
光的下边,就是村庄。
狗是村庄里一家农户养的,主人叫五斤,是他生下来时的重量,也就顺便成了伴随一生的名字。狗叫大黄,一身都覆盖着金黄的颜色,连一根杂毛都没有,在山野中出没时就如一团移动的火焰。
因为山村位于的深山除了山还是山,寨子及周边的田园像是大山的肚脐眼,高大的树和茂盛的草衣服一样伏贴在上面,对于硕大的世间,和不存在没有两样。
但有狗的地方就会有故事,尤其是那只大黄,它的出身就带了些来历。
这得从五斤说起,他出生在一户有一杆明火枪的家里,一家人惟一的业余爱好就是狩猎,而狩猎就需要狗,五斤从小置身其中,就培育了两大爱好,一是狗,二是枪。当光阴无数次地将春天变成冬天,又将冬天变成了春天的时候,五斤也位于了青年和中年之间,并成了户主,一座石头房子里除了他,就是一只狗。
狗并不是大黄,而是它妈。
他妈是一只黑狗,有些娇艳,在山里众多的狗们眼里,是绝对的美丽,成天被一群不务正业的狗围着,也就感觉良好,狩猎的水平只限于咬住一只野兔,但却有粘花染草的本领。一天,它独自外出,在一片开满了羊角花的树下巧遇了一只来自后山的公狗。它一身的黄,正追赶着一只獐子,眼看就要捉住,獐子在绝望中已开始放弃逃命,发出了哀叫声。
就在这时,它风流的老妈窜了过去,一声婉转的低鸣,就让已准备含住獐子喉咙的男狗停了下来,转过身和它一见如故地打起了招呼,獐子一见,立即从一棵开着白色的、细米般碎乱之花的树丛上越过,落地时被一根白桦树的枯枝绊了好几个跟头。
随后,两只狗就在一片树林与草地上像一见钟情的男女般浪漫了起来,回去不久就为五斤生了一条小狗。
小狗就是大黄。
大黄一出生就在村庄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和成了持续不断的谈资,首先它一落地就和其他狗类不一样,眼睛是睁开的,而且很大,水汪汪地,能将看见的东西映在里面,人们闻讯跑来,和它对视,每一个人就感到了背皮子发麻,总觉得那双狗眼看人一点都不低,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藏在眼底,让人害怕。其次是它一身金黄,而村里是没有黄狗的,都认为有些不可思议,老人们说,可能是哮天犬的种,所以,大黄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感。
大黄从来就没有安分守己过,在村庄里从最初的蠕动到飞快地跑,总是明星一样地引人注目,两个月的时候,身体就已如一条半大的狗大,力量惊人,能将其他的同类咬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成天带着同龄的狗伴,任意玩耍,将全村喂养的鸡猪猫羊整得惊慌失措。
它除了它妈似乎已没有可以在乎的了。
做多了坏事,就引起了不满,人们便天天都在骂它“豹子吃的”,并带着恶毒的味道。受连累的当然是五斤,他只好一天天地道歉,暗中却对大黄爱得不行。
一天,清晨的阳光从山野水一样浸漫下来,空气中充满了青草的气息,地里有雾气纱一样升起,路边的草叶上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大黄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随意地卧着,思想一天里将进行的游戏。日子很安详,它想,等五斤提供了早饭就出发,在一处叫老鸦石的地方召唤自己的队伍,然后就去森林中捉一只兔子野餐,但等了很久都没有动静。原来,它的狗妈昨天出去捕猎后就没有回来,在老地方与山后的黄狗也就是它的狗爸约会后,觉得天天这样太麻烦,干脆抛家弃子私奔了。这是一位上山采药的人看见的,他说,有两只狗从山上的两座山峰间欢快地逛着走了过去,那只黑色的就是大黄它妈。
当时,大黄即将满岁,却已是成年一般大,金黄色的毛闪闪发光,体态丰硕,就像村中一头半大的驴,只是思想还处于年幼的时期,对五斤与母亲充满了依恋和依靠。
太阳完全照耀下来后,大黄仍没有等到早餐。肚子开始饥饿起来,发出咕嘟咕噜的声音,有一次竟然把它自己吓了一跳。而大黄是不吃屎的,这也和其他狗不同,当听见有人喊:“崽——崽——崽”时,见一些狗拼命地冲将过去,将小孩拉下的东西一吞而尽,还将小屁股舔得干干净净,它就感到恶心,而且觉得它的同类们有一股臭味,这也是它时时感到孤独的原因,“如果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才不会理它们呢!”它想。
到了中午,它才感到了等待别人喂养的日子已经过去,“饿了得自己觅食才算好狗”,大黄想。当那些吃了很多屎的狗群即将走到它们游戏开始的地方,想如过去一样在它的领导下疯狂到天黑的时候,大黄却走进了一大片火地边的树林,连招呼都没有打,因为它从来就对他的那些追随者不屑一顾。
这天开始,大黄就成了狗中的独行者。
走进了树林却走不出饥饿。大黄转悠了很大的一圈都没有发现可以搜捕的猎物,那时,正值夏日,绝大多数动物都迁到了更高的山野,留下的只有一些土野鸡和企图在夜晚出来偷食半成熟的土豆的刺猬和野猪,要抓住一点什么并不容易,而它确实饿了,已快没有了力气,它想“狗是钢,肉是铁,一顿不吃难狩猎”。于是悄悄窜进村子,干了件几乎让它付出生命的事。
大黄走到的地方处于村庄的下边,因有一口井,就住了一家人,当家的小名六十二,是出生时他爷爷的年龄,和五斤有些过节。事情很简单,他娶了五斤喜欢的女人,弄得五斤至今还是单身。六十二又得提防,怕天天来往出一些风花雪月的事,就干脆找了个借口把两家弄成了不相往来的冤家。
当时,饿得不行了的大黄藏在草丛里,前面是一片黄豆地,豆子们很快乐,正在阳光下生长,身上的虫和叶以及半饱满的豆角吸引了六十二家的鸡,它们打打闹闹地在田里转悠,样子有似“胜似闲庭信步”。大黄觉得饿了吃一只鸡也不错,就隐藏在草间,等待机会到来,它想,这不是好事,一定要弄得人不知狗不觉。
正想着办法,机会却来了,好像活该有事似的,六十二家里一只负责打鸣报晓的公鸡,突然对一只贵妃般丰满的年青母鸡产生了爱情,试图过去亲热,而鸡贵妃却只想吃豆角,见公鸡撒开大脚,摇摆着冲将过来,就向田边跑去,刚钻进草丛就碰上了大黄的嘴,这让大黄无比意外,脑子一转:“哪有到口的鸡不吃”。顺势一口,就咬断了鸡贵妃的脖子。然后,一转身,把它拖到了一丛细叶子牛肋巴树下。
吃了鸡贵妃的肉,大黄增加了许多精神,想明天一定要在不饿的时候上山捕猎,它一直认为自己会听人话,人们经常说的“饱带干粮”,它经过观察就知道了意思,总是看见五斤才吃过了早饭,出门时又会在腰间装一块烧馍,大概对狗们来说,就是饱思猎物吧!大黄认为肯定是这样。
但还未等到天黑,事情就败露了。大黄睡了一觉,看见太阳已开始吻到了西边的山,就准备回去,在夜里,它觉得还是卧在主人家的火塘边舒服,就走了回去,刚一进村口,就被套了个正着。其实,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坏事是它做的,只是对狗进行检查,其他的狗都已检查完毕,没有
发现证据,只剩下大黄还没有回村,所以对它的检查就特别地仔细,一仔细就在它的眼角与耳朵之间发现了一根鸡毛,经验证,正是鸡贵妃的。
这就捅了马蜂窝,首先是六十二像中邪一样从地上奔了起来,嘴里喊着,“打死它!打死它!”并述说着那只鸡的可贵。
原来,当发现鸡贵妃消失的时候,六十二就发动一家人和一些村人开始了寻找,因为那只鸡是非常重要的,自从成熟后就不停地下蛋,好像从来没有停歇过,如生育旺盛的老鼠,有时一天下两个,而且很多是双黄,这在山村是绝无仅有的,鸡贵妃就成了一棵小小的摇钱树,每天可带来一毛至一毛五的收入,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就够了。
大黄在一群人和一群幸灾乐祸的狗的附和中感到在劫难逃,身体已被牢牢控制,只是感到奇怪,它记得自己做得非常隐秘,下口时鸡没有发出声音,连那只公鸡都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妃子已命丧狗口,仍在四处寻找想体验一番鸡类的浪漫。大黄吃完后,还刨出一个坑,撒了一层土将鸡毛掩埋了起来,然后,又到井边喝了许多水,将脚爪子和口脸都洗了一遍,却忽视了最不容易注意的眼耳之间。大黄感到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于是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到来的惩罚是毒打,六十二要求当众行刑,而且要由五斤自己动手。这很恶毒,谁都不会忍心打自己的狗,尤其是像大黄这样帅气又有思想的狗,但六十二不干,他用忆苦思甜般的诉说得到了村人的同情和对大黄的恨,五斤只好随手拿起一根六十二递过来的棍子,朝大黄辟头盖脸打了下去。
毒打进行了九分钟,一位心细的村民说他记的数字是一共打了一百九十九棍。
大黄本来不打算叫喊,但最终吃不住痛,在最初三分钟的时候,就用带着愤怒的叫声以示抗议,它觉得人类不可思议,不就一只鸡吗,还得用狗命来抵。只是它不知道人类还有“打狗看主人”一说,如果看自己的主人,就只有被打死方止了。
行刑进行到四至六分钟,大黄的叫声变成了哀求,汪汪的声音有时像是嘶声力竭的哭,有时又像一个疼痛难忍的人在大声喊叫,哀号声响彻云霄,四周围观的人声音也渐渐小了下去,惟有大黄的叫声传向山野又被山野挡回,发出了更加悲苦的回响。
到七至九分钟,大黄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哀嚎变成了呻吟,至最后一分钟,就没有了气息。那时,人们也完全静止了下来,看着棍子一下一上地击打在大黄的身上,又发出如敲打皮鼓一样的嘭嘭声,心一下子就揪紧了。山村人是极富同情心的,主张打是同情六十二家的油盐酱醋没有了,现在突然觉得那毕竟是一条狗,又不懂人事,打得那样惨,又何必呢!就有人跑过去,抓住了五斤的棍子,而五斤却还在抢夺想继续进行,他已完全是机械性的动作了。
又有人走过去,伸出手放在大黄的嘴边,感到还有一丝热气,就说“还没有死,真是狗有七条命!”大家就围着,过了一段时间,大黄从地上撑了起来,歪歪斜斜地从人们让出的缝隙间半依半靠地挪过,努力走到一堵断墙下,就吐了一地还没有消化的鸡的残留物,转过弯,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一直到傍晚,五斤水也没有喝一口,双手抱头,木然地弓在柴根上,没有一点活人的表情。
入夜,他才想起大黄没有回来,便诈尸一般跳起,拿了手电筒,出门沿着大黄滴落的鲜血寻找而去,在村外老鸦石的下边找到了它。
那段时间,大黄一直在呕吐,五官流着血,五斤看见一地白色的泡沫和大黄的惨状时,便丢了手电筒,大叫一声,抱了大黄的头,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于是,人和狗哭成一团,在本来就荒凉的山村夜晚,那传向远方的呜咽声,让天地平白无故增加了许多的凄凉……
人狗伤心到上半夜,五斤才将大黄抱回石屋,放在了火塘边一块专门展开的山羊皮上,又煮了一锅粥,清凉得如镜子,放在大黄的嘴边,它没有喝,却从米汤中看见了自己鼻青脸肿的样子。
它想,人们喂养的动物是不能吃的,这是一个教训。
几天后,大黄就康复过来,强壮的身体和超狗的智慧让它具有了超凡脱俗的能力,它觉得这可能还得益于当时用两只前脚抱住了头。
一天清晨,六十二家里那只追求爱情的公鸡开始报晓的时候,大黄走出了家门,向村后西北边一座雄伟的大山小跑而去。
此后,村人就很少看见它的身影了。
山很大,绵延了几百平方公里,最高峰大雪山是好几条河的分水岭,人迹罕至。相传,那里曾经是人们上天的地方,有一棵树,人只要到了那里,再爬上树梢,就可以进入天际玩耍一回。后来,一只猴子偷跑上去,打翻了一碗水,造成了人间洪水朝天,天神震怒,就砍倒了树,从此人间就和天际便断了来往。当然,大黄一开始并不可能到达大雪山,因为山太大了,从高空看去,是众多的山峰,山峰间是广阔的高山地貌,生长着森林、灌木、草甸和飞禽走兽,山村就在众多的山峰中的某座之间,已经大得村人一生都难以穷尽,大黄就活动在那些树林、草场和灌木之中。
开始,大黄并不顺利,它狩猎的经验不足,只是抓一些兔子,到了冬季,高山上的动物经不住寒冷,或者需要寻找食物,开始大批量下山,这就给了大黄练习与捕捉的机会,它开始对兔子不屑一顾,目标成了山羊、山驴和獐子,抓住后吃不完就放在老鸦石下,那里就像一个冰箱能将肉冻结起来很久不坏,大黄也从不捕杀超过自己消费需要外的猎物。后来村人发现了它存贮食物的秘密。
进入冬天,山村人就闲了起来,尤其是下雪的日子,只能围坐火塘拉些闲话,而闲话自然就会扯出大黄,它的一切尤其是那次毒打,都是打发时光的谈资,一些小孩则会外出,安装一些套子捕捉野鸡和画眉鸟,然后就用火烤了而食,味道很好。一天,也是六十二家那个和公鸡一样调皮、因矮小而号称地牯牛的男孩,突然间起了一个大早,本想去村边寻找其他人安装的套子,好偷取猎物,这在山里很正常,对于上山打猎,一直就有“见者有份”的说法。
地牯牛将手插在袖筒里,鼻子里挂着清鼻涕,走到村外一座小山坡上时,透过满天的雪,突然看见一团火从一丛树后闪了出来,惊得几乎喊叫出声,仔细一看,是大黄,嘴里还含着一大块东西。于是,等到它离开老鸦石,地牯牛才跑过去,从下面发现了一只草包子(不长麝香的獐子),就惊喜地带回家,傍晚,从他家里的天井上飘出的肉香就诱惑了整个村庄。
秘密随着一次次的肉香被暴露了出来,大黄也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明白了自己的食物何以不翼而飞。它想,人类也爱吃野食,好像在以前村人打到了猎物时,也听到过五斤等人说,“又有菜根子吃了”。它感到了那肯定是极好的东西。
于是,大黄觉得拿就拿吧,反正自己也吃不完,最多不过多跑一些山场而已,就在以往的基础上加大了捕捉的频率,一样将剩下的肉放在老鸦石下让村民来取。因争抢得凶,德高望重者就挺身而出,定了一个协议,大家轮流去取,每次三人,取了后大家平分,村人感到又有肉吃又能相安无事,也就很乐意地接受了。
这个过程持续了N个冬季,大黄在事情发生不久,就长了一个心眼,它觉得五斤分到的不一定是好肉,于是,只要捕捉了猎物,就先留下一条后腿,自己吃饱后将剩下的放在老鸦石下,然后将后腿含回家。但这却因五斤不参与分肉却能吃上最好的部分,又让村人有了些嫉妒和对大黄的不满。
但人们对大黄捕猎的本领还是认可的,特别是见证了它的威风之后。
那天,进入了又一个冬季的人们在太阳的温暖下,又齐聚在了村外一块堆放了玉米秆的地上,地较平,缓缓的坡伸向了坎的下边,人们躺在玉米秆上,享受得如神仙一样。时近中午,大黄突然从对面的山野里就将一只香獐从树后赶到了光溜溜的田里,位置正好在所有人的视线里。
其时,那只倒霉的香獐已被追赶得惊慌失措又精疲力竭,跑进田里本就是无奈与绝望的行为,它没命地跑,大黄在后面死死地追,但在一处田边,大黄却停了下来,让香獐吃了几口雪。然后在人们的困惑中,大黄突然跃起,就像一团火飞驰而去,大家感到那不是跳更不是跑,而是飞。香獐一惊,面对前面的高田坎只是迟缓了一下,已被咬住了喉咙,没有发出任何喊叫,就一缕香魂,飘零而去,到地府投胎转世变人或变狗去了。
村人一哄而起,朝了田边蛙跳而去,将香獐抢夺过来,除了肉,大家从那长长的牙齿感到了它还有一颗硕大的麝香,那可是管钱的,一出售,分了钱,过年就会丰富一些了。但他们太低估了大黄的智慧,就在争先恐后地抢獐子的时候,大黄已将麝香咬下,含在嘴里,跑回了五斤的家。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见者有份”只限于家门外,进了门,是谁家就是谁的了,所以大家迫不及待地将獐子放在地上,掰开两只后腿一看只有一个空空的血洞后,把脚顿得如发生了一次三级地震。对大黄则觉得它根本不是狗,而是一只狗仙,转而对自己那些只会吃屎的狗,咬牙切齿地恨了起来。
大黄的形象是在村人又恨又爱又对五斤充满嫉妒的复杂心情中慢慢树立起来的,特别是两件事。
一件事是有一年夏天,在高山牛场上放牧的牲畜突然受到了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大群豺狗的袭击。豺狗是一种猥琐的食肉动物,和狗本是一个祖宗,狗被驯化后,它们却越变越难看,捕猎时它们专门掏猎物的屁眼,这很要命。它们藏在草甸上的一丛蒿草或灌木后面,等待一心一意吃草的猎物靠近,然后将前爪闪电般伸出,用剃刀一样锋利的爪子将肛门里的肠子勾住,自己则稳定不动。负痛的猎物则在惊吓中拼命地逃跑,肠子就布带一样被拉出来,然后迅速倒地身亡。
它们猎杀的对象主要是家畜。
很多牲畜的死亡便引起了村人的恐慌,大家就赶着自己那些狗上山,并用明火枪协助,但豺狗哪里会把人和那些狗放在眼里,见人上山就躲藏起来,如果人狗分离,就突然袭击,把那些离开大门三尺就在无人势可占的情况下,夹了尾巴逃跑的狗教训得鬼哭狼嚎,不要说赶豺狗,就是听到叫声,也像得了狂犬病一样吓得将尾巴也夹在了肚子下。
那些时候,大黄依旧在山野的青翠与花的艳丽中悠然自得地生活,它在春夏秋都不会捕猎给村人食用,它觉得祖先留下的习惯一定有它们的道理,动物春要繁殖、夏要成长,秋要长膘,如果只是想到捕杀,到某一天,也就绝了,而对于狗,尤其是一条不吃屎的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呢!”它要做的就只是满足自己的胃,其余的时间则卧在草丛与树阴下用最舒服的方式思想,并渴望着像好老妈一样的艳遇,因为村里那些女狗它一只都不放在眼里。
豺狗的袭击让村里乱哄哄地失去了宁静,人们除了叹息就无可奈何,大黄从人们焦虑的神色和五斤与别人的交谈中知道了事件的真相后已有好几天时间,它在一旁卧着,一幅与世无争的样子,心里却想:“不就几只豺狗吗”。
第二天,山村还处在朦胧的曙色中时,大黄走上了通向牛场的路。
路是随山梁而走的,从村头出去,绕过一座小山,穿越森林和灌木,就是一望无际的高山草甸了,它们位于树和山峰裸露的岩石之间,广袤无限,放在其中的牲畜分散在绿色的画面上,就如宇宙中的几颗星。
大黄是悄悄地接近那些牛群的,它怕让处于惊弓之鸟的牛们受到惊吓,就藏在不远的地方,居高临下地一边欣赏风景,一边观察动静。到了黄昏,一只豺狗才慢腾腾梭了出来,朝一头有些笨重的牛靠近。大黄立即将思绪收回,只一秒时间就进入了战斗状态,它将山坡上黑色的肥土撒在身上,将脚半跪着在草丛中向豺狗运动而去。
当时,山里已有了风,草倒伏下去又伸直起来,就如一群人在整齐地做广播体操中的弯腰动作,那只豺狗也就在草弯腰时看见了它。但是,经过了伪装的大黄看起来已像一只豺狗,所以就被那只豺狗视为同类,便只管注意那牛和寻找下爪的机会,以至于大黄接近时,那豺狗还不知已大祸临头了。就在它发现来者是同宗而不是同门想逃跑的瞬间,喉咙已被咬断,它将腿不停地收缩,在草甸上挖出了两条沟,就呜呼哀哉了!
事情做得狗不知豺不觉,方法被大黄重复了几天,一只只豺狗被抛在山崖上又被老鹰带到了遥远的窝里。
十来天后,经过侦察,大黄觉得豺狗比预计的还多,而自己的方法已被对手察觉,成功率正在降低。它想,得有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干脆就以其豺之道来治其豺之身。一天,它将一只豺捉住后并不咬死,由它嘶声哇气地叫,然后,用前爪死死按住它的头,咬开屁股,将一截肠子抓出,钉在一根倒勾刺上,然后将那痛苦的豺狗放开,一跑,肠子就被拉完了,因为大黄知道,豺狗虽然也是犬科,有七条命,但却只有一根肠子,它听到过人们总是说它们“一根肠子通屁眼儿”。
相同的惩罚只进行了几天,豺狗们已被吓得魂飞魄散,它们觉得祖先的本领是传内不传外的,现在被一只狗学会了,并用它来收拾自己,面对的肯定是灭顶之灾,就在一天夜晚,像来时一样幽灵般消失在了茫茫的群山深处。
几天后,村人才惊喜地发现豺狗的消失,同时,心里又非常困惑,就上山寻找原因,他们在畜群活动的地方除了发现一根又一根挂在倒勾刺上已被风干的肠子和一些豺狗的骨架外,一无所获,心里却滋生了新的恐惧,因为神秘总是让人害怕的。直到一天,一个从山后来走亲戚的人才将大黄收拾豺狗的经过讲了出来,他说:“那天我在山里寻找虫草,亲眼看见的,还以为活见了鬼”!
于是,村人对大黄就有了些敬畏,偶尔遇见了会主动让在路边,并打招呼说:“崽”!
第二件事是大黄在一天救了它的仇人六十二的命。
因为六十二家的鸡和他的不依不饶而几乎丧命的大黄,对那件事一直记恨在心,但却没有想过报复,它觉得狗的美德有两种,一是不嫌家贫,二是知恩图报,还没有听说有对人类报仇的狗,除非他要自己的命,在知道了是地牯牛偷走了它的草包子后,也没有伏击过他。
六十二出事是在临近春节的时候,他和山村人一样只能是山村人,只是多了些心计,如将五斤的
人弄到了手,又制造了让两人不来往的矛盾。但毕竟还得按千年的习惯生活,村庄里的人都是劳累的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然规律,因山高路远,这里没有电,照明的工具是油灯或者松光,为了节约点灯的油,人们就会在天黑时上床睡觉。六十二也一样,和别人不同的是,和他一起日落而息的还有他的老婆,睡早了便不会很快入睡,不能很快入睡就会与婆娘发生许多事故,后果则是他家有了地牯牛一、二、三、四、五、六。娃多了就更加贫穷,这也是他在乎一只下蛋鸡的原因。
对于这些,六十二感到很正常,“儿多享福”。但要将那些张口货养育到让自己“享福”的时候,压力就山一样大,虽说山村人一贯是贱生薄养,只要能养活就是一切,但毕竟过年总得有一身新衣服吧!
六十二越到春节也就越心慌,他很长时间在大山里踩着吱吱乱叫的雪,安装了无数套子,本想抓住一只香獐,让一家人过个好年。但是,香獐只有像大黄那样的狗或者会些法术的猎人才能获得,因为它们集了天地间的灵气,能感知很多东西,据说,它们还会在被套子套住时,变成一只草鞋,等到人将它取下一丢,立即又变成香獐逃走,特别是麝香长到八两时,已是宝贝,又有了“七香八宝”之说,而带有八两麝香的香獐有时还会变成美女。
六十二每天无功而返,只收获了呼呼的北风。
农历腊月二十八,离大年三十还有两天,六十二再也没有办法了,清早起来,穿上一双羊毛袜子,套上草鞋,就怀着悲壮的心情走出家门,向村下遍地白雪和覆盖了冰凌的小河对面的大山走去。
山是阴山,冬天的第一场雪下来后便不会融化,随后就不断堆积,直到第二年春才开始消融,积雪往往一米多厚,是村人眼中的禁区,他听说有人看见从悬崖绝壁上摔下了几头野牛后,就一直想去寻找,那会有很多肉,能换到卖衣服的钱。
六十二如赌徒一样出发的时候,村里没有人知道,但被大黄发现了,它当时正在村边一棵花红树下撒尿,看见了六十二在大雪上歪歪斜斜地挪动,就有些奇怪,它想,他要干什么,那是连狗都很少走的路,就一直望着。见他在雪地上像一个侏儒般挪进隐藏在树林里的路后,才大略知道了他的目的,并凭本能预感到了将会有事情发生,就悄悄地尾随在后。
六十二义无反顾地挪进林中,又义无反顾地用两根棍子撑在身后,将羊皮褂子垫在屁股下,坐在一道直直地通向山脚的沟朝里,像滑板运动员般滑到了小河边,又从冰面上跟斗扑爬地扑进了对面的山脚。
随后,他向上爬去,到了半山腰一片较平缓的林中时,雪更厚了,几乎没入他的双腿,看上去就像一个半截人。缓坡的上边,就是笔直的悬崖,像是插在地上一样,野牛可能就是从山顶上的草甸边摔下来的,他找了许久,一无所得。此时已是正午,太阳正闪过树梢,六十二又冷又饿,看见不远处一座高高突起又伸向北边的山坡,因为和沟壑相比就多了些阳光,雪化后只剩下枯萎的草和光叉叉的树,就想,得上去晒一下太阳,把烧馍吃了,然后观察一下再继续寻找,就向坡顶爬去。
坡顶有点像一口倒扣的平底锅,下面望不到上面的情况,所以,六十二吃力地爬上“锅底”时,突然就如钉子一样地钉在了一根树干的旁边。
因为一头被称为铜钱花的豹子正在上面晒太阳。
只是瞬间,豹子发现有人竟敢侵犯自己的领地,就猛扑上来,将魂飞魄散的六十二按在地上,想一口咬住他的喉咙。这时,六十二已回过了神,凭借本能爆发了从未有过的力气,就用两手抓住豹子的两只前爪,用头顶住豹子的脖子,在几平方米的地上惊心动魄地打了起来,豹子一见无法咬住喉咙,就转动着灵活的头颅朝他的全身乱啃,只几分钟,六十二就已体力不支,准备束手待毙了。
这时,大黄猛扑上去,将豹子的耳朵咬了下来,又咬住它的后腿,用驴一样的身体向后拖去。豹子一惊,见来者是比自己还高大的狗,又有人,如果单打独斗它并不害怕,自己毕竟在猛兽中被排列为“头猪二熊三老虎四豹子”中的老四,而狗是没有名次的,但人狗联手可就不一样了,它想起在活过的很多年中,就吃过不少人狗协作的亏,于是,丢开六十二,反爪给了大黄一巴掌,一溜烟跑向了坡下的森林。
六十二看见是大黄救了他,就有些神魂颠倒,想招呼一声以示感谢,却开不了口,想站立起来又全身无力,浑身疼痛难忍,像被人抽去了全身的筋。大黄本想去追赶一下豹子,但见六十二老是爬不起来,就转身用嘴将他系在腰间的麻布带子咬住,连拖带拉地朝坡下的河边走去。
当拖着六十二半步一步地到达村里目光所及的最后一道山梁时,大黄看见有人在村里的房顶上张望,就将六十二放下,大声叫喊起来,村人见了,因已知道了六十二的冒险,就一窝蜂似地跑了下去,将他背进了家里。
人们于是烧起冲天的大火,让六十二躺在一张老熊皮上,先用雪对全身进行搓揉,后又改用白酒。这时人们才发现他并没有伤口,只是全身除了头部,都是青包,便觉得奇怪。一位老人说,山里是有一只豹子,但应该很老了。人们一想,才觉得那只豹子确实该老了,因为发现它在山里活动已有几十年,看见六十二的伤势,听了他对经过的介绍,大家才明白原来那只豹子己老得掉光了牙齿,乱啃了一气,却只给六十二留下了无数青包。
但人们还是觉得是大黄救了他的命,否则他必定会被啃死。
此后,大黄就在村里树立了神秘和让人更加敬畏的形象,人们总想以某种方式亲近它,同时表达一下毒打事件中推波助澜的歉意。但大黄不管这些,仍然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直到把自己弄成了异类。
被村人视为异类或者怪物的原因是山驴狠狠地踢出的一只老蹄子。
又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猛,大朵地飘舞下来,就如扬筛时飞翔的玉米屑,村人都蜷缩在自己的火塘边,前胸烤得起了干壳,后背则冷得发凉,风不断从山上下来,又从山下上来,或者横着来回地走,没有规律,有时将雪旋转起来,形成的雪柱直冲云天,人们就会感到害怕,骂:“妖风”,呸地吐一口口水以示没有惹上它。
大黄就是在一股妖风中出发的,它超狗的嗅觉感到了有一只猎物就在村后不远的山里,于是追踪而去,从村人砍柴的小路跑到一块岩石上时,就看见了一头硕大的山驴正在林中的一块荒地上踏雪寻草,大黄隐蔽前行,在认为合适的范围内发起了进攻。
山驴是一种中型的野物,比家养的驴子要强许多,见了大黄猛烈地扑面而来,一纵就跳上了一个很高的土坎,疯了一样地向高山上逃去。但驴毕竟不是马,跑的速度较慢,很快就被大黄逼上了一处绝境。
那是一座山梁,从大山的主体中突然向外伸出,一条小路通向顶端后除了原路可以返回就已无路可走,山驴跑上去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但大黄己封住了退路,于是回头和它对峙,就形成了驴狗的相持状态。
这样的结局一直被村里人称为“关”,听见狗老是在一个地方叫,而且很凶,就说,有东西被关了,接下来就是带上明火枪,赶到猎物被困的地方,
举枪将无路可逃的猎物击毙,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所以,当村里一名枪手赶到,看见被关的是一只山驴的时候,就有些大喜过望,他发现一是那个地方被称为三绝岩,猎物根本没法逃走,二是山驴很大,是头成年的公驴,肥得油光水滑。于是枪手在与岩顶平行的地方找了一个位置,举起了百发百中的枪,他认为只一炮就行了,于是,装上引火炮,扣板机,轰隆一声,枪口就冒出了一股烟幕,有点像小小的平射的蘑菇云。
枪响过后,却没有看见山驴倒下或者滚落岩下,而是鱼死网破般地冲向了大黄,在慌乱中,大黄就被飞起的后蹄踢中了头部,当即翻滚到了路边的一丛灌木上。
枪手目瞪口呆,他才想起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枪里只有铁砂,忘了装填独弹,威力只能打死一只野鸡,细小的砂粒钻进山驴的皮,只能引发痛疼与愤怒而不会致命,这就使受了皮外伤的山驴怒火中烧,来了个“驴急跳墙”,让大黄吃了苦头。
而这一踢就造成了严重后果,大黄先是眼冒金星,后又晃晃悠悠地好似不是自己,等到恢复了元气,返回五斤家的时候,就有了特别的感觉。
感觉是走到一块平缓的田里时,它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像人一样行走,就将两只前腿抬起,后腿踏在地上,摇摆着如初学走路的幼儿般走了起来。
此后,大黄就感到了直立行走有很多趣味,在行走中个子能与人一般高甚至比六十二高。在老鸦石和五斤家的那段弯曲的小路上,村人就目睹了它的怪异,每一个第一次看见的人都被吓得呼爹唤娘,加上山后出现了一桩人命事故,谣传说那人是凶死,魂没有归依,已开始在四处奔波,大黄可能就是被附体了,各种猜测传开,人就自己吓着了自己,天黑便不敢出门,在拉起相关话题时,坐在外边的就要朝里面挤,挤不进的总是不断回头向大门口张望,并感到毛根子都立了起来。
大黄则认为很正常,走路有多种方式,对村人的大惊小怪不可理解,就我行我素地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它觉得面对的生灵其实都很不幸,而且不公平,就说人吧!能主宰动物却主宰不了自己,忙乱地活,还有那么多的是非和烦恼,就如六十二,一直都在为生计操劳却还是在贫穷中过着,惟一的快乐可能就是和婆娘的那点事了。它想,人有时还真的不如狗,自己能像人一样地走,也可以像狗一样地爬,而且除多了点人的思考外,并没有丢失狗性,就将头靠在前肢上,眼一闭,对着南面的山,在阳光下修身养息了起来。
第二年夏天,雨水出奇地多,人们看见地里的庄稼因缺少阳光而白嫩得像剥了皮的竹笋,就急得要命,寻不到食物的野猪又成群结队地到来,把地里的土豆翻腾得一塌糊涂。
这便惊动了上级,山村虽小,仍有自己的领导。
上级是大队派来的一位民兵连长,叫二骡子,那时,一个大队的民兵连长手里掌握着武装,每个大队都有基干民兵,每个基干民兵手里都有一支三八式步枪用于对四类分子进行专政。当然,也在专政之外用来打猎改善生活。
伟人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就威风,民兵连长二骡子便成了村民眼里的上级,都以能请他到家里为光荣,一些地主富农见了则会堆上一脸的笑,久了,二骡子便有了很良好的感觉。
二骡子到山村首先就遇见了大黄,它在村外一段长了蒿草的路旁立着,见有人来,就藏在一丛野花椒树后,当二骡子背了枪走近时,就像人搞恶作剧一样,将嘴对着他的耳朵,“汪”地一声大叫,将二骡子一下子就惊得三魂七魄乱飞,向外本能地一跳,脚下踩空,就滚到了路坎下的地里,在伸出手想抓住什么时,又握了一把花椒刺,倒栽葱般杵在地上痛得惊叫唤。大黄却没事一样,人模狗样地沿着两边都是毛草的路,悠然自得地走去,转身消失在了弯道的后面。
一开始,大黄就被二骡子怀着了恨。
二骡子住在一户老贫农家里,这和山外有区别,山村毕竟是山村,有些山高皇帝远,尾巴割得并不凶,村人年年都能吃上饱饭,还有野物肉强壮身体,二骡子所住的那家除了号称贫农,其实有的是饭吃。贫农离五斤家不远,就隔了一块大石包,二骡子很快就知道了大黄是五斤养的,而且很怪异,每次看见它立着走过,就惊得不行,全身软兮兮的,越想除掉它。
但他知道狗在山里人心中的分量,不敢动手,就先展开了对野猪的专政,和村里有经验的人一起,经过观察,发现了野猪出没时有一条必经之路,就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二骡子提前藏在那条路的一块岩石后面,用枪对着前面悬挂在崖壁间的小道,然后,村人就带着狗一起吆喝起来,将野猪赶往他等待的地方,野猪一露面,二骡子就扣动扳机,三八大盖里钻出的子弹就会将一头野猪的腰打断或者头打破。
这种狩猎方法往往十分奏效。几个月后,野猪之害就基本消除了。
那段时间,村里就天天都吃上了肉,因为天热不能放久,便天天煮,满村子都飘满了肉香,大家也就对二骡子更加地尊敬,觉得他就是干了坏事也可以不计较了。
二骡子便越发春风得意起来。
当然,二骡子还有一个阴谋,就是想在打野猪时以误伤或者以枪走火为借口将大黄打死,但大黄知道这些,从不参与对野猪的追赶。他的阴谋不能得逞,就变成了心事。
野猪被杀死或跑了之后,二骡子便有些寂寞起来,几个月的好生活让他的身体更加强壮,又有枪助威,就想做出一点事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他突然觉得山村里的阶级斗争烈火没有燃烧起来,有一天,就把对野猪的专政变成了对人的专政。
专政的方法是带着娱乐性的,不如山外整得厉害。到了天黑,他就将村里本来就在数量上形不成人气的村民招集在村里一座用来做保管室的房子里,点上惟一的马灯,将村里两家四类分子翻来覆去地斗,过程几乎一样,他站在一条板凳的旁边,先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听的人则在下面交头接耳。然后,就喊将斗争对象带上来,被斗者就在自己的侄辈们象征性的押解下走上板凳。这时,二骡子就振臂高呼口号,但本应紧跟的人却没有声音,大家将手举起,却软绵地笑弯了腰,随后,连被批斗者也走下了板凳,大家围在一起,摆条拉家常,只是每一次都离不了大黄的话题,每一次又都会增加二骡子的恨和恐惧。
一天,他终于找到了处置大黄的借口,当时,大黄正人一样走在地里,随口就将一只玉米棒掰了下来,二骡子一见,就大喊:“大黄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立即拿出了枪和全部子弹,欲置大黄于死地而后快。
大黄听见叫声,回头,发现二骡子拿着枪,就知道要和自己过不去了,便恢复了狗的姿态,朝前方一处山梁风一样跑去。
山梁不远,只两百米,和二骡子的位置相对应,大黄停在一棵松树的旁边,转身,立起来,向他做了几个调戏的动作,把二骡子气得怒火中烧,就举了枪,抬手就是一炮,大黄见他举枪,就闪在树后,子弹便“日”一声,或者打在树上,或者从树边飞走了。枪响过后,大黄又闪出来,立着像一块靶子,二骡子枪一举,它又闪回树后,如此反复,二骡子在人们的注视下很快就将剩下
的十九颗半子弹打出了十九颗,剩下的半颗因是哑弹得名,他自我解嘲说:“留下镇枪”。就将它压进枪膛,转身走进贫农家罩挂在了一根柱头上。
躲过了子弹的大黄知道了二骡子原来是想弄死自己,便生了狗恨,它想,狗族是只报恩的,但也不能欺狗太甚,急了还要跳墙呢!一定要认真收拾他一下。
没有了枪,就少了肉吃,只有大黄除外。
这让二骡子很不自在,他又不想回家,因山村比山外好过,“乐不思蜀”是人之常情,就在临近丰收的时候又想出了一个鬼主意。
主意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他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在村里村外转悠,发现村民们家里养的鸡和猪,数量都超出了标准,于是召集大家宣布了规定的数量,多出部分一律割掉,这又解决了一个吃肉的问题,就一家一户地割,但多出的部分不销毁,拉出来杀了,大家吃肉,吃完了再割第二家的。
如此,山村又持续了一个月的好生活。
二骡子无所事事,就对贫农家一位好看的女子打起了主意,她叫三花,健康又充满野性,在第一次见到三花时,二骡子就有了想法,只是当初并不打算动真的。现在,他被割下的“尾巴”养得精力旺盛,人又有“饱暖思淫欲”的德性,就利用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大好时机,调动了带领民兵的战术,天天调情。有一天,二骡子比较轻易地就将在一棵野杨柳树下采猪草的三花,连哄带骗加威胁利诱地弄到了手。
事情一发生,就成了自然,于是,二骡子就会三天两头和三花在老地方行那不轨之事。
在他们认为人不知狗不觉时,大黄却知道了。
一天,两人又在秋天被阳光照亮的风景中,第N次走向了相约的地方,大黄看见后就想到了收拾他的办法,便尾随其后,走了一段路又绕道从另一个地方提前赶到了那里,在铁衫树粗大的树杆下隐藏起来。
不久,二骡子和三花也到了,就在树后的野杨树下继续曾经的故事,将身上的附属物全部顺手挂在了树杆支出的一截枯枝上,便忘乎所以了起来。
大黄见状,从容地从树杆下钻出,将所有的衣物抱住,跑到了老鸦石上狂吠起来。
事情就败露了出来,村人大惊,那贫农更是无地自容,要知道那是伤风败俗的事,就在大黄的引领下抓了现行。三花见状,硬说是二骡子用枪逼的,她说:“谁不怕,那半颗子弹说不定就响了”。
二骡子随之被告到了山外,上级一听,这还了得,对准阶级敌人的枪不但用来对准了贫下中农的女子,还做了和资产阶级一样腐朽的事。便派了两个民兵也就是二骡子的部下,将他灰塌塌地押解到了大队,又被大队押解到了公社,后又被押解到了县革委,就判了刑。
这一切大黄当然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后果如此严重,只是觉得二骡子不见了,同时感到少了对手也少了乐趣。
农历八月十五,大黄突然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而且很惨,就对着月亮升起的山崖大哭,呜呜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它一直哭下去,直到月光又像扫帚一样从东南的山脚扫向山顶,才走进了老鸦石下边的岩窝里进入了沉思的状态……
随后,山村便进入了“烂九黄”的日子,雨不停地下,到处都在起水,村里惟一的小溪浑浊得无法使用后,就只能在很远的一处岩石下接浸出的凉水。
一天,五斤一大早就趁雨稍停的时候,走出门,肩上斜挎了那杆明火枪,他想利用野鸡翅膀被雨打湿飞不远的时机,猎取一两只,他经常这么做。走到村外的一道山沟时,周围依旧静得出奇,他将枪依靠在一棵树的枝条上,认真地用嘴接饮那股像筷子一样细的凉水。这时,积累了足够能量的小水突然发威,岩上的泥土塌陷下来,又被涌出的大水冲动,就形成了泥石流,瞬间就将五斤裹向了山下。
同时,山村后边的一座土包下滑,将村庄也带向了山下的小河里。
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大黄正在老鸦石下沉思,它在午后走出,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沿着泥石流冲过的痕迹,一路找去,终于寻出了五斤留在世间的一只手,便用嘴含到老鸦石,在旁边挖了一个坑,埋了起来。
然后,它转过身,沿着通向牛场的小路,跑向了西边的山峰,在翻越时,站在一处可以望见山下那个它生活过的地方的梁子上,回头望了一眼,又转身面向西边,奔向了那座矗立在天际间的雪山深处……
作者创作简历
梦非,男,羌族,1965年3月生,四川省汶川县人,现供职于茂县地方志办公室。
1986年开始文学创作,体裁以诗歌散文为主,至今已分别在《民族文学》、《四川文学》和《青年作家》、《草地》、《阿坝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约200余篇,出版有诗集《淡蓝色的相思草》,旅游文化散文集《相约羌寨》和羌族旅游文化图文集《人文羌地》。组织发起成立“茂县羌族文学社”并推动活动卓有成效地开展。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文学感言:
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一只“鸡肋”,写作时觉得自己需要写,怀疑时感觉无路可去,就这么坚持下来后,太阳仍在升起,雨仍在落下,自己却已不是原来的自己。总之,写作是心路的历程,所有感悟都在结果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