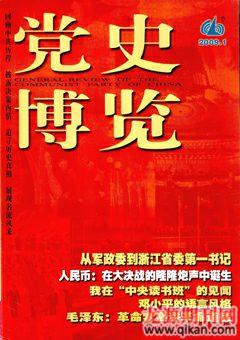亲历板门店停战谈判
杨冠群
1950年11月,笔者穿上了军服,由外交部干部转换角色成了军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夙愿终于实现,但却是去参加停战谈判的。在朝鲜三年半的时间里,历尽风险,有幸见证了板门店停战谈判的全过程。
西方记者报道说,当天的会议“时间必长、内容必多”,根据竟是中方记录人员进帐篷时挟了厚厚的一叠记录纸
1950年7月11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在朝鲜故都开城举行,11月25日起移至板门店。谈判伊始,就陷入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中间打打谈谈,10月27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了协议。1952年5月,双方又解决了停战监督和战后限制朝鲜境内军事设施等问题。但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严重僵持,谈判已徒有形式。
1952年11月8日,双方谈判代表来到板门店。双方代表坐定后,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按照老一套先问我方对其9月28日提出的坚持“自愿遣返”的方案有何想法。我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不予接受。于是,这个瘦小的、面带杀气的美国将军宣布“无限期休会”,且不等我方作出反应即起身朝帐篷外走。我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了我们的蔑视,直到对方全部人员撤走后才离开帐篷。
板门店是中立的会场区,本应得到双方的尊重和维护,但傲慢、无信的美方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多次炮击会场区,派特务渗透,更多的是派飞机侵入会场区。谈判破裂期间,美机更是肆无忌惮地侵犯会场区的中立地位。那时,美机经常低空飞越会场区上空,对周围我方阵地轰炸、扫射,站在会场区内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为此,双方安全军官频繁地在出事地点会晤,进行联合调查,以确定事实真相,但每次美方都赖得一干二净。他们的借口是:飞机在上空飞行,站在会场区内用肉眼观察,总是感觉飞越了头顶,其实飞机都是在会场区外的上空活动,充其量不过是擦边而过,不构成违反协议。美国军官甚至挑衅地提出,要我方用其他方法证明飞机确实飞越了会场区上空。
面对美方的挑衅,朝、中安全军官进行了深入讨论,想了很多方案。不久,又发生了美机侵犯会场区上空事件。我方要求双方安全军官立即会晤。双方军官先在会场区中心的帐篷外集合,然后一起步行到出事地点。
双方开始调查,我军事警察陈述事件经过:“我们两人在会场区内巡逻,走到这里,突然一架美军P-50型战斗机俯冲下来,低飞掠过会场区上空,飞向北去,攻击我方阵地。”
双手叉腰、若无其事的美方安全军官故伎重演,问我军事警察:“你怎么能肯定飞机飞越了会场区上空,而不是在会场区外?”
这一次,我军事警察斩钉截铁地回答:“当时我仰起头来,飞机就在我头顶,和我身体成一垂直线。我立得笔直,同地面形成九十度角,因此,我敢肯定它侵入了会场区上空。”
按照几何学的原理,我军事警察的论证完全正确。美方安全军官没有思想准备,支支吾吾,对这一论证不知如何反驳,耸了耸肩,认可我方的作证,并表示要向上级报告。
1953年2月,美军司令员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俘。中央认为这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变立场的试探性行动,指示我谈判代表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以后不要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
休会期间,板门店十分冷清,只有双方军事警察的身影。但一旦遇有会议,会场区便顿时热闹起来,车水马龙,夹杂着直升机的轰鸣声。帐篷外的公路上熙熙攘攘,双方记者交头接耳,互换信息。有的干脆就蹲在路旁写起新闻稿来。根据协议,记者不能进入会议帐篷,于是谈判代表进出帐篷时便是他们抢镜头的珍贵时刻。代表们的衣着、举止、神态,以及使用的交通工具等都是新闻资料。有时,连我们工作人员也成为揣测观察的对象。一次,一位西方记者报道说,当天的会议“时间必长、内容必多”,根据竟是中方记录人员进帐篷时挟了厚厚的一叠记录纸。
美军少将师长威·迪安在被遣返时说:“我被俘时估计是130磅,被遣返时为180磅。”
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为了迎接我方战俘,工作人员在会场区我方控制一侧搭起了一座高大的彩门,用朝、中文写上“祖国怀抱”。彩门上的国旗和彩旗,在春风中凌空飞舞。
上午9时,首先到达的是朝鲜人民军的伤病俘。这些朝鲜人民的忠实儿女,进入板门店会场区时一路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振臂高呼口号,并开始从汽车上扔掉美军发给的一切物品。用西方作家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便是:“车队经过后,停战后的遣返工作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之一是:延伸了几英里,空荡荡的公路上铺满了被扔掉的士兵工作服和靴子。”
等他们到达会场区中心时,每个归来的人民军战士身上只剩一条短裤,但头上都戴有一顶自制的人民军军帽,又从军帽里取出秘藏的布片,拼出朝、中两国国旗及“朝中友谊万岁”的标语来。
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当志愿军伤病俘回到会场区时,却见不到那种激昂的情景。开始时,我们感到不解。后来,到休息帐篷里探视他们,见他们哭成一团,纷纷脱去上衣,露出被强迫刺上的侮辱性词句——“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及控诉遭受的残酷迫害时,我们才明白志愿军被俘人员比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残。
下面,让我们比一比双方被俘人员所受的待遇吧:
美方被俘人员中军衔最高的是第二十四师少将师长威·迪安。这位美国少将于1950年8月被朝鲜人民军俘获。美军曾报告他已以身殉职,并授予他代表美国最高荣誉的“国会荣誉勋章”。不料,他竟在平壤附近的战俘营中度过三个春秋。在战俘营中,他可以进行体育锻炼,给亲属写信,还写了一本《在朝鲜被俘历险记》,回国后出版。1953年8月5日,迪安被遣返。遣返的前一夜,我方有关领导设便宴为他饯行。他对记者说:“我被俘时估计是130磅,被遣返时为180磅。”
我方被俘人员的最高军职是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1953年8月04日,美方宣布志愿军被俘人员已遣送完毕。在我点名要人之后,美方才于9月6日将吴成德等138人遣返。志愿军代表团的领导人之一杜平当时曾前往接收站迎接,后来他写道:“吴成德当时实际年龄不过三十几岁,可是由于美方非人的虐待,头发脱落了一半,脚上穿一双补丁摞补丁的解放鞋。在敌人长期秘密囚禁期间,他坚决拒绝穿敌人的皮靴,始终穿着这双祖国的鞋子。美、蒋特务曾在单独关押他的牢房里安装了两个高音喇叭,每天在喇叭里喊叫:‘吴成德快交代。弄得他白天黑夜不得安睡,受尽了折磨。孙振冠等人也是面色憔悴,骨瘦如柴。”
谈判耗时两年零十七天,签订停战协定仅用了十分钟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签字的全过程仅有十分钟,在长达两年零十七天马拉松式的谈判中,它的确只是短暂的片刻。
上午9时50分,双方的观礼代表和工作人员开始就座。志愿军的观礼代表来自志愿军司令部和前线各军,共约30人。所有出席的人员都空着手,唯有冀朝铸和我各带了一个纸夹,准备万一美国代表发表讲话或双方参谋交谈时,就上前作笔录。这是两年谈判中我们英文速记人员的职责。当时,我方决定“以不致词为原则,若对方一定要讲,我方应准备讲稿”。我们两人有备而来,但哈里逊一言不发,我俩便只好作壁上观了。
签字大厅呈“品”字形,南北长,东西短。大厅南北各开一门,供双方代表团各自进出之用。双方人员分南北两边面向而坐。谈判代表的席位居前排,其他观礼人员居后排。凸出的部分是记者席,正好面对签字桌。过去谈判时,一张长桌当分界线,把双方隔开。今天则不然,双方之间是一块空旷的场地。东端面北设小方桌一张,放着18本待签字的停战协议文本。小桌两侧又各放一张长方桌,上面分别置有朝鲜国旗和联合国旗帜,是双方代表签字的座位。大厅可容纳2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虽然来宾不少,但大厅仍显得宽敞明亮。
11时整,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步入大厅。我方人员正襟危坐,宛如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对方人员则是千姿百态,有歪着身体的,有跷起二郎腿的,有伸直了脖子的。两位首席代表就座后,便在双方参谋的协助下先在本方准备的9个文本上签字,然后进行交换,再在对方的文本上签字。这一过程共历时十分钟。记者席上一片按快门声和镁光的闪亮。“大功告成”之后,两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然后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
一名记者以特有的职业敏感报道说:“哈里逊向记者席瞥了一眼,挤出一丝勉强的微笑,与南日同时起身离开。两人目光交遇一下,又赶紧避开,分别同本方人员退出了大厅。”
十分钟的仪式似乎过短。中国外交部的有关部门事前按照常规,曾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计划,但在请示过程中,关于“中国外长在北京举行招待会”的建议即被否定。周恩来指出:“外交部的签字计划,似过于宏大,与目前这个停战的实质不尽相符……签字仪式中的进门就互相握手和碰杯应以不要为好。”停战只是战斗的终止,并不意味朝鲜半岛和平的到来。这就是实质。50多年过去了,以和平条约代替停战协定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板门店停战谈判创造了两项历史纪录: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停战谈判和持续最久的武装休战。时至今日,一条240公里长、4公里宽的非军事区仍腰斩着朝鲜半岛,将这个民族一分为二。
李奇微要求美方代表团人员“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李克农要求我方人员注意“察言观色”
停战谈判的结果关系到重大利益,因此双方都选派精兵强将组成谈判班子。根据协议,交战双方的谈判代表团各由一名首席代表及四名代表组成。
谈判开始前,“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先是指定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为首席代表,接着又推荐乔埃的副参谋长勃克少将、远东军空军司令克雷奇少将、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及南韩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为代表。此外,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李奇微总部抽调一批人马组成该班子的智囊团。
金日成指派了朝方的首席代表南日、代表李相朝和张平山,以及与我方联系的首席联络官张春山等。中方的谈判班子主要由北京方面(外交部、新华社、中央机要局)和志愿军司令部组成。周恩来提名李克农及乔冠华统领这支队伍。志愿军司令部派出了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参与谈判。我驻朝鲜使馆派出柴成文为中方联络官。乔冠华还从外交部带来了一批写作、外语、新闻干事。朝、中两支力量合在一起,组成了“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根据两国高层的协议,联合代表团由李克农领导。
李克农坐镇开城,但重大决策都是北京和平壤作出的。这里,尤其要提到周恩来发挥的作用。《周恩来传》中这样写道:“随着边谈边打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同志就同时担负起这双重的任务。那时,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应、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
战场上还在厮杀,谈判帐篷里就不可能有平和的气氛。板门店停战谈判名为军事外交谈判,却没有半点外交氛围:进帐篷时双方各走各的门;代表见面时互不理睬,更没有握手、寒暄的礼节;开会时,有话就说,无话就散;中途休息时,各去各的休息帐篷;连厕所也是各修各的,以免混杂。
这是对等的双边谈判,不设主席,遇事协商解决,双方都有否决权。有时,要抢先发言,比如开城首次会谈,就是乔埃抢了先。谈判进入僵持阶段,双方都“无话可说”,多说一句或先说一句,好像就是示弱。因此才有美国将军霍治提出的“用抛硬币的办法”决定谁先走一步以打破僵局的笑话。开城首次谈判时,双方首席代表还交换过授权证书,后来换代表都不通知对方,会上也不作介绍。代表席位上出现了新面孔,你就知道换人了,姓甚名谁、哪国人(后来也有英国人、泰国人为代表),就只好看新闻报道了。
这种谈判史无前例。双方对陌生的对手心中无数,因此交手时都格外小心。李奇微要求美方代表团人员“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而李克农也要求我方人员“注意观察会场上的每一个细节,察言观色,争取较快摸透对方的脾气”。例如:乔埃初到开城时,朝中人员向他敬礼,他还礼时却紧绷着脸,漫不经心;哈里逊讲“我同意休会”前,也要写条子经内部传阅同意;美方朝语翻译恩德伍德工作时,每吸一支烟都要在日记本上记上一笔;苍蝇在李相朝的脸上爬动,但他仍正襟危坐,纹丝不动;南韩联络官李树荣就座时一屁股坐到地上,只有中方联络官柴成文哈哈大笑……这些细节都被对方注意到,有的还写进了后来的回忆录中。
李克农说:“我不担心哪些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挑逗而冲动。”
谈判开始时,志愿军派出的代表是邓华和解方,后来先后有边章五、丁国钰、柴成文等参与其中。
邓华,1928年参加红军。1938年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曾参加辽沈、平津战役。担任四野十五兵团司令员时率部解放广州和海南岛。组成志愿军时,他是十三兵团司令员,后任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提名邓华时,邓曾以对外交不熟悉为由推辞,“看得出他心里不是很乐意”。但是军令如山,他后来还是接受了。在开城期间,邓继续关注战局的变化,提出“敌方深沟高堡,固守以待,进行阵地攻坚战,对我不利”。彭德怀事后曾多次表示,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些好主意,是个好帮手。0950年00月,边章五接替了邓华。卸任后谈起参加谈判之事,邓华气犹未消,说:“我宁愿在战场上与之见高低,也不愿去干谈判这种差事。”显然,驰骋战场的军人,受不了谈判桌上有时还需屈尊俯就的窝囊气。
解方,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东北军的师参谋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达延安,先后任军委情报部局长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兵团参谋长。解方被认为是“我军难得的既富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曾和解方直接打过交道的美国代表藤纳评论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担任其英文翻译的外交部官员称他“能言善辩,有很高的军事外交水平”。1953年4月,解方离开代表团。之前,李克农曾考虑让他出任停战后的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但他要求“解放”,志愿在国防军事工作上做些建设性工作,并已向志愿军司令部党委正式报告。为此,李克农表示:“他既然有此要求,也不必过于勉强了。如有适当人选接替,让解方仍在军事上去发展或让其参加志愿军军事总结工作是有好处的。”
边章五,1900年生,河北辛集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红军时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48年留在东北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出任首任驻苏武官。他是典型的北方大汉,身材魁梧,长期的军旅生活,养成了举止端正、衣着整洁的好习惯,颇有军人仪表。
丁国钰,1906年生,1933年入党,红二十五军老战士,1934年参加长征,曾在抗大学习,历任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等。1950年11月,任第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时入朝。1952年,李克农认为他适合做外交工作,便让他去开城代表团主持政治思想工作。1952年至1953年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负责。1953年4月26日,接替边章五为志愿军第三任首席代表。停战后,任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1954年02月25日,带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撤离开城。此前,周恩来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称:“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一“告状”反而使周恩来知道了他,以后让他脱掉军装专搞外交。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丁国钰先后出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
柴成文,1905年生,河南遂平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因中国驻平壤大使尚未到任,周恩来从第二野战军将他调出,并指派他先带几名军事干部到平壤,同朝鲜党、军保持联系并了解战场变化。作为驻朝大使馆代办,柴成文陪同彭德怀首次会见了金日成,并先后两次陪同金日成赴北京与我国领导人会晤。商定我出席停战谈判人选时,北京指派柴以中校名义任志愿军联络官,并按李克农建议将柴军武的原名改为现名。柴在谈判初期,同朝方联络官一起排除困难,恪尽职守,为谈判的具体安排作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4月,他接替解方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停战后继任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回国后历任我驻丹麦公使、总参二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和中国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平曾这样描述柴成文:“他个头较高,人很精干。虽是行伍出身,在谈判桌上却能谈吐自若,机智幽默,随机应变。”
这些代表虽然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但多数人同美国人打交道却没有经验。因此,在谈判开始前的一次会议上,李克农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担心哪些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挑逗而冲动。”他对代表们的忠告,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在谈判桌上说了的话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对外表态要特别慎重。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也不要抢先一分钟。”
在这些代表背后,有李克农这样一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纵横捭阖、为党工作的老将掌舵,确是谈判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谈判中运筹帷幄的幕后英雄
李克农在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中有极高的威信。
杜平回忆道:“开城一年多的朝夕相处,李克农留给我的印象是:知识面广,经验丰富,又善于团结人,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干将。他严肃稳健,不管在什么场合总是衣冠严整。他戴眼镜,穿马靴,留短胡须,举止大方,很有外交风度。”
伍修权写道:“克农同志正是这一战场上的前线总指挥。也正是由于他的高度智慧、无穷精力和忘我精神,才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为中朝人民赢得至今还享受着的和平成果。”
丁国钰谈道:“李克农和乔冠华都是开城代表团不可替代的人物。没有李副部长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威望,很多事都难以办成。李副部长是一个有风度、有气魄的领导人。特别是停战谈判涉及中朝两党关系,谈判桌上,是朝方代表发言,而谈判的具体操作又是中方管。这就不太好办。所以搞好同朝方的关系,至关重要。李副部长经常找朝鲜同志开会,谈心,一起商量。每次同美国人在板门店见面前都要召开中朝两方的预备会。在朝鲜同志面前,他从来不流露‘以我为主的心态,因此很能得到朝鲜同志的信任和尊重。”
平时,李克农讲得最多的是“团结”两个字。他说,我们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都各有本领。他说他自己没有什么本领,工作都是靠大家,如果说他有一点本领的话,那就是会“团结”。他不仅关心高级干部,对年轻干部、对刚从学校调来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更是关怀备至。他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但态度和蔼,谆谆善诱。
李克农在代表团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隐蔽他的身份,我们都称他为“李队长”(谈判代表团初期称“谈判工作队”)或“000”首长。这一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至少在谈判期间,没有见到美方的新闻媒体上出现过他的姓名。正因这样,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乔冠华是代表团的第二把手,代号“002”。干部称他为“乔指导员”,同事称呼他为“乔老爷”。代表团给中央的请示报告都是由李克农先讲个大概,乔冠华口述,浦山记录,经修改后再送李克农批发。代表团的形势分析会和战前的预备会也大多由乔冠华主持,内容最后由秘书处整理,经李克农过目后连夜向中央汇报。
杜平是代表团的第三号人物,代号“003”,代表团党委书记。去代表团前,他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重要工作之一是负责战俘管理。来开城途中,他带着两箱战俘材料,翻车受伤,四根肋骨裂缝,幸无生命危险。如果这两箱材料被美机炸毁了,板门店谈判不知又会出现什么曲折。在开城,他担负起指导战俘问题谈判的重任。同李克农和乔冠华一样,杜平也没有在谈判桌前露面,他们都是运筹帷幄的无名英雄。
李克农致信章汉夫,信里对乔冠华深表关爱:“希望……能让他回国休息一两月,恢复疲劳,保证健康,为党储才。”
谈判桌上的斗争十分尖锐,双方代表经常唇枪舌剑。为此,每次会前都要作充分的准备,特别是拟好发言稿。发言稿有两类:一类是长篇发言,系统驳斥对方的论点;另一类是短兵相接时使用的临时发言稿。朝中代表团先开会,商定对策及发言内容,落笔的任务便交给了乔冠华。
乔冠华思维敏捷,语言铿锵有力,且有独特的工作方式。他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低头沉思,猛抽着烟,来回踱步,口中授词,参谋执笔疾书。成文后,再经他过目定稿。我和另一名青年则静候在旁,他每确定一稿我们便立即复写五份,其中两份立即送去翻译。这一过程,往往要赶在当天早晨谈判代表出发去板门店前完成,时间十分紧迫,关键人物便是“乔老爷”。
对谈判中的重大问题,乔冠华也常有自己的见解。1953年初谈判破裂期间,我方内部讨论是否要主动提出复会问题。乔冠华提出:“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此建议颇得中央赏识。又如谈判开始时,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乔冠华在讨论时表示:“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没过多久,战俘问题果真成了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绊脚石。
乔冠华是代表团中的才子。他在德国读过哲学,懂得好几门外语,对中外文学有研究,笔头很锋利。有人说他“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行文洋洋洒洒,张口妙语连珠”。这样的赞誉,恐不过分。在举止仪态方面,乔冠华也独具特色。“乔冠华很活跃,笑也笑得潇洒,骂也骂得利落。他天性好动,外出时,手里喜欢拿根文明棍,不停地摇着,大有学者之风。”
乔冠华的两大嗜好是烟和酒。“茅台喝得差不多时点子就出来了。”每次开预备会时,他身边总是放一瓶茅台酒,说到高兴处就品一口茅台。但每逢李克农和朝鲜同志都参加分析会时,他就自制,顾不上“照顾”茅台酒了。酒能提神,也能误事。一次喝醉了,李克农瞧着直摇头:“这可不行,在外交场合要误事的。”
乔冠华才华横溢但高傲自负,不拘陈规,和他配合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伍修权曾回忆道:“当时第一助手是乔冠华。‘乔老爷,可不好领导呀……而他(李克农)完全有办法领导好老乔,让我留下来就有困难。”谈判签字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乔喝醉了,摔了酒杯,对李克农出言不恭。当时李不在场。事后周恩来批评了乔。乔向李承认错误时,李只是平静地说:“这事我知道了。你眼里没有几个人,要吃大亏的。”
乔冠华当然不会知道,这位老人曾致函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表露了对他的深切关爱和期待:“多年来老乔辛苦了。如果没有老乔,我个人不可能支持下去。乔身体并不健康,尤以睡眠甚少,长期维持绝不可能。此点,老乔还不自觉。希望协议达成后,能让他回国休息一两月,恢复疲劳,保证健康,为党储才。”李克农的大将风度、爱才之心和处处为党考虑的高贵品德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