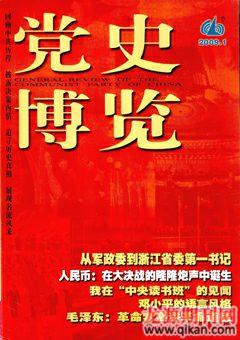从军政委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铁 瑛
一日读报,偶尔读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原主任,现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所填的《自在人》一词,忍不住拍手叫好。词曰:“胸中有海,眼底无碍,呼吸宇宙通天脉。伴春来,润花开,只为山河添新彩。试问安能常自在?名,也身外;利,也身外。”顿时,改革开放初期在事关“温州模式”争论问题上,我与马凯同志接触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此时,电话突然响了,是在南京军区当作家的女儿竹伟打来的。她说今年(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请爸爸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文革”结束后,“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到各省当领导的部队干部全都返回部队了,为什么全国唯独你一个被中央任命为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第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为什么没有绝对服从“两个凡是”,而是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不少部队离休老干部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却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步步想不通,常常一边吃肉一边骂娘,为什么你却能完全接受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对“温州模式”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
我笑道:怎么我刚想到什么,你就问到什么呢?!
从舟嵊要塞区军政治委员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周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大声称赞道:“铁瑛同志,你真痛快!”
人的一生中,有些日子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我,在当天晚上接到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紧急电话,要求尽快赶往北京开会。第二天赶到北京后,我便直奔西山。
会议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主持。当会上宣布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时,全场掌声雷动,足足有三分钟。我也是喜出望外,眼含热泪,手掌都拍疼了。
不过,当听华国锋主席布置回去怎么传达、怎么批判,提到还要继续批判邓小平时,气氛就没那么热烈了。怎么还要继续批邓呢?我不禁锁起了眉头,讲真话的习惯又让我憋不住了。当会议开始征求意见时,我霍地站起身,大声提出一个请求:“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我坚决拥护,但我认为揭批‘四人帮和批邓是两个正反面,我希望停止批邓,专一揭批‘四人帮。”
“对,我赞成铁瑛同志的意见!”坐在旁边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立即表态支持我的观点。
华国锋主席平静地说:“这慢慢地会转过来。”
散会时,有同志向我伸出大拇指,也有人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地说:老铁,你怎么还是当兵的作风?是啊,虽然转到地方工作四年多了,但还是当年的脾气。
1972年3月底的一天,时任舟嵊要塞区军政委的我,正在外海花鸟岛上检查部队战备工作。半夜时分,秘书报告说:刚接到中央紧急通知,要你明天赶到北京。
第二天上午9点钟,飞机从宁波起飞,同机的还有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因为北京天气不好,飞机只得降落南京。在那里,许世友司令员很严肃地向我俩介绍了情况:为解决浙江问题,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了一周了,没有什么进展。他最后说:“你们两个去,有什么就讲,不用怕。要不行就找总理去,不用理那些‘戴眼镜,夹皮包,打起仗来一团糟的人。”我和马龙闻听会意地笑了:许司令员指的是张春桥、王洪文。
我像往日领命出征一样,只想着一定要完成许司令员交代的任务,有什么讲什么,压根没想过自己人生会有什么转折。
我俩于3月31日晚赶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委托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一宣布开会内容,我便举手发言,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马龙也讲了一二十分钟。我俩联系浙江的实际,揭发了林彪及其追随者搞乱浙江、分裂军队、分裂党、破坏军民团结的一条又一条具体罪状。等我们发言完毕,已经是夜里12点了。周总理宣布:“好,明天开小会。”
起身离开时,站在门口的周总理伸出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力摇晃了一下,大声称赞道:“铁瑛同志,你真痛快!”接着又握着马龙的手说:“你也痛快!”
4月26日,全体政治局委员再次接见浙江同志。这次谭启龙同志(时任福建省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谭启龙同志、铁瑛同志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主持浙江省委工作。”
听到中央的这个决定,我感到十分意外:参加革命后,工作虽曾有过多次变动,但主要还是在部队,现在要到地方,尤其是到省一级领导岗位上,去管理3300万人民的衣食住行,自己能行吗?
于是,我向周总理如实讲了自己的顾虑。总理看了看我说:“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吧。只要认真,可以做好的。你的工作以地方工作为主,但军队也要管。”接着再三叮嘱说:“到省委后,要抓紧安定团结,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保障全省人民的生活。”
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又说:“铁瑛同志在会议期间表现很好,对解决浙江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许司令员也个别跟我说:“谭启龙是个老红军、老同志,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搞好团结。”
带着总理和许司令员的教诲、鼓励和嘱托,我于1972年5月1日到浙江省委任职。
省委领导工作本来就千头万绪,比起军队工作要复杂得多、辛苦得多,加上又是在“文革”期间,有“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工作起来更是不易。从1972年到1976年的四年中,浙江省委刚团结起来就被搞分裂,再次团结又被分裂;工农业生产也一样,刚有点恢复,又被搞得停工停产。尤其是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在“四人帮”直接插手下,省里派性大泛滥,我被列为“林彪线上的人”,大会小会日夜被批斗。
面对冲击,我尚能镇定;面对批斗,我也能应付;但面对浙江经济的又一次倒退,我却心如刀绞。我觉得愧对中央、周总理的信任,愧对浙江千百万父老乡亲!记得那时从北方调运地瓜干、小麦支援浙江,在一列火车上有一行白漆狂草——“给浙江懒汉吃”。鱼米之乡的浙江,在三年困难时期尚能调粮支援兄弟省市,现在竟然落到如此地步,我的心被深深地灼痛了。而最让我心痛的是:省委一班人因为“四人帮”插手而分裂,浙江形势被造反派折腾得一片混乱。那一时期,我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忧心忡忡的不眠之夜。
这样复杂的局面,我过去在部队从来没遇到过。在部队里,党委内有话说当面,哪怕拍桌子吵一架,只要达成一致,形成决议,大家会齐心协力执行;发现问题,总是第一把手抢着挑担子,绝不会诿过于下级。
后来,我横下一条心:既然我是省委书记,无论造反派追究什么错误,哪怕是省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别人推得一干二净,我也决不“翻烧饼”,决不往下面推责任。再怎么批斗,我也一肩挑,坚持保护下面的干部,否则,让执行省委决议的干部今后如何工作、如何生存?!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同年10月,谭启龙同志被中央留在北京,直至调离浙江,省委的实际工作由我主持。我牢记使命,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性,使浙江的经济逐渐开始恢复。
1975年11月,我正在绍兴搞调研,闻知又要批邓,心情十分压抑、苦闷。因为劳累,再加上心情郁闷,身体终于挺不住,突发的脑血栓使我在会场突然讲不出话来。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身体不能动弹的我,只能躺在病床上流泪。在上海、南京治疗8个月,得知毛主席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内心着急,带病赶回杭州……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迎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春天。根据中央部署,浙江省委一班人就像是上足发条的机器,不知疲倦地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中去。
1977年2月,中央任命我为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胡耀邦对我说:“我们考虑过了,你不能回部队,还在地方吧!”/注重团结,实事求是,讲究政策,浙江的工作很快有了起色
虽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我心底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重新返回部队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抽调部队领导干部到地方工作的情况确实有,尤其抽到外交部出任驻外使节的部队干部不在个别。“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各部委、各省市地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当政府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时,为了安定局面,才出现了“军管会”,才有了各级部队干部到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地县机关“三支两军”。有一段时间,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干部被抽到地方任职。后来,随着中央和各省市地县解放干部,领导机关恢复正常,部队干部陆续返回部队。截至1976年,仍担任省级领导干部的军队干部,只剩下我一个。
实事求是说,我在浙江省委四年,经受冲击的力度、历经斗争的复杂,是我30多年军旅生涯中不曾有过的,同时,获得的政治荣誉也是在部队任职时不曾有过的:我参加了党的十大,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后来又当选为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也参加了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亲耳聆听了周总理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心中刻下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目标。
在许多人眼中,“四人帮”被粉碎了,一切走上正轨了,我继续当省委书记,可谓“多年媳妇熬成婆”,苦尽甘来,名正言顺。加上又是在江浙富裕地区当“父母官”,这是多少干部梦寐已求的事啊!但是,站在发展浙江的立场上想,正因为这里是鱼米之乡,要恢复和发展经济,更需要有领导地方工作经验、熟悉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内行来当省委领导。在经济战线,外行是无法长时间领导内行的。
于是,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我找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谈了自己的想法后要求道:“现在‘四人帮也粉碎了,部队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也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还是回部队吧,派更有经验的地方同志去浙江省委。”胡耀邦同志听后对我说:“听中央的嘛!”过了两天,他又跟我谈:“我们考虑过了,你不能回部队,还在地方吧!”
我仍然坚持:“胡部长,我主要是从工作考虑。我搞地方工作是外行,还是请有经验的老同志来担任比较合适。”“铁瑛同志,你在浙江搞得好,能团结常委一班人。只要省委一班人团结,这是能搞好揭批查、发展浙江工农业生产的最大前提。”
看胡耀邦同志态度坚决,我只好表态:“我是共产党员,服从中央决定!”
浙江有很多长期在本省工作的老同志,他们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但因为历史原因,或者因“文化大革命”中的因素,同志之间有一些隔阂。作为“班长”,我一直注意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注意扬长避短,求同存异;多次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向前看,聚精会神搞建设。
1977年春,陈云同志来到杭州。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好!铁瑛同志,我知道,你是个年轻的将军嘛!”然后,他对我们说:对“四人帮”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处理,要有区别,要实事求是,讲究政策。
久违了的“实事求是,讲究政策”,给我启发很大。
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谈了自己的收获,常委一班人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在省里清查造反派头头时,我们不以感情代替政策,不因为他们曾经批斗过我们就对他们抓住不放、完全用对待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而是先将他们调离领导岗位或单位,组织力量揭发、批判、查清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1977年4月,我代表省委宣布: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审查对象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搞好定性处理工作已经提到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因为注意政策,浙江的揭批查运动开展得比较顺利。
我敬仰毛主席,但更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的讲话干脆利落:“我就讲一句话,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现在年轻人的眼中,我们这些老一代,对毛主席有感情是“个人崇拜”。
不错,凡是参加过打江山的老红军、老八路,对毛主席确实有极深厚的感情,这倒不是因为林彪的“大树特树”,而是在每一次革命关键时刻,共产国际说毛泽东错了,中央有人说毛泽东错了,偏偏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对的。一次、两次、三次,党内许多领导同志不免就形成了思维定势: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是对的,有时自己不理解,可能是因为看得不如毛主席远。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绝大多数干部不理解也继续紧跟的主要原因。但到了1971年后,尤其是“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严酷的现实让许多同志有了自己的看法。我就常常自问:毛主席已经年近八旬,他老人家对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还能否了解全面?
1975年1月,我受省委委托去金华地区收缴武器,经过艰苦工作,收缴了三四百支枪,武斗总算被制止。可当我被召回杭州开会的第二天,金华地区又响起了枪声。我深感痛心和困惑:党的领导如此缺乏权威和软弱无力,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不曾有过。
1975年2月8日,毛主席到杭州治眼睛,谭启龙同志和我到专列上去迎接他。老人家握着我的手,第一句话便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我心里很惊讶: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见谭启龙同志没吭声,我回答说:主要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几天前,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造反派冲进会场,要把谭启龙和我抓走,警卫部队赶来才从造反派手中把我们夺过来,但杭州饭店被造反派占领,会议只能易地召开。
落座后,毛主席面带微笑问我:“铁瑛同志,你是哪里人哪?”“河南人,南乐县的。”虽然是第一次与毛主席面对面谈话,我心里并不紧张。主席接着问:“在哪里读书的?”我回答:“在保定二师。”
“噢,保定二师。那是个好学校,好学校。”毛主席明显带着赞赏的口吻说,“谈谈省里情况吧!”
当着主席的面不讲更待何时?我立即抓住重点,汇报了省里的情况:“批林批孔”,批唯生产力论,许多工厂停工;农村受武斗影响,江南鱼米之乡都吃北方省运来的地瓜干、玉米面……前后谈了20多分钟,毛主席表情凝重,吸着烟,只是听着、思索着。
毛主席在杭州两个多月,省委分工由我负责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和安全工作。我白天去省委开会、工作,晚上便住进汪庄六号楼。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经常找我去汇报省里的情况。
是如实汇报“批林批孔”运动遗留下来的成堆问题,还是追随当时的政治气候报喜不报忧?我没有犹豫,毅然选择了前者。我坚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绝不会看轻中国黎民百姓的温饱冷暖的。我如实把省里存在的令人担心的问题一一向主席汇报。
很快,汪东兴同志对我说:毛主席表扬你了,你比××好,并作出了果断决定。当着我的面,汪东兴同志拨通了王洪文办公室的电话,通知王洪文:毛主席批准浙江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被占领的杭州饭店赶出去。一直无法无天的造反派头头,嚣张气焰受挫,渴望安定团结的广大市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毛主席回北京不久,纪登奎同志受中央委派率工作组来到浙江。他对省委一班人说:这次带工作组来,小平同志亲自交代要为解决浙江派性问题、“双突”问题制定出办法和措施。
在西泠宾馆,纪登奎同志对我和谭启龙同志说:江青,毛主席批评她了。在湖南给毛主席演《青春之歌》,毛主席鼓掌,但其他人叫主席不要鼓,因为江青说是毒草。主席说:我没看到有毒啊。张春桥写了打“土围子”,主席批他:“土围子”指许司令他们。姚文元写文章,毛主席也批评了他。王洪文到长沙去告总理状,毛主席批评他,让他们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
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说法。说到底,“四人帮”还是毛主席给定的名。
在中央于1977年2月任命我为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尤其是胡耀邦同志与我谈话后,我不再想回部队的事,专心浙江省的改革开放工作。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我开始并不知道这篇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背景,但从自己当六年省委书记的实践中,切实体会到这点是真理。我指示《浙江日报》于6月10日全文转载,组织省委常委连续几天学习、讨论这个问题,并达成了共识。
9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浙江省委的讨论情况。这就是后来说的“浙江是第七个表态的”。
我到北京开会,汪东兴同志曾找到我问:“你对‘两个凡是的看法是什么?”我当即明确表示:“我们完全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按‘两个凡是,如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何解释大批老干部的复出?”
1978年10月,我与陈丕显同志率中国党的工作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期间,突然接中央紧急电报:提前回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时,受社会各种思潮影响,中央工作会议上争论很尖锐,最焦点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下去?
陈云在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应该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一批老同志的职务。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讲话,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作了书面检讨。
小平同志是在闭幕式上讲话的。他干脆利落,直插主题,三两句话就把大家的心牢牢抓住了:“我就讲一句话,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的问题宜粗不宜细。同志们,我们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赶紧转移,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转移到以抓生产为重点上来!”
话不多,却使人异常振奋。我心头的疙瘩,也得以迎刃而解。
听完浙江经济“翻两番”的汇报后,小平同志很满意:“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指标。”/从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留在省里担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1979年初,浙江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省委有了统一的认识,掌握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会议总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讨论了如何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问题。我代表省委郑重宣布:浙江全省揭批查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各级党委要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毕竟不能很快统一。会后有人要与我们辩论,说现在工作重点绝不能转移,“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虽然已被粉碎,但与他们有牵连的人和事尚未彻底查清,造反派的帮派体系还没有彻底查清,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等等。对此,我们一边要求干部加强学习,一边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强调要把工作重心转移过来的道理。事实上,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后,人们的思想认识才真正统一起来。
1983年春节前夕,小平同志来到杭州过春节。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第一次到杭州,也是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接待他——当时我们已经将省委机构改革的计划上报中央,并已获得批准。根据计划,我与省委的大多数老同志都将退居二线,提拔一批年轻同志担任领导,只是根据中央指示尚未公布。
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缓缓停下后,小平同志从车中下来,步履平稳,满面笑容,伸出手来与我和李丰平、王芳、薛驹等同志一一握手。
小平同志已是近80岁高龄的老人了,旅途劳顿,我们想请他先休息几天。小平同志摇摇手说:我不累,大家进屋里一块谈谈。
进了屋里,小平同志先说开了。看得出,他心情很高兴。他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
接着,我开始汇报。当我讲完第一个问题——省委机构改革的情况后,小平同志说:班子如果可以再年轻一些,11个常委中有两个50岁以下的同志,就更好。接着,我汇报了第二个问题——浙江1982年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当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已经人均600美元。我们分析了全省工农业发展的情况,认为到2000年翻两番半或翻三番是可能的。
“哦,你们有信心能翻两番半到三番?”小平同志认真地问道,“你们有什么措施作保证吗?”
“有的。”我接着汇报了省委目前紧抓的五项措施,“解放思想,抓改革,抓科技和教育,抓浙江轻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从纲到目,汇报了近两个小时。小平同志全神贯注地听着,看不出有丝毫的疲惫和倦意。
听完汇报,小平同志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你们的工作不错,我很高兴。是呀,到2000年,江苏、浙江是应多翻一点,不然青海、甘肃这些基础落后的省可能会有困难。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指标。”
看得出,对不同地区的改革,小平同志有不同的要求。就像打仗有攻坚、有打援一样,广东、福建改革的任务是搞特区,闯路子,而我们长江三角洲比较富裕的省份,则是在充分发展原有经济的基础上,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改革、发展、提高。
事实也确实如此。改革有先有后,不可能齐头并进。回想当初浙江推广“包产到户”的情况,省委就有同志批评我犹豫了。实际情况是:省里开常委扩大会议,大部分同志不同意“包产到户”,尤其是富裕地区如杭嘉湖平原地区,包括宁波、金华地区都不同意,提出许多问题,例如:生产队的挖泥船、打稻机、拖拉机怎么分到户?群众还想不通,又怎么贯彻执行?
于是,我们从省里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改革开放不必一刀切,先从山区、从比较穷的地方开始,从南向北逐步落实“包产到户”。这样,浙江全省完成“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任务比有的省晚了半年左右。当时,省里是陈作霖同志分管农业。他去北京开会时,代表我们省委检讨浙江的步子太慢了。
我去北京开会时,李先念同志很真切地对我说:“铁瑛同志,你们省还检讨干什么呢?你们搞得晚一点,稳一点,少走点弯路,这样好嘛!”我回杭州后,即向省委传达了李先念同志的谈话。由此也可以看出,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脚踏实地地工作,是可以得到支持和理解的。
1983年4月,胡耀邦总书记找我谈话:“铁瑛同志,我们一起再干一届,到时候一齐下!”从这句话里,我听出中央对我的信任。粉碎“四人帮”那年我正好60岁,这年67岁,这七年第一书记的工作虽然很累,但因为有了省委一班人的团结,有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浙江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五年位居全国第一。于是,我信心百倍地表示,只要组织需要,一定努力干下去。
谁知10月去北京开会,胡耀邦同志再找我谈话时,意思却变了:“铁瑛同志,我们带头下吧。趁小平同志和我们在,领导班子新老接替搞快一点,我们当顾问,扶他们上马,再送他们一程。”
相隔只有半年时间,却一个上一个下,真是天壤之别。要说不意外,要说没想法,这是假的。而当时像我这样下来的“心潮起伏”的省委第一书记不在少数,有人去找中央领导要求换个岗位,继续工作在第一线,也有人劝我也如此去做。
我冷静思考几天后,想通了:革命不就是后浪推前浪嘛。是啊,趁中央老一辈健在,趁我们这中间一茬身体还行,让更年轻的同志上来,在领导岗位上学习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后劲十足,一步一步走向更深入。
所以,虽然看到有些省委第一书记下来后又到北京各部委继续任正职,而且也确实有中央部委向我提出邀请,我都没有动心。按照中央决定,我留在省里当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继续为浙江各项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注重调查研究,经常与群众面对面交谈,才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针对争论,邓小平指出:“允许实践,错了改。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改革也要靠这个。”
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一直是我非常重视并经常运用的工作方法。
在任期间,我跑遍了全省每一个市、县、区,深入工厂、农村和科研单位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写出了不少调查报告,如发展山区经济、海洋渔业、食品工业,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的报告,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并批转全国各地,或者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经济问题研究》、《农村工作通讯》、《党建研究》等刊物上。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突然问我:“铁瑛同志,你在省里是不是有一个写作班子?”
“没有啊!”我有点奇怪,“为什么这样问?”
“我看你年年有文章发表嘛!”
原来是这样。我如实回答说:“宋部长,这些调查报告都是我每年带着秘书下基层调查,然后分析研究后写出来的,没有专门写作班子。”
后来,秘书帮我统计过,自我到浙江工作后,全省每个县市都去调查过,而且最少也是三遍。这是过去历届省委书记都没达到过的纪录。因为常到各地调查研究,和群众面对面交谈,所以在许多新生事物出来后,我都能及时了解,认真研究。只要是对人民生活有好处,我总是举双手欢迎,而不会站在对立面。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一次去江苏江阴华西大队学习、考察,那时的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亲口对我说:“铁书记,‘文革期间,无论是国家领导人来视察,还是全国各地来我这儿取经,我只讲发展集体农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实我一直留了一手不敢讲,那就是我们有个牛皮纸袋厂。这些年来,大队主要靠着这个厂积累资金,按时买进化肥农药……光靠种田,只能糊个嘴呀!”这番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之后,省委大力支持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使浙江省那几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以每年16%以上的速度递增,发展速度位居全国前列。
再就是一直支持温州改革之路。
改革开放后,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温州人民开始一往无前地闯进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千家万户兴办家庭企业,创办起数以百计的专业市场。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首次提出“温州模式”概念,引起了全国强烈反响。
对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格局,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和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温州模式”到底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有人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区域是“资本主义特区”。一位北京来的领导到温州转了几天,断言说:除了市委、市政府大门上的国徽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而在这一问题上,浙江省委也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听到从北京传来的一些领导的批评时,难免有思想压力。
为此,我走遍了温州的市、县和农村,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国力有限,国家在温州投入的工业基本建设的项目少,而资金更少,发展也不可能快。如果温州人不自力更生,都向政府要工作、要收入,国家能包得起吗?
1984年,邓小平亲临深圳视察,极大地鼓励了特区建设者的信心。在一次讲话中,他说:“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是资本主义,怪得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依我看,社会主义应有这样的胸怀,能把世界上一切文明的东西,好东西都拿过来为我所用。我们已经耽误了太多时间,我们不宜拖延,不能拖延,拖不得。再耽误不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我们划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中央不给钱,只给政策,要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不搞争论是我一大发明。允许实践,错了改。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改革也要靠这个。”
1984年5月,温州被国务院列为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198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为全国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然而,对“温州模式”,全国的争论依然十分激烈,浙江省委一班人的意见也很难统一。一次,当时的国务院总理陪同外宾到杭州,我坦率地向他汇报了自己对温州的看法,同时摆出了中央和省委对温州都有不同看法的实际情况。我向他提议:请中央派一个工作组,由经济学专家领队,当然要选一位不怕压力、敢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对温州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拿出一个比较中肯、有说服力的报告,说服中央和地方上的不同看法。
不久,中央就派了经济专家马凯同志。他带工作组到温州调查研究了近半个月,写出了调查报告。报告既如实反映了在温州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环境中,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肯定温州国有经济比重虽下降,但其发展速度仍与全国、全省保持同步。结论是:温州经济发展70%是社会主义的、是好的,30%不好的有待纠正,从而肯定了温州经济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
但是,这次调查后,对“温州模式”的争议并未就此结束,直到1992年初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发表,以及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人们才逐渐统一思想认识,温州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才画上句号。■
——浙江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