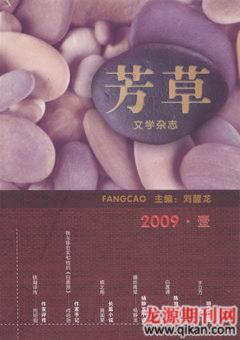你为什么不害怕
强 雯
作者简介:强雯,重庆人。有中短篇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大家》、《小说界》、《红岩》、《啄木鸟》、《飞天》、《当代小说》、《重庆文学》等刊物。参加二○○七年全国第六次青年作家创作会,毕业于二○○八年第八届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班。现在重庆某报社供职。
一
宋菌和莫巧巧呈丁字形躺在床上,房间里黑黑的,有一点隐约的光在墙角怯懦地瘫着,比一节用废的电池发出的能量还要差劲。有近五十秒,两人都没说话。没有浓重的喘息声,只有不算流畅的鼻息顺着自己的下颌爬到耳朵里。那只A货的雷达表发出嗒嗒的声音,代替了一切语言。宋菌不自觉地数着声响,好像他一直掉在一大堆器械零件中,然后碰了碰莫巧巧,她没有反应。
要一分钟了。他说。
那又怎么样?莫巧巧扬起小巧的额,又飞快地把眼神收了回来。
雷达表还在嗒嗒。
那又怎么样?莫巧巧一跃而起,俯视着脚下的男人。他的脸色和光线一样混沌不清。她跨过他的身体,利索地穿好衣服,然后走向窗户,试图去拉开窗帘。
别拉。光线让宋菌突然警觉起来。
莫巧巧回过头看他,重新坐在床沿上,扑哧笑了出来。宋菌已经坐了起来。“别动!”她从后面逮住他,就像几分钟前他要求她的那样。“我太激动了,别动,求求你,别动。”她记得他刚才温柔又急不可耐的声音。
宋菌背对着莫巧巧,轻易地就甩开了她的两手,他有些发窘地穿好衣服,没忘记那只A货的雷达表,现在它的声音已经消失了。他稍感到平静地坐在莫巧巧的旁边,并且主动打开了床头灯。
莫巧巧看到了宋菌的眼袋。他们都没有洗澡,他们其实都应该去冲冲,莫巧巧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她没有动,好像她动一下,马上就会遗漏掉什么情节,宋菌也没动,他希望某个情节快点跳过去。两人并肩而坐,莫巧巧继续看宋菌的眼袋,几乎和眼睛成一对一的比例,烟锅煤似的脸,像一个真正吃了败仗的人。莫巧巧笑不出来了,低着头想,如果他此刻来讨好我,或许我可以原谅他的丑陋。
但是什么都没发生。他们像一块木头挨着另一块木头。
我,要走了。宋菌站起来,抖抖牛仔裤上的皱褶,有点不自在地说。他把搁在床沿的公文包提在手上。
莫巧巧盯着他。
你想我陪陪你是吗?走了两步,宋菌回过头,仿佛发现了加油站的地上有个烟头那般小心。
莫巧巧有一秒钟的迟疑,但立即点点头。
可是不行,快四点了,他抬手看看表,我要回报社了。这一次他不容置疑地说。
宾馆前台把已经完成的结账清单递给宋菌,莫巧巧倚在门框上看车水马龙,宋菌上前,连肩都没拍,“那咨询什么的,我们在网上要多联系。”说完,他们各自消失在前进的路上。
二
真有趣。宋菌在电脑边欢快地完成法律在线的栏目后,想不出今天能写的第二篇稿子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四个星期了,他每天只是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中选择一个,向某律师抛出一个问题,然后整理出来。宋菌站起身来,走到窗边伸了一个懒腰。茶色玻璃外是茶色的天茶色的桥,好像夜晚已经提前降临。蓝河县的河水已经响动起来了吧?一到夜晚,蓝河县的河水就哗啦啦地震动起来。那地方娱乐少,下了班人们就关灯睡觉。一条河的声音响动整个县。离开蓝河县的一个月,宋菌每天晚上都枕着两个声音入睡,一个是蓝河水,一个是铁轨声。蓝河县跟松城通上了铁路,过去开汽车要十三个小时的路程,现在缩短到六个小时了。他要离开这里,他跟在教工食堂里做墩子的妻子说,“快去快回。像铁轨一样。”
真的是很快。宋菌从窗户边转了回来,偌大的一个新闻制造车间,键盘敲打的声音在空间回荡,这节奏让人心慌。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宋菌必须快速运转自己,把这一天有价值的东西统统塞到电脑里去。他没有自己的座机,作为一个从区县借调上来的记者,他目前还处于试用阶段。他和三个记者共用一个座机。
“试用只是暂时的。”给宋菌办理借调令的头头拍拍他的肩膀,宽慰他说。“总要有个过程,我跟上面好有个交代。”宋菌努力点头,好像要把那黝黑的面孔藏起来似的。“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用我的座机。”这次宋菌把头压得更低了。
他不想别人听见他打电话。每一句问话都非常艰难,他甚至希望在他用电话办公的时候,周围的人正好都在休息。他完全可以干净利落地采访,但他不想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其实宋菌的口才挺好的,在蓝河县做教师的时候,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但现在不行了。他的舌头好像被松城吃掉了。
办公室的座机就搁在两个电脑之间,它和最近的一个人的距离不到一米,那么,宋菌要用的话,不到一米的人,会听完他所有的通话内容,然后用不到一天的时间,把他那些可笑的提问传送到同行那里。一个被引进人才的笑料。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结论。宋菌看着那电话,直到它被另外一个手摘了去,不甘却终于理直气壮地吐了口气。
还是找不到新闻线索。宋菌勾着头自我审判似的待在自己的座位上。快一个月了,他的记者生涯没有一点进展,他也不会像那些小姑娘,整日抱着电话,一手翻着城市黄页一边娇滴滴地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其实,他也会哄人开心,就像家访一样,他不也是说了些赞扬别人孩子的话吗?介入主题之前需要一点放松,他知道。但在松城,各种要害部门,这种最通常意义的寒暄往往被粗鲁地打断:“你到底想说什么?”接线员公事公办地问。
“政府部门高效节能了。”握着盲音话筒的宋菌,像一截干枯的树枝,马上就要掉下。每一个路过他的人,都忍不住要顺带扒拉下。
宋菌搓了搓自己那张黝黑结实的脸,有一层油垢,顺势跑到手指甲里。黑框眼镜丢在一边,镜片上有太多重叠的手指印,粘着稀稀拉拉的头皮屑,他用手指里里外外抹了几下,看也不看,重新挂在鼻梁上。在蓝河县,宋菌至少还是自由的,每天他只需要像放鸭子一样,带学生即可,不像现在斤斤计较工作量,以防落入末位淘汰的行列,其实他已经是末尾了,宋菌想,不过是头头放他一马。还有两个月,宋菌皱皱眉头,他已经拿下了莫巧巧,她为什么不恐慌。
三
为什么要恐慌?莫巧巧不解地问。
为什么?宋菌第一次单独和莫巧巧见面,隐隐觉得找到了突破口。
法律在线是个最简单不过的栏目,只要跟某个律师事务咨询所建立一种长期关系,这个栏目的操作,就不再有什么难度。作为新入门的记者,宋菌从同行那里得到了几个律师的电话,以示关照。开场白不算顺利,和陌生人在一分钟内建立友好关系,宋菌还不自信。好在对方利落通晓,快速约定面谈时间。
是莫巧巧接待宋菌的。莫巧巧的胸前挂着实习生的牌子,这让宋菌感到一丝侮辱。他们两人的年龄应该相差二十岁,宋菌在律师事务所的角落里端着一次性水杯不停地吹气,他想他们应该在另外一个场合里说话,他会自然些。
“朱律师说,你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他的邮箱,他回答好以后再转发给你。”莫巧巧抱着文件夹说。“不过,你既然来了,也可以把问题直接写下来,我会把它们录入电脑的。”她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白纸。“他正在打电话,你愿意等他一下吗?”
宋菌点点头。四下里不算宽敞,两格蓝板格子间反而使空间无序,电话铃和人声此起彼伏。二十分钟后,朱律师亲切会见了宋菌,三分钟。他的话简短有力。
“知道为什么吗?”朱律师把轮椅从办公桌里推了出来,“因为我脑子太快了,所以上天要让我的什么地方慢下来。”他那营养过剩的上半身和他机敏的神情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你不会觉得我无礼吧。三分钟可以办很多事。”朱律师又把轮椅推回了办公桌里。
“那是。”
“巧巧,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他招呼莫巧巧,迅速完成了交接仪式。
四
我们是同一种人。现在,宋菌来回答莫巧巧的关于恐慌的问题了。我们在这里都没有住房、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对了,你是自己租房吗?
没有,我住学生宿舍。
那是迟早的事。你迟早会自己租房的,对吧。
有可能。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你住学生宿舍,是群租,我也是跟人合租。我们都是寄人篱下,当然,你的房租是父母出了,我是自己出的,不过有一天,你也会自己付房租。是吧?
那当然。
是的,你必须有经济实力后,才能自己承担房租,你有实习工资吗?
没有。
你得给朱律师谈谈。
莫巧巧不言语,低头喝橙汁。
你必须给他谈谈,知道吗?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宋菌侧转着身子,可惜我不是编辑,否则,我会给你开稿费,当然那并不多,但你可以请我喝一次橙汁。
莫巧巧抬起头,她似乎一直都没笑过。
把职业装脱了。宋菌平静地说。知道吗?这样不会显得太冷。宋菌把胳膊搭在旁边的椅子上,看起来胸有成竹。
莫巧巧想了想,果真脱下职业装,搭在椅子的后背上。她回过头来的时候,脸上换成了清纯的神色。似乎还有一点不明显的微笑。
这样好多了。他说。你从来都不恐慌吗?
现在有一点了。莫巧巧坦白地说。
我看出来了。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跟他谈谈实习工资的事,你跟他单独吃过饭吗?
没有。
我想起来了,他行动不方便。那你有上他家去吃过饭吗?
也没有。不过,你请我也许我会去。
为什么?
我说也许。
好孩子,先去谈工资,这样下次你就能请我喝一杯橙汁了。
五
头头交给了宋菌一个新的采访任务,一个女名流的专访。“慢慢采,别着急,先用电话联系,约好时间,登门造访。”宋菌鸡啄米似的点头。这些话他教学生时,也说过的。脸发烫,好在黑,看不出变化。
名流的资料只有一页,一张加了柔光的艺术照。“不真实,让她换生活照。”头头交代。
宋菌回到办公桌前,又看到了那台电话,不过它现在正在被另一个人使用。几分钟后,他等到了那个电话的使用权。电话通了,是一个自动留言机。“你好,我是……”宋菌留了个口讯。十分钟后,他再次拿起电话,给自动留言机留了个单位座机的号码。他的背后传来一阵放肆的笑声,宋菌也嘿嘿地迎合地笑。一会儿,宋菌才意识到是首席记者接到了什么猛料。宋菌凑过去,有几个记者已经围到首席记者身边,听她夸张的讲述。“好!”他附和着,握紧双手觉得应该有个更有说服力的手势,但人们都背对着他。他黑黑的脸庞更适合做一个背景。他并没感到无趣,如果此刻离开办公室,到大街上去,让他去采访个什么人,他才会感到无趣。他想了想,第三次拿起座机,对着自动留言机讲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宋菌提起了那件不算干净的外套,搭在肩膀上,像一个真正的城市盲流一样,决定出去消磨下时间。茶色玻璃外的天空并不是茶色的,天空,还有那么点清新。只可惜一眼望去,更像是松城群楼的边角料。新华街上的“得意不夜城”已经开始营业,那张每天下午一过六点,就会准时出现在后宫会所门口的一张古床,映入人们眼帘。粉红色的帷幔在床沿上飘荡,看不清床单的颜色,似乎还带着一股子香气。轻轨的进出口就在几步开外,宋菌气定神闲地走过古床,镜片反射出帷幔,他装作从容地跳上了轻轨大扶梯,偶尔会回过头来,有那么几瞥,解渴似的,然后等着扶梯下到城市底处,那里有个山河书店,专卖时尚杂志,宋菌无心浏览,也不乘坐轻轨,掉头又上了向上的轻轨大扶梯。他混迹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再次将若有若无的眼神投向那片路过的流光,宫闱似的大门有影影绰绰的人影,房子内的灯光深邃甜美,运气好的话,会碰见小生抬出一张巨幅广告画,那是今天的主题:有时是《红玫瑰与白玫瑰》,有时是《亲密爱人》,有时是《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情欲饱满,无处可藏。时间很充裕,足够把整个中兴路走上几圈,几小时以后,宋菌又会反复一次,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狗。这一带声色场所占据了中兴路三分之一的街道,每晚十点以后,那里发出的狂欢似尖叫,百米开外的中兴路跳蚤市场都能听见。跳蚤市场的铁门阴冷,透出不明的灯光,出其不意地那里会探出一颗头来,好像那里有一桩命案正在发生。不知为何,宋菌总是在这个时候莫名其妙地竖起耳朵,松城的夜空,红蓝变幻,光柱从不同的方向射向云层,拐角有家无名客栈,泛黄的木板门写着五元一晚,摇晃的公车慢悠悠地驶过,灯光有一茬无一茬地扫过拐角,突然地,宋菌就破口大骂起来,对于大多数收班车来说,他们似乎对这样的情景见惯不怪。连头都懒得伸出来,车厢里只有不多的几个顾客,也倦意浓浓。
骂完了祖宗八代的宋菌,隐藏在街道的黑暗中,不急不缓地前行。毫无畏惧。
因为在城中央,宋菌的房租自然不菲。但他不想待在那里,冷冰的灶房和生硬的床,还带着一股猫尿味。他也不想回办公室里,尽管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他完不成工作量,这意味着他无法实现一月三千的收入梦想,更不用说把那做墩子的妻子接到松城来。二十年前,他不过是个村小教师,十年前他成了县中教师,并且,功劳大大地将同是村小的妻子变成了县中的食堂墩子。现在,他终于有点关系来松城工作了,却一点都激动不起来。激动,应该像蓝河县的河水一样哗哗哗哗,生猛有力。而现在,他像被困在一大堆岩石背后。
钱柜KTV、真爱俱乐部,后宫会所,苏荷BAR……宋菌数着这些光亮的玻璃橱窗,流连踱步,他并不比那些手操扁担等待下力的人好多少。在“得意不夜城”里转了两圈,没有一个人招呼宋菌。手机也纹丝不动,没有任何来电显示。
好孩子,可以请我喝杯果汁吗?一种虚弱袭上心头,宋菌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只是紧紧地握住电话,听一听电话那头比他更微弱的声音。
我没有钱。过了晚上九点,莫巧巧就不想出门,宿舍的大门会在十一点上锁。
我也没有钱。他攒着口袋里快出水的银行卡,意识到火候未到。我想家了,你想吗?他闭着眼睛,想象全城断电的情景。
我还没有。
等会你就会想的。他把银行卡放进了贴身的内包。
为什么?
明天我会有钱的,明天我请你喝果汁。
老地方吗?
老地方。
宋菌挂了电话,走在报社大楼的下,望着第四层楼黯然的灯光发了会神,那里的灯光将持续到凌晨三点,才会全部熄灭。宋菌步履稳重地走了上去,记者们大多已离开,夜班编辑来来回回奔走,他们的工作才刚开始。宋菌拿出那个名流的电话,用座机拨了过去,这一次他十分平和地对留言机说明了自己的完整意图。
六
无论哪天,三峡广场都跟周末一样人满为患。据说这不仅是全松城,也是全西南绿化率最高一个休闲广场。凡是在这里生活学习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引以为傲。“瞧瞧,这里可是前省长的亲笔题名。”他们会这样指着告诉你,“再走走,这东南西北有三峡景观区、绿色艺术园、文化商业街和名人雕塑园呢。八万平方米,够大了吧。”所以,连葛洲坝微缩景观上、丰都的情人桥上都站满了不少人,有时,夜晚也会放上一两部水幕电影,比如《虎口脱险》、《出水芙蓉》,尽管色彩、画质都十分勉强,但仍然被观赏者包围个水泄不通,棒棒们也不做生意了,三三两两地看着,谈论着,找到了打牌喝酒之外的新乐趣。偶尔有一两个老外驻足,但他们更好奇的好像是这些看热闹的人,穿梭的人,他们对松城人的兴趣远远胜过广场上的流水、小桥以及三峡大移民的雕像。
宋菌在广场中心的擎天柱标志下环顾了三圈,终于发现了位于东南夹缝方位处的梨人宾馆。“三星级的,梨人宾馆二楼。”名流在电话里这样说。
他并不想这么快见到她。但宋菌已经坐在了名流的对面,只有憨憨地笑。
“我还没做好准备。”他没想到电话留言的第二天,名流就雷厉风行地做了决定,她饶有兴趣地要求能在当天下午采访。宋菌慌了神,突然结巴起来,拒绝和请求一样难,他把头埋在和电脑桌同一的高度上,然后不断地弯下去,弯下去,从侧面看,他似乎是一条往陆地上凿水井的金鱼,嘴里还咕哝着吐着看不见的气泡。
“不行,明天我就要去横店。明天上午的飞机。”名流补充。
“这,这可真为难。”他真想不出一个好的托词。
电话那头随意地笑起来,“不为难,”她的声音嗲起来,“我请你吃午饭,我们随意聊一聊。”
于是,他们约在一家三星级宾馆吃自助餐。考虑到吃相不雅,宋菌没有通知摄影记者。名流肯定了他的想法。“我会传给你我最新的照片的。”
开始名流谈的是她的童年,她的奋斗历程,她试图幽默,但宋菌总是跟不上节拍地笑。为了消除名流对他的误解,宋菌及时地赞扬了这里的食物。然后名流又谈到了社会环境、治安一类的公共问题,几次宋菌要掏出笔记本来记录,都被名流随手递过来的一牙西瓜或一只熏鱼打断。“要用脑子。”名流想了一会儿说,“成功的人都用脑子。”宋菌只能抽空记下两三个字。他的盘子里堆满了食物,清单和油腻搅在一起,跟他脑子里杂乱的头绪一样。他需要一支钢笔来清理现场,但他没胆量把它像筷子一样抽出来,肆无忌惮地使用。他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备受煎熬。而名流已经在餐台和饭桌前往返了好几次。她不再年轻了,却有一种漂亮的气势,让宋菌十分紧张。他一双眼睛在她身上流转,却什么都没看进去,心里怕得要命。末了,她很有条理地说,我吃好了?你呢?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宋菌吐了一口气,合上笔记本,“我能不能吃了再走?”他指指那盘食物。尽管有好几个问题他没问明白,他也不在乎了,反正已经完蛋了。
七
再来杯果汁。德克士里灯光明亮,音乐轻松欢快,有几个小孩在近处玩滑梯。
重新采访!宋菌把果汁递到莫巧巧手边,心里充满怒火。
如果没做好,只有重新做了。莫巧巧举重若轻地说。好像她的一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不是那样的。宋菌摇头,不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莫巧巧笃定地说。
他也为难过你?宋菌把头别到玩滑梯的几个小孩身上。
莫巧巧点头,她也看小孩。太吵了。她说。
什么?宋菌抽抽眼镜,往身后一靠,哦,那什么,就别做了。
莫巧巧并不看宋菌,只望着宋菌身后的空位子。
你害怕?
没有。
你为什么不害怕?宋菌向前一靠,发出炯炯的光芒,他太生气了。
莫巧巧一慌神,眼皮也不利索了。
你为什么不害怕?
你的眼镜脏了,我给你擦擦吧。她说着就摘了宋菌的眼镜,摸出一张餐巾纸,擦了起来。光线放闸般突然而至地跑到宋菌的眼睛里了,他不适应地紧闭着,一种钻心的疼痛,他一点都不害怕,紧紧地闭着,直到有一点液体渗出来,他才眨巴眨巴打开视线,眼镜又回到脸上了。浑浊的河水又清澈了。
好孩子,他抓起莫巧巧的手,说不出多余的话来。
莫巧巧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既不抽出手来,也不答应什么,她笑笑,完全知道自己的表情都尽在宋菌的眼里。
太亮了,他——宋菌把脏字吞下去,站起身来,耳边响起蓝河水的声音,哗哗哗哗,他现在要奔过去,要快要有力,要抓住来之不易的瞬间。
几个小孩突然跌了一跤,哇地哭出声音来,他们顾不上张望,对望了一眼,肇事者般逃逸了现场。
八
离开宾馆后的莫巧巧回到了律师事务所。她不能做到和往常一样,冰冷的职业装也不能给她过多的掩饰。她看上去更冷了。
律师事务所的墙上写着“热情服务,顾客至上。”莫巧巧用鸡毛掸子掸了一下上面的灰。朱律师从办公桌里出来,手上拄着一只拐杖,他走路的姿势很不好看,让人心酸,脑袋像个土豆,不合比例地种在身体上。他并不喜欢坐轮椅,可以的话,他愿意多走走。莫巧巧的另一个工作就是帮他叫一辆车,当然,她不需要送他回家,她也完全不必替他做这些事,但莫巧巧还是这么做了。待人接物是实习生的必需课程,这一点上,她显得很成熟。
今天她好像忘了这样的事,她想在事务所里多待待。只要愿意,总有做不完的工作。朱律师是这么引导她的。
我应该给你开点工资才是。朱律师站在她身后有一会了。
嗯?莫巧巧转过头来,她的眼神天真,毫无杂念。
朱律师盯着她,饶有意味,她在这里打磨得很快,短短几个月,他不得不刮目相看。
我应该给你点报酬。朱律师用拐杖点了下地板,他像是对自己下命令。
她看着他,无所畏惧,也无所求。
春天来了,去买点漂亮衣服。
她笑笑,像一个女人对着男人,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得意。他不就是个男人吗?此刻她这样想。
想不想和我去出庭?她的笑,让朱律师有了思考的空隙。
可以啊。她的语调并不太热情。出庭,尤其是婚姻案件的出庭是绝对隐私,实习生是不能进入的。也许这是朱律师众多诱饵中的一个。“我也就这么点爱好。”在一次酒会上,他对同行大言不惭地说,甚至没有避开她。他以为她离开他不行?现在,她真的离开他了,莫巧巧想起下午干的事,那个眼袋浮肿的男人,让她终于抵制住老板的诱惑了,尽管是以这样的方式。
你也知道我这里的条件的,我对你算不错的了。朱律师点点头,三个月了,这女孩居然不上路,这真有些伤自尊。他有些自顾自地说话,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
她放下鸡毛掸子,我还是给你叫车吧。她说。现在莫巧巧不觉得什么是难的。她搀扶着朱律师到路边,天还未黑,公司里就他俩,他们完全可以去吃一顿什么,就像他时常邀请她的那样,然后再听他说上一两段男男女女的事,而她,不是也有了可供对话的资本了吗?她可以比以前更加轻蔑地吃这顿饭。几辆出租车擦过身边,里面都坐着人,这个时间段里出租车是很不好打的。 他们必须要耐心等待。不一会街道就空落了,对面的榕树下有隐隐几个走着的灰的人,一切都毫无特色。如果这时朱律师说一个笑话,她一定会哈哈大笑,笑出泪来。可是没有。她就这么静静地等待出租车,情绪低落到极点。她也不想给那个大眼袋男人打电话,可是工作还是要做,她想赌一赌,他是否真的熬得过,她自己能不能熬得过。但朱律师没有邀请,那颗土豆脑瓜子上的两个黑珠子比什么时候都转得精明,他没发出这样的邀请,直到一辆显示空车的出租车在他们面前停下,他也只是满腹心思地望了下莫巧巧,扬尘而去。
大街又空落了,莫巧巧不是滋味地站在门口,一阵心酸涌上心头,她没有打败他,这个土豆脑袋,连平手都不算。
九
日子平静得可怕。
高高的天花板上,高脚蚊子静伏不动,所有的物体都像标本一样,死了,徒有其表。室外的阳光光芒万丈,可是这些和他有什么关系。他不需要和莫巧巧见面,他为什么要和莫巧巧见面?
名流的电话要么不通,要么就是秘书接下的。“她会跟你联系的。”对方总是这么说。头头过问过两次,时间拖得太久了。最主要的是,这是个打翻身仗的任务。他必须要有所交代。一连几天宋菌在中兴路转悠,希望找到重新采访的勇气。却一无所获。三个星期后,他才意识到莫巧巧很久没跟他干了。他像无意间摸到密码一样,心里震了一下。
她的问答整理得很好,一丝不苟,他前几天都直接复制粘贴用了,完全不用操心。邮箱那头,好像不是某个人,而是一台自动问答机,流水线操作,是呀,他怎么就忽略了她呢?她的淡定让他升出一股不悦。他现在想起了,而且至关重要,宋菌一跃而起,这寂静的房子,要做点什么了!
阳光很刺眼,宋菌摘掉眼镜,这样他觉得光线没那么暴力了。在模糊的人群和树影里穿行,让他觉得充满了盲目的自信。他甚至还哼起了小调,一种踌躇满志的感觉袭上心来。他在三十三路车站旁的一个IC电话亭里给莫巧巧挂了电话,强大的噪音让他几乎听不清自己说的什么话。“你听清楚了吗?嗯,听清楚了吗?”他更像是说给自己听。
她应该会来的,尽管他不确定莫巧巧那头的回复,他还是去订下了一个酒店。这是中央商务区的一个酒店,价格不菲,闹中取静。能俯瞰整个CBD的繁华。蜿蜒的中兴路被中国银行的群楼遮挡,“得意不夜城”的招牌尽管在白天显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它鲜活的夜间景象还是不设防地跳进了宋菌的脑海里。“这里的景观是很好的,尤其是夜晚。”服务员用标准的普通话介绍,眼神一刻也没放过宋菌。宋菌被盯得不好意思,表演似的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百元大钞,要付预付款,宋菌心疼了一下,这笔钱应该是邮寄回蓝河县的,蓝河水像一艘筏子飘过宋菌的脑海,他看着服务员的笔,直到她递给他一张单子,他的脚步都还是有些迈不动。就这么定了,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堡垒是需要一个一个攻克的。现在他把单子和笔记本同时放在床头柜上,暖色的灯光泻下来,他有些晕乎乎的,想着是不是先睡上一觉,反正时间还早。但不知为何,他却努力克制这种想睡着的感觉,笔记本上那几个稀疏的字,好像那里藏着某个密码,他不得其解,嘿嘿笑了起来,眼皮却更加沉重。
四点十分,他取下A货的雷达表,决定今天不去单位了。
窗外看不见树枝,俯瞰下去密密麻麻的人头在做无序运动,那里有丰富的颜色和细节,但宋菌看不进去。他脱掉全部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到床上去,这是一张柔软的皮床,适合做爱。
你来!他对空空的四壁发出命令。
你来!他取下黑框眼镜,又轻声地命令道。
你来!他觉得还是带上黑框眼镜比较好。
你来!他带上黑框眼镜,坐起来念了一遍。站起来又念了一遍。他的头离天花板还有半人高的距离。
他有些困了,像被倒悬着,时间还过得很慢。不知为什么,一阵荒凉涌上心头,这么高,他想,鼻腔里竟然发出呜呜的声音。像蓝河县的风吹过蓝河,冬天,那里的冰窟窿就发出这样的声音。
你来!他冲着空房间大叫一声。难掩失控的情绪。
砰!砰!门房被敲了两下。
宋菌愣了下,像凭空被射中了两颗子弹,失神地站在原地。两秒钟,他回过神来,忐忑地光着脚去开门。
莫巧巧站在光线的阴影里,侧身进来,轻声地掩过门去。她什么话都没说,像只小老鼠快速擦过宋菌身边,熟视无睹地走到靠窗的椅子边,坐下来,安静地,审视地,轻轻地,好像她一下午都坐在那儿一样,时间从她身上流过,停止了。
你来不来?她对着黑暗里相距三米的男人清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