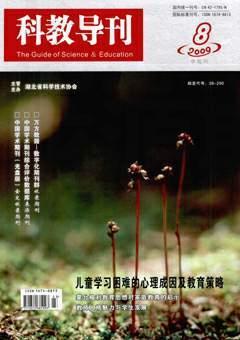课堂呼唤师生双方的自我意识
陶玉虹 刘春燕
摘要课堂是师生双方在交往中不断进行自我实现和自我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师生的话语方式既体现各自的自我认识又重塑着自我。关注课堂师生话语、关注课堂实践过程是解决课堂矛盾冲突,是推进师生主体性解放和自我构建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课堂话语 主体性 解放
中图分类号:G45文献标识码:A
从夸美纽斯正式论述课堂教学以来,课堂教学已走过了三百余年的历史。从传统的师道尊严、自上而下的线性单一的师生课堂交往方式,到现在所倡导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动合作,充分体现人本主义思想的师生课堂交往方式。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都将重心由教师转移到师生共同体,这给教育教学改革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存在方式的变化正是师生课堂话语权力矛盾不断调和的表现。
师生间课堂对话活动从外在表现形态上看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学习活动;但就其本质而言,它应是教师与学生基于教学内容和彼此生活经验对学习内容的探索和内化的过程,是师生双方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重构的过。显然,师生课堂话语过程是进行教育教学研究的有效方式。如果我们接受后结构主义“话语首位”(primacy of discourse)的观点,那么话语分析就成为对社会生活进行描述、解释、分析和批评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对教师课堂话语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确课堂中存在的矛盾,以便于寻找恰当的解决方式。教师与学生如何达成共同话语空间,是困扰教师的重要问题,教师就此问题具有清楚的认识,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的必要条件。
1 “老师”与 “同学们”——“自我”在制度中消失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H·米德的研究,“自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逐步发展的,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那整个过程的关系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可见,米德认为自我产生于社会经验。这种产生于社会经验的自我,必然在形成过程中同时也形成了批判性反思能力。奥地利教育家布贝尔曾指出:“具有教育效果的不是教育的意图,而是师生间的相互接触。”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教育的实践性本质。教育存在于师生的交往过程之中,同时,教师和学生的批判性自我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认识并进行着对自我的重构。如果教师不能意识到职业生活中是什么遮蔽了真实的自我,而只是盲从于占主导地位的行为模式,那么教师就成为了现状的维护者。
对话主体应敞开内心世界,平等相待,真诚倾吐、倾听和接纳。课堂应排斥话语霸权,教师、文本、好学生都不是权威;作为课堂对话参与者、组织者和服务者的教师,要从生命的高度、生活的视角及时捕捉、巧妙把握对话的话题,创设对话情境,搭建起学习群体探索真理、提升人格的生命场景和平台。这是我们对课堂话语的理想诠释。然而教学实践中的教师和学生的对话却常常让我们看到被异化的学生主体和老师主体。下面我们具体看一节课中教师与学生对话的实例:
(1)“刚才老师和几组同桌的同学交流了一下,我发现大家喜欢的自然段各不相同……”
(2)“那下面老师就有一个疑问了,既然你们那么喜欢课文的第二自然段和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一定有喜欢它的理由。那么谁来阐述一下自己喜欢课文第二自然段的理由?所有喜欢第二自然段的同学可以相互补充……”
(3)“老师可以补充他刚才说的话吗?”……
(4)“是因为老师笑你了吗?”……
(5)“老师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6)“请同学们齐读……”
以上是师生对话是作者在听课活动中选取的典型实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课堂中教师总是以“老师”而不是“我”的身份与学生进行对话。教师在课堂中对自我称谓的选择不断强化着对话双方的“师——生”关系,而不是日常生活对话中的“你——我”关系。 通过“老师”的使用, 使自己的发言和评价的话语权威化,使自己对儿童学习所作出的干预和控制得以合法化。在这样一种话语中,老师本人也被剥夺了私人的性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围绕知识的授受而形成。教师成了知识技能的占有者和代言人,从而适应了课堂中所特有的一种认知氛围: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和学生都被预先设定的“教学任务”或“知识”所限定,教师和学生都未能充分享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权力。
同时,“老师——学生”的课堂话语模式使得课堂中的个体之间人际关系淡化,重建了为适应于课堂而组织的制度性的人际关系。这种抽象化的“老师——学生”式的课堂话语模式对组织课堂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话语模式中个体的消失——不再是教师个体与学生个体间的对话,教师个体成为一种抽象化的角色;而学生个体则成为群体的组成部分,师生双方的个体性都被消减。教师在这个过程中遮蔽了真实的、饱满的、具有喜悦、孤独、兴奋、同情等情感世界的“我”的存在,而异化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化角色,进而拥有该角色所特有的权威。
2 关心——真实的“我”是否存在于课堂
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特有的对话构成了一个个新鲜生动的教育事件。同时,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对话又在不断地生产着教育意识形态。一切行动都在教师和学生没有觉察的情况下悄然进行。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实现自我,改变自我同时又在摒弃自我,再生成意识。
课堂应成为师生共同探索真理进行平等对话、享受主体自由的生命场景。然而课堂中却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着话语霸权和争夺话语权的游戏。提问,是师生交流中自然必须的语言形式。课堂中教师往往通过问题来检验学生的知识水平。本文作者在研究过程的一次听课活动中发现在一节课的68个课堂问句中,有15个问题完成了相同或类似的交际功能——布置任务或提出要求。该教师以问题的形式提出了若干不容置疑的要求,而值得注意的是学生所有的回答都是赞同、接受或许可。学生并没有对这些话题表达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这里,老师仅是以问句的形式表达了一连串的指令。“可以吗?” “好不好?”“行吗?”这些听似平等的商榷活动,并不能真正构建民主平等的师生对话关系。请看实例:
(1)T:我想把它读给大家听,可以吗? SS:可以。——要求学生听老师读课文。
(2)T:……依此类推,咱们接好,好不好?SS 好。——介绍规则,布置任务。
(3)T:在我们课堂发言的时候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好不好?SS:好。——提出规范要求。
(4)T:所以大家要多听好不好?SS:好 ——提出要求。
(5)T:你能不能用上颜色这个词来说说第二自然段的意思呢?SS: ……——提出要求。
……
从以上师生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教师完全控制着课堂的决策权,她所关心的不是是否能够与学生一起在课堂中深入探索某一话题,得出共同的理解,而是学生是否能够按“我”的要求走上“我”所引领的方向,达到“我”的期望。同时,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该班级的学生完全顺从于教师的安排——我们几乎看不到学生会关心“自我”的需要,学生对教师的要求都无一例外地给予肯定的许可。课后访谈中,教师对该问题的回答也是“课标要求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很明显这里教师已经把 “我” 视为一种完成教育目的的客体。教师所期望看到的是学生的表现“是否达标”或“达标程度”。可见,在该教师眼里,学生和她本人都不具备 “自我”的力量。
从本质上看,对话不是用一种观点反对另一种观点,也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而是双方的一种共享。通过对话,师生双方共享知识、共享经验、共享智慧、共享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对话是双方共同追求理解,同情和欣赏的过程,但是对话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探寻,人们一起探寻一个在开始时不存在的答案。教育是整体的、动态的,教师和学生在彼此的对话交流中解释着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认识。“在海德格尔的眼中,关心是人类的一种存在形式。他认为,关心既是人对其他生命所表现的同情态度,也是人在做任何事情时的严肃的考虑。关心是最深刻的渴望,关心是一瞬间的怜悯,关心是人世间所有的担心忧患和痛苦,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关心之中,它是生命最真实的存在。”然而,类似刚才这样的师生互动过程中,教师关心的是如何确立和保护教师角色在课堂中的权威地位,否认了教学是教育与知识的探索过程,否认了学生作为创造者的可能性,学生与探索过程完全割裂开。而学生则即不关心问题的真相也不关心如何推进问题——学生的主体力量被完全隐匿、遮蔽。甚至学生自己对他们所拥有自我主体力量也毫无察觉。 “教学是教师作为人的表达”,“教师不是永恒的并失去个性的相互替代的学术符号,受教师生命历程中的信念、价值、观点和经历的影响”如果教师自己失去了这种自我意识,那么教师就不可能对自我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成长始于对经验的批判性思考。在教学生活中,教师可能会越来越认可自我的教育角色,逐渐放弃了自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