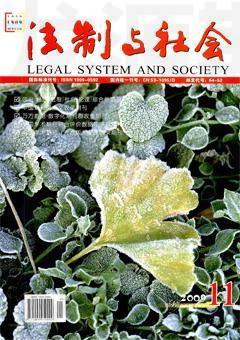对食品安全事件中董事损害赔偿责任的探讨
韩 烨
摘要 因我国关于董事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化、缺少操作细节而导致这一追究机制非常无力,本文通过对比借鉴我国三鹿案件和日本达斯金案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司法实践中很有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责任董事范围的确定、损失数额如何认定等)做出探讨。
关键词 董事责任 善管注意义务 损害赔偿额
中图分类号:D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1-347-02
一、引言
在所有与经营分离的现代公司中,董事在公司经营决策及业务执行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力,其作为公司执行机关董事会的组成人员,在事实上是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者。为避免董事因种种原因而损害公司的利益,规制董事的经营管理行为,现代各国公司法一般都规定了董事对公司应负的忠实、善管义务。当董事违反这些义务,就应该对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董事对公司的民事赔偿责任)。
很不幸,我国审判实践中追究董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这与我国对其的规定非常原则化、缺少操作细节有很大的干系。新《公司法》在第148-150条和第152条中仅仅笼统地作了一些规定,至于司法实践中很有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违法行为与善管注意义务之间的关系、责任董事范围的确定、损失数额如何认定、在何种条件下适用免责等却没有做出详细规定。
从2008年9月到现在,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事件就完全暴露出了我国对于董事损害赔偿责任追究机制的无力。而在邻国日本,无论是学说还是判例,对于董事责任制度的相关研究都非常先进。下文将介绍在日本影响巨大的达斯金违反《食品卫生法》案,对比三鹿案,提出问题,进行探讨。
二、达斯金案①的简要介绍
(一)案情
2000年10月至12月,A公司(达斯金公司)经营的唐纳兹门店贩卖的大肉包中添加了一种没有在日本国内得到许可的添加物——TBHQ,并一直隐瞒该违法事实。2000年11月,担当董事Y1和Y2决定给指出问题的交易方6300万日元的封口费。2001年2月,在董事会议上董事们知道该违法事实后没有任何公开的意思表示。2002年5月20日,问题曝光。5月31日,大阪政府对A公司做出行政处罚。2003年9月4日,公司以及担当董事Y1、Y2因违反食品卫生法被处以20万日元罚金(刑事责任)。此后A公司共花费大约105亿6000万日元进行营业补偿以及挽回公司信誉等宣传活动。社长和专务董事们辞职。股东们针对董事的不同责任,分别提起两个股东代表诉讼:(1)追究董事Y1和Y2的责任,因其自始至终知晓混入了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添加物却决定继续贩卖并加以隐瞒;(2)追究其他11名董事和监事的责任,因其事后知道这一真相却没有选择公开。
(二)法院判决
2005年2月,一审法院基于两名直接担当的董事Y1和Y2违反了善管注意义务而判处其承担 106亿24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责任,对其中一名事后接受报告却没有采取措施的原专务董事基于违反善管注意义务和与损害相适应的因果关系而课以损害的5%=5亿5805万日元的赔偿责任,对其他10名被告则不予追究。②
2006年6月,上诉审法院以“假设董事尽了义务,中止贩卖,公开真相,也同样需要花费一定数额来挽回公司信誉”为由,判处被告Y1和Y2承担53亿435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责任(一半损失额再加封口费)。对于没有参与隐瞒的其他11名被告,法院指出:这些被告在董事会上采取 “自身不积极地公开”的方针,没有积极地研究对策,是一种职务懈怠,违反了善管注意义务。故判处原社长和原专务董事分别承担5亿2805万日元和5亿5805万日元,其他9名被告则被处以2亿1122万日元的连带损害赔偿责任。③
(三)与三鹿案的相似之处
1.董事或主动隐瞒或“不作为”地让公司违法经营。A公司的2名担当董事自始至终都采取措施主动隐瞒违法事实,其余11名董事则一律“不作为”,没有尽到其监督的义务。同样地,除了三鹿董事长田文华等人积极隐瞒外,在董事会中不赞成隐瞒决定的少数董事选择了沉默,没有积极地公开真相。
2.事发前都曾有类似教训,但董事自信于以前成功的公关措施而做出错误决策。A公司早在雪印乳品中毒事件后就建立了风险管理体制。三鹿的自信则来源于四年前成功的危机公关史:2004年“大头娃娃奶粉”事件,三鹿位列其中,当时由董事长田文华挂帅,副经理蔡树维远赴阜阳斡旋,结果成功公关。
三、案件所折射出的问题
(一)关于董事责任承担者的范围
公司发生丑闻后,知情的董事们就负有立刻采取积极措施(直面损失、公开真相、减轻损害程度等)的义务,否则就是懈怠职责,违反善管注意义务。而事后出席董事会的董事们即使没有参与隐瞒,而是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其对于损害也要负担一定责任。这一关于“不作为”的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认定可以说扩大了董事责任承担者的范围,对于今后的案例势必会有极大的影响。联想到我国公司中那些不愿得罪掌权董事而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董事们,当这些董事知道违法事实,却没有在董事会决议上表明自己的异议而采取不作为——弃权或缺席时,是否要追究其对于损害的责任?
(二)关于赔偿数额
无论是一审还是上诉审法院,都对被告判决了惊人的赔偿数额。这说明对于食品公司而言,信用丧失是公司的致命伤;但也让人不禁要问:当公司固有的处理危机的手段也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时,将损害的全部归于特定的董事是否合理?是否可以基于过错相抵的法理适当地减轻董事的责任,减少赔偿数额?之所以三鹿的董事们迟迟没有公布反而选择强势隐瞒到底的原因,或许有一部分也可以归咎到集团本身一直在使用以危机公关来处理食品安全事件的体制上,至于能否以此减轻责任,则有待进一步证明。
四、问题的探讨
在探讨前,必须要明确一个前提:即在考虑董事责任时,仅从公司的经济利益来考虑是不够的,还应考虑董事是否顾及到了公司的社会责任,是否为使公司合法经营而诚实信用地进行了工作。公司作为重要的社会存在,应当对社会负有一定的责任,该责任的最低要求为遵守各种具体的法律法规;而作为控制公司运营的董事,应保证公司正当合法运营。即使是为公司利益,也不能使公司违反法律不当经营,否则应对公司承担责任。所以,董事让公司违反了其经营活动中应遵守的法律规定时,无需考虑董事的行为是否构成违反善管注意义务,而可直接认定构成董事损害赔偿责任。
(一)关于董事责任承担者的范围
对于承担责任的董事范围,从日本旧商法第266条第1-3款的规定来看,首先是直接实施违法行为的董事,当责任董事有数人时,则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董事责任的发生原因的行为是基于董事会决议而实施时,赞成该决议的董事将被视为实施了该行为的董事,须对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且,一般认为二者承担相同的责任;而参加了该董事会决议的董事,只要在会议记录中未记载异议,就被推定为赞成决议。若不能证明异议,就得承担相应责任。④
首先,笔者想要补充一点:虽然日本旧商法的条文中对于负有连带责任者之间的负担份额未作具体规定,但从前述案件中可以发现,判例对于实施了责任行为的董事和只是违反了监视义务而被追究责任的董事间的处罚作了区分,根据责任程度的差别,或者说根据损害事实和违法行为之间相适应的因果关系,对连带责任的承担份额进行了裁量。
其次,建议对我国新公司法第113条第3款进行修改——该条款虽然明确规定当董事违反义务致使董事会不当决议通过时,应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在实际操作方面却存在一个重大瑕疵:未明确规定董事在表决时投“弃权票” 以及因缺席而未参与表决是否属于“表明异议”。
弃权票可以说是一块规避法律使立法意图不能得到实现的灰色区域,针对此种情况,笔者认为应在原条款的但书后增加“在表决时投弃权票并记载于会议纪录的,原则上应对公司负赔偿责任,若该董事欲免责则对于免责事由负举证责任”的规定。
同样,缺席董事对于董事会不当决议的通过也要对公司负损害赔偿责任。之所以对那些既不参加董事会会议,也不履行一定反对程序的缺席董事强加法律责任,是因为董事负有监督和控制其他董事行为的职责,也因此,其要对公司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正如美国的博乐克法官指出的那样:“董事对公司的活动有持续加以了解的义务。董事不能对公司的不当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又主张,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公司的不适行为,因此他们对此无监督的职责。董事在自己的职位上睡大觉对他们有职责加以保护的公司并无什么好处。”⑤
(二)关于董事应支付的赔偿额的问题
1.损益相抵
假设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实施了违法行为,但该行为虽然给公司造成了损害,同时客观上又给公司带来了利益:或者不仅未给公司造成损害,反而给公司带来了利益;此时,董事还要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吗?能进行损益相抵吗?从确保公司守法经营、杜绝违法经营的原则来看,对损益相抵应持慎重的态度。应参照日本的做法,要求:(1)能够进行相抵的损失和利益必须是基于同一原则、同时发生且性质相同;(2)对违法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做严格的解释;(3)公司因违法行为所受的处罚及带来的名誉、信誉的损害应视为公司的损害。此外,我国的有关法律一般都规定,因违法而得到的非法所得应予以追缴或没收。因此,因实施违法行为使公司最终得到利益的情形应该是不多的。
2.应用过错相抵的规定
假设:董事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但却是继承公司的历任经营者的做法,或者是由于公司的组织及管理体制的深刻缺陷而引起的,即所谓的“起因于公司素质”或者如前文提到过的公司固有的危机公关手段,那么当公司本身也对公司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情况下,能否适用“过错相抵”的原则呢?从理论上看,在董事及公司对公司的损害都有过错的情况下,在追究董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时,是可以适用“过错相抵”法理的。但是,在董事实施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要证明公司本身的不良传统或低下素质对这种损害的发生也曾起过作用是相当困难的。同时,在上述情形下,还必须考虑到董事负有改善公司素质的义务。
此外,公司的其他董事或职员为尽职责行为也是损害发生的原因之一的场合,能否适用过错相抵法理?从董事之间对公司的责任为连带责任及董事对职员有管理监督之责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适用过错相抵法理也是很困难的。
3.将赔偿责任与报酬结合的可能性
当董事因其经营中的过失给公司带来损失时,完全由董事个人对此承担赔偿责任不仅是不恰当的,而且有时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任何董事都必须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的前提下,董事的赔偿责任如果远远大于其从公司获得的报酬,显然有悖于公平的原则。因此,董事败诉时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与该董事因担任董事职务而获得的经济利益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比例。而如何公平考虑两者间的合理比例,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①[日]北村雅史.違法行為の隠蔽による信用の失墜と取締役の賠償責任―ダスキン事件高裁判決の検討.商事法务.2007年第1803号.4-14.
②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号和登载出处:大阪地判平成16?12?22金判1214号26頁 (判時1892号108頁).
③二审法院的判决书号和登载出处:大阪高判平成18?6?9 判タ1214号115頁.
④马太广.判例所表现的商法法理.法律出版社.2004.270.
⑤张民安.公司法的现代化.法律出版社.2000.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