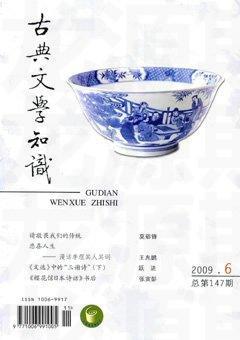瞿兑之及其《中国骈文概论》
李鸿渊
瞿兑之(1894—1973),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名宣颖,以字行,晚号蜕园。笔名甚多。现代史学家、文学家、画家。
兑之出身望族。其外姑为曾国藩“满女”崇德老人曾纪芬。其父瞿鸿禨,为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举人,次年成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后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曾先后典试福建、广西,督河南、浙江、四川等省学政。中日甲午战争时,上四路进兵之策,未被采纳。庚子之役爆发后,他认为“拳乱不可纵”,主张进行镇压。后升为工部尚书,并受命赴西安行在跪安,瞿因此深得慈禧信任。事后,入军机,充政务处大臣,又调补外务部尚书。1906年授协办大学士。1907年由于与庆亲王奕劻有矛盾,忤慈禧旨意,被劾开除回籍。与王闿运等吟咏结社,逍遥度日。辛亥,湘变起,流寓上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聘其为参政员,坚拒不就。1918年卒于上海,后追谥文慎。自撰有《止庵年谱》,另有《止庵诗文集》、《汉书笺识》、《瞿文慎公诗选遗墨》四卷、《使闽豫日记》等著述传世。瞿鸿禨官运亨通,耳濡目染之下,难免会给兑之种下热衷仕宦的因子,这从其后来的经历可看出端倪。而诗书传家的家风,又使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文化熏陶,为其后来的求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母傅氏,乃河南按察使傅寿彤之女。傅氏擅古琴,兼通书法、作诗,为一闺中才女。瞿兑之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清贵的书香门第。
兑之生于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二日,时为花朝。这年,其父始买宅于长沙朝宗街。他在此宅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少年时光。四岁即接受私塾教育。后来他在《故宅志》中有文字记载那段时光:“一生所得文史安闲之乐,于此为最。每当春朝畅晴,海棠霏雪,曲栏徙倚,花气中人。时或桐阴藓砌,秋雨生凉,负手行吟,恍若有会。”诗意的生活环境、充裕的读书时间给予了他茁壮成长的温床。这一时期,王闿运、王先谦常往来于其家,遂从二位文坛名宿求学。
1906年,兑之以第五名的成绩考入京师译学馆,主修英文、算学,旁及法、德、俄、意乃至希腊、拉丁等语言。1916—1917年,兑之三位业师尹和白、王闿运及王先谦先后逝世。不久,其父亦与世长辞。连遭变故,他并未一蹶不振。这段时间,他陆续翻译了一些关于介绍国外战争情况的文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其关心时事之状略可想见一二。1918年就学于圣约翰大学时,因能以英语与外国人对话,兑之曾代表上海大学生参加了“学生救国会”,并担任文犊,学联章程以及各种文稿多出自他的手笔。因此遭开除处理,随即转学复旦大学,仍担任学生代表。毕业后,因家无积蓄,又无经济来源,境况颇窘。为生计所迫,叔兄宣治偕同兑之及其妻聂氏于民国八年应荐北上,自此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
1920年,年仅26岁的瞿兑之即任职交通部,充路政司交涉科副科长、参事厅办事,兼国务院秘书厅佥事上任事。年少得志,激起了他“热衷”仕宦的热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次年,任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理顾维均的秘书长。其后还陆续担任过司法部秘书、京兆尹公署秘书长、国务院秘书、财政部管理总务厅事务、署印铸局局长、铨叙居帮办、国史编纂处处长、财政部盐务科稽核总所文犊股帮办、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务。以一读书人从政,并得如此重任,除得父荫之助以外,还得力于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谦和的处世态度。
1928年,兑之任燕京大学讲师,是为教学之始。此后,他先后任职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在南开大学时,他开设了方志学课程,此举发前人所未发,实为一大创举。后上海市市长还聘请过他及汤济沧、赵正平三人,为上海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专任委员,为通志馆的成立做了不少工作。
“七七事变”后,北平建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兑之滞留北平,改名为益锴,并任职北大监督,此为其人生一大污点,亦为他晚年之牢狱之灾埋下隐患。从其“暂学凫依渚,初逃雁就烹”之类的诗句可以推测,他那时应该受过日本人的胁迫,联系他文革时期的表现,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
1947年,瞿兑之流寓上海,自此开始了卖文为生的生涯。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谨慎小心。后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特约编辑,并为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虽曰点校古籍,但多不刊其名字。
“文革”中,瞿兑之受到冲击,生活趋于困窘。1968年夏,他以“现反”罪遭逮捕,判刑十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他未能及见玉宇澄澈之时,即瘐死狱中,时年八十。十年浩劫结束后,始得沉冤昭雪。(参尹娟,《班马志业,王谢风流——论瞿宣颖的文献学成就》,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兑之学问渊博,精研文史,于职官、方志等学均有深湛研究,尤精于掌故之学。幼年随宦长期居住北京,于京师建置数百年来的风土人情、街道变迁、人物景色熟悉无遗。现代治掌故者不少,最具功力的有三人,即徐一士、黄浚(秋岳)和兑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博闻强记、胸罗极富而又善于研究分析。徐、黄二人的著作均请兑之审读和作序,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兑之学养的信服和敬重。而兑之的序言不仅对《一士类稿》和《花随人圣庵摭忆》予以评价,更对掌故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和个中甘苦作了清晰的阐发。到目前为止,有关掌故学的理论探讨依然罕见,读《〈一士类稿〉序》仍有空谷足音之感。至于兑之自身的掌故学,较之徐、黄,又有所区别。除了著述更丰、分类较细之外,作为史学家,他善于将掌故学的成果运用于专题史(如地域史、风俗制度史)的研究;作为诗人,他的《燕都览古诗话》又能创造性地以诗配文的生动形式来谈掌故。此外,徐、黄均以文言写作,而兑之则有文言、白话两副笔墨,后者显然更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吴宓曾称赞:“兑之博学能文,著述宏富,又工书法,善画山水及梅花。合乎吾侪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文人之标准,兼治西籍,并娴政事。其于史学,则邃于史,掌故精熟。”(吴宓《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兑之著作繁富,有《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国骈文概论》、《方志考稿》、《秦汉史纂》、《汪辉祖传述》、《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注》、《养和室随笔》、《杶庐所闻录》等。喜藏书,斋名补书堂,其父留在老家的藏书均由其继承,并运至北京。抗战前夕,他将藏书1811种、59769卷寄存国立北平图书馆,该馆特编印《瞿氏补书堂寄存藏书目录》,以为感谢。
1918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在民国初年的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新文学思潮。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骈文研究的兴盛局面。民国期间,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孙德谦的《六朝丽指》、钱基博的《骈文通义》、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谢无量的《骈文指南》、金钜香的《骈文概论》、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和《骈文学》,此外,尚有蒋伯潜、蒋祖怡的《骈文与散文》等多部骈文研究著作。当时的学者们以为,骈文为中国所特有,且骈文和诗歌都是世界至美之文学。刘麟生以为:“骈文为吾国独具之美文,有其光荣之历史。”(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谢无量说:“中国文字皆单音,其美文之至者,莫不准音署字,修短相均,故骈文律诗,实世界美文所不能逮。”(谢无量《骈文指南》,中华书局1918年版)这些表述,带有明显的反文化殖民的味道。瞿兑之在《中国骈文概论》“总论”里也说:“中国语的特点在单音。因为单音的原故,所以用骈体组成的语句容易引起联想与美感。古经典的多用骈句,不外这个道理。”当然,骈文这种文体形式确实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是其他国家其他文字所不可能产生的。应该说,“民国初年的学者们首先注意到了骈文产生和生存的文化空间”(莫山洪《论骈文理论的历史演进》,《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此时的骈文研究者,大抵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学根基,或者是家学渊源,且对骈文情有独钟。瞿兑之就是如此。他“从幼年时代,亲从王闿运学作骈文,而清末的骈文家李慈铭及《骈文类纂》的作者王先谦,都是他的父执”(刘麟生序),“逮稍知读书,便嗜《萧选》,兼及徐、庾,以为天下之美在是”(瞿兑之《中国骈文史•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兑之时任南开大学教授,应刘麟生的约请而写《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为此书写的序中,引用了兑之给他的信。从中可知,因已有刘麟生《骈文学》在前,瞿就“决定不必作什么骈文的文学史,也不必指示什么骈文的作法。只要老老实实地介绍几个重要的作家,几篇传诵的杰构及其特殊的风格,并约略地将他们的前因后果指点出来。这就是使人能欣赏骈文,能了解骈文,能运用骈文的一个绝妙方法”。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来安排全书纲目的,“所以只分为若干题目,略略按他们的因果次序来说明”(《总论》)。
《中国骈文概论》,1934年世界书局初版,约6万字,为刘麟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丛书”之三。次年,收入刘麟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八论》中,仍由世界书局出版。1994年,海南出版社列入“人文袖珍文库”出版,易名为《骈文概论》,并附“外一种”——刘麟生《骈文学》。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将《中国骈文概论》收入《中国文学七论》。
全书分十七节,除总论外,按照骈文史发展的时间先后,选择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骈文现象来介绍。目录如下:一、 总论;二、 从《三百篇》到《楚辞》;三、 赋;四、 魏晋文与陆机;五、 骈文之论;六、 写景文与齐梁体;七、 书札文与徐陵;八、 《哀江南赋》;九、《滕王阁序》;┦、《文心雕龙》与《史通》;十一、 唐代之骈文与古文;十二、 陆贽;┦三、 李商隐;十四、 宋四六;十五、 清骈文;十六、 律赋与八股;┦七、 八股与骈文。
关于兑之对骈文的具体论析,下面略举几段,以窥一斑。
在“骈文之论”一节中,瞿以为:“寻常的见解,必以为论说一律非骈文所宜。因为论说是发挥义理的,而骈文以辞藻为重,为格律所拘,发挥义理,便有所不足。殊不知以骈文作论说,正可利用他的辞藻,供引申譬喻之用,利用他的格律,助精微密栗之观。”
在“写景文与齐梁体”一节中,瞿对《水经注》的文学成就评价很高:“郦道元恐怕是古今很少有的学者而兼文学家了。《水经注》这部书,在那交通梗阻图籍缺乏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着手的;而他不但叙述得那样有条理,并且能以敏妙的文笔,将一切景物活跃地描写出来,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部动人的游记,而并不是死板板的地理书。”
在“《滕王阁序》”一节里,瞿将其与《哀江南赋》比较来谈,很是贴切入神:“固然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作风,一篇文章更有一篇文章构成的要素。这两点合起来,方才成一个文学家的杰作。《哀江南赋》是沉郁之中写出来的,《滕王阁序》是急遽之中写出来的。沉郁所以缠绵而往复,急遽所以奔放而自然。庾信的作风本来缠绵,所以《哀江南赋》作于沉郁之中,格外作得好。王勃的作风本来奔放,所以《滕王阁序》作于急遽之中,也格外作得好。所以我们欣赏一篇美文,不独须了解当其作文时的一种环境,而且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要照作文章时之情景来读,方能彻底领略。读《哀江南赋》应该缓缓地读,读《滕王阁序》应该匆匆地读。”
在“律赋与八股”一节,瞿受到刘麟生的影响,也以律赋为骈文之别支流脉,认为“大凡一种文字,作成了一定格式,强迫人人仿效的,总不能好。八股文之所以不好在此,桐城古文之所以不好也在此,而律赋之所以不能好也不外乎此。再加以律赋的用途,大抵不离乎颂圣。请问颂圣的文字,能够发挥什么了不得的文学之美么?所以律赋,很不为学者所乐道咧”;并从押韵的角度,阐释清代律赋无佳作的原因是“到前清时代,还须将官韵的字,押在每一段的末一句,这无非是防弊的法子。法制愈严,所以自然的趣愈没有,而愈难作得好了。唐人的律赋,在《文苑英华》里收的颇多;明清人的赋,却多半不收入自己的文集的,也因为不足登大雅之堂的原故”。“对清代律赋这种贬抑性的评价,是当时的文化环境使然,也代表着一种主流的看法,这对我们今天的清赋评价还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孙福轩《清代赋学研究述评》,《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总体看来,该著篇幅不大,语言浅近,可以说是一部骈文史漫话,意在普及骈文的知识。虽然如此,它在骈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因为这样“以鉴赏之法传之于人”(《中国骈文史•序》),能帮助更多的人了解骈文,欣赏骈文,勿使之成为绝响。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