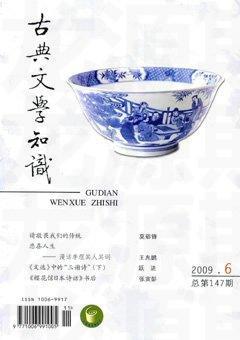请敬畏我们的传统
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确,无论是人文学还是社会学,人类都有许多殊途同归的思考,也得出了许多大同小异的结论。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首先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句话在《论语》中完整地出现了两次(《论语•颜渊》答仲弓问,又《论语•卫灵公》答子贡问),可见孔子对它的重视。无独有偶,在孔子身后五百多年,耶稣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难怪后世的西方哲人伏尔泰、托尔斯泰、爱默生等在推许孔子此言是道德方面的金科玉律时毫无心理障碍,原来在西方传统中也有类似的思想。那种对别的文化传统知之甚少便大放厥辞地予以全盘否定的做法,难免流于轻率。所以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批评汉语缺少辩证思维的词汇,不能像德语的“奥伏赫变”(Aufheben)那样“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故而不宜思辨,便受到钱钟书的尖锐嘲笑。钱先生在《管锥编》的开卷之初便举“易一名而含三义”的例子,指责黑格尔“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在今天,生活在地球任何角落的人们再也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由互联网构成的虚拟世界使我们能隔着辽阔的地理空间促膝谈心,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今天出席会议的老师和同学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却都对中国语言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大家欢聚一堂,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尽管如此,世界上毕竟存在着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因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不同的文化毕竟是在互不相同的背景中独立产生的,是在互不相知的状态下各自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们是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有朝一日我们地球人有机会与外星生命进行交流的话,文化的丰富性必将给人类带来最大的骄傲。
中华传统文化便是人类诸多文化中极为独特的一种。中华文化当然不是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自身便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大家庭,所以中华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相当复杂的演变过程。由于我们一向提倡宽容精神,一向把文化看得比血缘更为重要,所以中华文化具有比较强烈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很多民族冲突,但其最后结果往往是文化融合而不是种族灭绝。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曾与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发生过战争,但是中唐的大诗人白居易是汉代龟兹胡姓的后裔,与他齐名的元稹是鲜卑人的后裔,刘禹锡则是匈奴人的后裔,这正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一个精彩例证。中华民族与外民族之间也有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达摩西来,鉴真东渡,无论是接受还是赠予,都没有伴随火与剑的痛苦。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毕竟是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内产生的,它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文化,尤其是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性。比如说在古代的西方,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中国人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女娲、后羿、大禹等神话人物其实都是人间的英雄、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伟大人格的升华。中华先民崇拜的不是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而是发明了筑室居住的有巢氏、发明了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和发明农业生产的神农氏。当然,也包括与此次会议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汉字的发明者仓颉。所以在中华文化中,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忙于创立宗教时,中华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剂或愉悦感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用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差异如此之大的两种文化,它们之间有优劣之分吗?有高级与低级、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分别吗?没有。有的只是差异。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差异,承认这种差异,并尊重这种差异。我认为在文化上,任何民族的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都是同样的荒谬。
可惜的是,从近代以来,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出现了许多荒谬现象。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中国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打击下缺乏招架之力,许多人便把原因归诸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种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我首先声明,本人决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完美无缺,也不认同某位著名的老人有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预言,我也不相信中华文化便是根治世界现代化弊病的灵丹妙药。但是我反对把中华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反对有些“愤青”或“愤老”成天埋怨祖先却从不自责的轻薄做法。让我们把话题回归到此次会议的主题上来,说说有关中国语言文学的情况。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而言,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典籍。要是离开了汉字,我们如何能了解先人们几千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感?可是恰恰是这种至今仍然被超过十亿的人口每天都在使用的文字,曾经受到最严厉的批判甚至谩骂。在“五四”时代,钱玄同和鲁迅都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稍后,废除汉字的主张也差点由某些政治人物付诸实施。时至今日,随着形形色色的汉字输入法在电脑键盘上大放异彩,那种把电脑时代视为汉字死期的说法是没人再提了,但总还有人对汉字要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恋恋不舍。其实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相传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那真是先民们在发明汉字时惊喜心情的生动描述。要是没有汉字,神州之大,各种方言的差别又几如外国语言,操着各种方言的人们如何进行思想交流?要是没有汉字,我们怎能通过阅读典籍而理解祖先留下的浩繁文本?拼音文字当然有其优点,但是又何尝没有缺点?随着语音的不断变化,拼音文字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英国诗人乔叟死于609年前,可是今天的英国人或美国人中有几人能读懂乔叟作品的原文?然而我们现在来阅读《论语》、《孟子》,在文字理解上并没有太大的障碍,那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文本!如果真的强行实施了汉字拼音化,比如把我们的唐诗宋词都用汉语拼音排印出来让人阅读,不说美感的严重丧失,即使只求意义上的准确解读,恐怕就大成问题。况且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又如何全部转换成拼音文字?如果不转换,那么只认识拼音文字的现代中国人又如何能掌握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如今的韩国人中十有八九不能阅读本国的历史文献,就是我们实施汉字拼音化的一个前车之鉴。
况且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是维系该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利器。法国文学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为何那么感人?就因为它生动地刻画了即将被禁止说法语的一群阿尔萨斯人对母语的无比热爱。尽管有人指出事实上多数阿尔萨斯人本来就是操德语中的阿列曼方言的,但并不影响这篇小说的意义。英国人常把英语称为Sweet English,还认为英语比英国的北海石油更加宝贵。难道汉语、汉字就不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一定要用世界语或英语来取代汉语,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如今在中国热心推广世界语的人是基本销声匿迹了,但是英语热却达到了非同寻常的程度,在有些人的眼中英语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母语,真让人匪夷所思。有些当代诗人甚至声称他们从来不读唐诗宋词,他们只愿意从西方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我总觉得这就像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的荒谬。在我看来,除非你想用外语进行写作,否则就不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脱离关系。只要你用汉语进行思考,用汉字进行写作,中华传统文化就悄悄地渗透进你的文本中来了。因为传统早已渗透进汉语和汉字的深处,无论是词汇还是语法,都不可能摆脱传统的影响。即使你坚决不读唐诗宋词,难道能在写作中绝对不用成语典故?能绝对摆脱情景交融等传统写法?至于学术研究,更不可能与传统学术割裂。即使你能得心应手地运用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所提供的新方法,但如果你想在古代汉语研究上做出点成绩来,那就必须精读《尔雅》、《说文》等经典著作,必须熟悉“六书”以来的小学传统。
文学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文学史源远流长,这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从不间断地奔流了三千多年,而且三江九派,形成了庞大复杂的独立水系。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文学”的眼光来从外部来对它进行审视,但是决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贬低它。可惜的是,从“五四”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贬低、否定,几乎成为潮流。陈独秀大声疾呼,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严家炎先生认为陈独秀所说的“古典文学”实指“古典主义文学”而不是“古代文学”,但是“古典主义文学”就可以一概否定吗?即便我们把这里的“古典文学”狭义地理解为陈独秀深恶痛绝的明代“前七子”、“后七子”以及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魁等人,但是他们果真就像陈独秀所说的,是什么“十八妖魔”,非得彻底铲除而后快吗?周策纵先生认为陈独秀攻击的真正目标是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以及江西诗派的诗歌,前两者也即钱玄同所说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在五四的具体语境中,他们的主张其实是一种论辩策略,是为推行新文化运动而进行的扫除廓清,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就像鲁迅所说的,为了要让大家同意在屋子上开窗户,就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因为你不说掀掉屋顶,就连窗户也开不成了。即使是钱玄同与刘半农两人合谋上演“答王敬轩书”的双簧戏,我虽然觉得他们的做法不够光明磊落,但也没有太大的反感,因为他们的目的也与陈独秀殊途同归。但是掀掉屋顶的主张必然是一种矫枉过正,其自身的偏颇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今天从学理上进行反思,就必须指出上述贬低、否定古代文学的言论是相当荒谬的。可惜的是,从五四发轫的反传统思潮在后来愈演愈烈,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流论,到1949年以后的民间文学主流论,再到阶级斗争主线说、儒法斗争主线说,一部中国文学史简直被歪曲得不成体统,我们的文学传统受到彻底的颠覆。直到今天,只要打开某些中文系的学术网站,诸如“自大狂屈原”、“杜甫是酒鬼加混子”之类的帖子仍赫然在目。对于这种现象,大家当然可以从学理上深入探讨其原因。我在这里只想一言以蔽之:对传统缺乏敬畏之心!
与此同时,在学术界也有另一种现象,就是过于热衷于运用现代西方理论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而将传统的研究手段束之高阁。或是过于推崇西方汉学家的选题倾向和研究方法,甚至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这种现象虽然在表面上并没有像陈独秀那样否定中国古代文学自身,但由于背离了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其结果也会导致失去对传统的敬畏。我并不反对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哲学理论,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运用这些理论做出了较好的研究成果,闻一多先生运用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方法研究《诗经》、《楚辞》,就是一个范例。但是在总体上,西方的理论毕竟是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理论家在创立一种学说时很少把中国的传统放在归纳和思考的范围之内。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好像只有美国的苏珊•朗格曾经通过分析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来说明其观点。俄国的巴赫金的文集里倒有一篇文章论及中国的四书五经,但是仔细一看,原来他连“四书”是哪几本书都没弄明白,恐怕不可能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当然,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纯粹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发育起来的理论肯定也会有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容,而来自他者的异样眼光还会给我们带来新颖的解读和分析,这正可以证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然而不必讳言,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可以成功地移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来。植物的移植要避免水土不服,理论的移植同样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新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当时颇有人声称再不运用“新三论”,古代文学研究就要无疾而终了。二十年转瞬即逝,今天再来回顾“新三论”,仿佛黄粱一梦。
其实方法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既无需强分新旧,更难以抽象地判断优劣。方法的价值在于实用效能,在于它能否较好地解决问题。中国古代文学自有其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其独特的学术术语,这是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又何必要将它弃若敝屣?现代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又怎能事先就对它奉若神明?朱熹曾对禅师宗杲的一段话大加赞许:“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了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的确,手持许多兵器,逐件舞弄,往往只是花拳绣腿。正如《水浒传》第一回所写的九纹龙史进,身上刺着九条青龙,手里的棍子舞得“风车儿似转”,煞是威风凛凛。然而东京来的禁军教头王进用棍子一挑,史进便“扑地往后倒了”。为何如此?王进说得很清楚,史进先前所学的“风车儿似转”的棍法只是“花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拳绣腿”,它是缺乏实战效能的,它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说实话,我觉得如今学界的某些人正如当年的史进,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文章正是学术上的花拳绣腿。换句更文雅一点的话来说,他们正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学步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只好匍匐而归。试看近年来的许多论文专著,堆砌着许多时髦的新概念和陌生的新名词,但是对于其研究对象从文本到发生背景都不甚了然或所知无几,所得出的结论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这与寿陵余子的失其故步又有什么区别?
不过,我对运用西方理论颇存戒心,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此,而是担心另外一种结果:有些学者对西方理论有相当好的掌握,由于浸润太深,久而成习,就会养成一切都以西方的观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样一来,当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举个例子,据媒体报道,前年夏志清教授在美国发表了一通从总体上贬低中国文学的言论,其中有一句是:“唐诗也不够好,因为都很短。”先声明一下,我并没有看到夏教授发言的原文,不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属实。假如没有误传的话,这真是典型的数典忘祖!中国古代的写作,无论是文是诗,都以简练为原则,辞约意丰是千古文人共同的追求目标。陆机把其中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诗歌更是如此,唐诗中许多传诵千古的名篇正是篇幅极短的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无论是古人的诗歌写作,还是古人的诗歌评论,从没见过把篇幅不够长当成缺点的。我猜想夏教授是把唐诗与西方诗歌进行比较后才这样说的。虽然英国诗歌史上有一位名叫 Richard Crashaw的诗人,他曾写诗咏叹《圣经》里耶稣使清水变成美酒的故事,全诗只有一行: The modest Nymph beheld her Lord ,and blushed!但一般说来,欧洲的诗歌大多篇幅较长,反正其平均篇幅要比唐诗长得多。可是篇幅的长短难道是判断诗歌孰优孰劣的一个标准吗?夏教授虽以研究中国文学而著称,但大概在美国生活得久了,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欧洲文化本体论的立场上,所以指责唐诗太短。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中国文化本体论的立场上,那么马上可以得出针锋相对的结论:“欧洲的诗歌也不够好,因为都很长。”这岂不是荒谬绝伦?上述例子也许只是相当偶然的现象,但是还有许多事例也有类似的倾向,不过比较隐蔽,不易觉察而已。再举一个例子。台湾“中央研究院”里设立了一个“中国文哲研究所”,顾名思义,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是该所的重要研究对象。可是我们去查一下该所的资料,有人研究唐诗吗?没有。有人研究宋词吗?只有半个人。我说的“半个人”是指林玫仪教授。那么文哲所里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员都研究什么呢?几乎集中于明清的通俗文学,尤其是弹词。我不是说不要研究通俗文学,我也赞同某些学者把弹词作为终生的研究对象,但是弹词毕竟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重要的部分,犯不上让堂堂的“中国文哲研究所”的人员一窝蜂地集中在这个领域。我观察到文哲所的年轻人几乎都具有西方教育的背景,因此猜想他们的研究思路其实反映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从而漠视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
如果说从西方的视角来否定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空间维度的歪曲,那么另一种歪曲则源于时间维度,那就是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只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是只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博物馆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其实,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依然生机勃勃,它的内部蕴涵着巨大的生命力,它从生成之初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它是一只可以屡经涅槃而获得永生的凤凰。随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愈演愈烈,现代人更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举一个例子:人们常说中华传统文化重视群体利益而轻视个体的生命价值,其实我们的传统中何尝缺乏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内涵?美国人梭罗写的《瓦尔登湖》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人抵拒物质引诱的圣典,但我觉得庄子的类似思想要深刻得多,而陶渊明的诗歌则清晰地表明他比梭罗更能理解朴素生活的价值。德国人海德格尔说出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名言,但事实上像海氏那种热衷于名利、又与纳粹不清不白的人哪能真正做到诗意栖居?我觉得宋代的苏东坡的一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意栖居。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我们的传统一概加上“落后”、“陈旧”之类的恶谥?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着自虐的心态来否定我们的传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我们的传统保持必要的敬畏?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和烙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继续生存的根本理由。龚自珍曾语重心长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如果毀灭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结果必然会毀灭那个民族。在今天,像内藤湖南、白鸟库吉那样居心叵测地诋毁中华文化的学者也许不会出现了,但是对传统文化毫无敬畏之心的陋习依然会导致类似的结果,无论这种陋习是发生在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的身上。所以我想向与会的老师和同学们呼吁:如果你真心热爱你所从事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就请敬畏我们的传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お
编者按:本文采系莫砺锋教授于2009年7月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等联合主办的“中国语言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