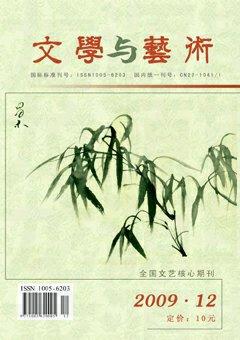简单故事的背后
【摘要】《彩虹》所叙述的故事很简单,毕飞宇通过睿智的叙述技巧让一个简单的故事充盈着意义。他从人的孤独感切入,直面人与人之间隔阂,在切入人们心中柔软的情感后,引领人们对人生进行反思,在简单的故事中写出了不简单的意义。
【关键词】毕飞宇; 《彩虹》
被评论者称为“短篇高手”、“具有短篇精神”的毕飞宇说:“我所渴望的短篇小说与经验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相对说来,我所喜爱的好的短篇似乎是‘不及物的。因为‘不及物,所以空山不见人,同样是‘不及物的,所以但闻人语声。有时候,我认为短篇这东西天生就具有东方美学的特征。东方美学是吊人胃口的美学……[1]”在他看来,好的短篇小说,就如同被“烤”了一下的羊肉,是能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短篇小说《彩虹》,是在“三玉”(《玉米》、《玉秀》、《玉秧》)之后,搁了好长时间后推出的短篇作品,据作者说是酝酿了一两年了。《彩虹》写的故事很简单,概括起来就一句话:“老铁与小男孩不同寻常的交往。”在这样简单故事中,毕飞宇是如何将其烤出味道呢?
毕飞宇写《彩虹》是缘于,“我的脑海里还有一个记忆,是一个孩子。他一个人站在商场的柜台边,(可能在)等待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许就在不远处,正悠闲地盯着架上的时装,一件一件地翻过去。小家伙很孤独,他孤独的眼神都是动人的。它会使你产生一种自作多情的冲动,想蹲下来,给他做爸爸。当然,情况远远没那么严重,他只是可爱罢了,有一点点好玩……[2]”由此看来,小孩子孤独的眼神触动了作者,在《彩虹》中,孤独感很自然地成为了毕飞宇所关注的“不及物”。他有意把故事中的人物设定为物质富有,却是亲人缺席的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儿童。两位老人老铁和虞积藻是退休的大学老师,而三位儿女,尽管都是成龙成凤,但是“大儿子在旧金山,二儿子在温哥华,最小的是一个宝贝女儿,这会儿正在慕尼黑。”老人想孩子时,只能对着四只分别被拔到了北京、旧金山、温哥华和慕尼黑时间的时钟,唠叨“吃午饭了”、“下班了”、“又吃午饭了”。房子住得越高越大,但是就如文本所描述的:“老铁就趴在阳台上,打量起脚底下的车水马龙。它们是那么的遥远,可以说深不可测。……老铁有时就想,这个世界和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看,站得高高的,远远的,看看。嗨,束之高阁喽”。言语中,充满了暮年的无奈与凄凉感。而小男孩呢?尽管出生于富有的家庭,却独自被关在家,无聊得只能用他的舌尖不停地舔玻璃,或是磕玻璃,感叹“生活真没劲”。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空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都市人的孤独感,由此可见一斑。
人物的无聊感与孤独感,为下文故事的发展做了铺垫,正是这种彼此的无聊感,才有了老铁与小男孩“不同寻常”的交往。从情节链条上看,这便种下了“因”的种子。在作者快节奏的叙述下,事件的发展一切都合情合理,但是细究之下却显现着作者苦心积虑的安排。作者有意把人物设定为衣食无忧的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而且还让虞积藻摔了腿,虽然住上高层却没有下楼的兴致,更让两位老人不安居,老囔囔着要到“地球上走走”,并且还预备下了高倍望远镜;又让小男孩谨记着要对陌生人保持着警戒,于是便有了下文老铁拿望远镜观察小男孩,小男孩在暗中窥探老铁,老铁吹泡泡吸引小男孩以至于小男孩的来访。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叙述都是有深意的,所写的细节都是为下文铺垫的,但也充斥了不少的巧合,有点“戏剧”的色彩。从逻辑层面上看,《彩虹》的情节发展,就像连环计一般,环环相扣,显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若按照传统现实主义来看,便有点失却自然。然而以“自然”来评判毕飞宇的小说,恐怕会遭到他的不屑。
就作者而言,毕飞宇并不认可“自然”是短篇小说的高级境界,他并不信奉传统的现实主义,他说:“现实主义是我非常鄙视的东西。那是没有想象力的标志。[3]”“我理解的现实主义就两个词:关注和情怀。……我指的关注是一种精神向度,对某一事物有所关注,坚决不让自己游移。[4]”。于是,在他的作品中,人的情感理所当然是他关注的中心。毕飞宇所感兴趣的“不及物”,其实也就是人的情感。在短篇小说中,毕飞宇向来喜欢挖掘“美满生活”中的不美满的情感,或者说不安分的情感。像《架纸飞机飞行》中的“我”,有一个和睦安定的家庭,但却突然萌发了“又想恋爱”的念头,渴望像表姐那样有声有色地爱一场。《元旦之夜》写了成功人士发哥,在大雪飘飞的元旦之夜,却陷入了精神的空虚与无聊之中,约来前妻,进行忏悔,“渴望再一次找回最初与妻子在一起时那种天陷地裂的感受”。《彩虹》也不例外,关注的是当下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中精神的孤独。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毕飞宇如何在短小的篇幅中展开这种孤独感,并且使这种日常情感具有普遍的真实意义。
短篇小说由于篇幅较小,在叙述时,既要直切事件的中心,又要在有限的文本中拓展出无限的蕴味。“一部真正优秀的短篇,常常饱含着内敛、迅捷、诗意、机智的叙事特质和艺术品性,并在有限的文本中蕴藉着无穷的审美韵味,让人们既可以充分地品味到语言自身异常丰饶的审美质感,也可以领略到作家在驾驭叙事过程中的灵动才情。[5]”短篇小说多是叙述“故事的碎片”,它不大可能具有很长的时间的长度,“因为它不可能依靠讲叙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故事来表达作家的理想,不可能通过对事件来龙去脉的大量衍说来呈现生活的繁复,它只能借助故事的某些片断直指叙事目标,通过那些饱含审美信息的“碎片”来完成作家审美意图的表达。[6]”这也就意味着,短篇小说需要很好地处理时空关系,把握好叙述节奏,在有限的时间叙述中拓展空间。
在《彩虹》中,涉略了很多事件,比如老铁和虞姬藻年青的事情、儿女成龙成凤的经过、买房子的事件、老铁年青时的“婚外情”等,对于这些事情作者常常是几句话,甚至是几个字就过去,小说的开头“虞姬藻贤惠了一辈子,忍让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来了个老来俏,坏脾气一天天看涨。老铁却反了过来,那么暴躁、那么霸道的一个人,刚到了岁数,面了,没脾气了。”这两句话就把两位老人的一生给高度概括了。在小说中,对于老铁和虞姬藻的过去及其子女的情况,作者的笔触都不作停留,点到即止。不过,在涉及到亲人情况中,唯一有稍微展开描述的便是那位讲德国话的小外孙女。而这一叙述节奏的放慢,一方面是为了下文老铁与小男孩的交往做铺垫,正是因为小外孙女的可爱,促使他们天然地喜爱孩子。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两位老人晚年的无奈,好不容易看到外孙女,却无法沟通。严格来讲,小说叙述节奏真正慢下来是从老铁站在阳台上看风景开始的。作者花了整整六大段的篇幅描写老铁与小男孩几个回合的暗中窥探,甚至还花了一大段的篇幅来描写高倍望远镜。作者如此地费周章,其目的在于要突显出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本来邻里间的老人和小孩是很容易交谈起来的,但是老铁和小男孩却彼此在暗中对对方观察了好几天,没有任何的言语交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普遍现象。“短距离本身并不是亲近;而大距离就其本身而言也不是疏远[7]”都市里时间和空间的缩短没有带来亲近感,人与人之间看似亲近却又虚无,看似熟悉却又陌生,就像“望远镜,它拨弄着距离, 拨弄着远和近,使距离一下子有了弹性,变得虚假起来,却又都是真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是在表面而是在心灵.科技尽管发达,但仍无法跨越人彼此间心灵的距离.至此,小说的叙述就获得了价值层面的意义,笔调从人的孤独感触摸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而这种距离感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造成的。
小说在关注人的情感时,并不是仅仅揭露出问题,同时也给出了答案。在小说中,随着小男孩的介入,老铁与虞姬藻变得越来越孩子气。老铁竟然也有些孩子气伸出舌头学小男孩舔玻璃,甚至还帮小男孩数嗑玻璃的次数,而且为了引起小男孩的注意,还去超市买了瓶泡泡液,顶着炎热的气浪吹起泡泡。而虞积藻腿脚不便却还要到处找热闹,还无赖般地吵着要去广场吹泡泡。老铁和虞积藻的孩子气在与小男孩的接触中逐步表露出来的。在与小孩子的接触中他们没有大人的老成与世故,反而变得小孩化.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回归了内心,在与童真的对话中找到了乐趣.虞积藻“无声地笑了,满脸的皱纹像一朵砰然绽放的菊花,全部挂在了脸上.她的眼泪都出来了。虽然躺在床上,可虞积藻觉得自己的两条腿已经站立起来了。这个小家伙真是个小太阳,他一来,屋子里顿时就亮堂了,虎虎有了生气。”小男孩的到来,使他们摆脱了精神的空虚,孤独的情感被幸福感所代替。在这样的幸福画面中,直面地透露出了家庭的温馨与可贵,提醒着我们应该关心一下留守在家的孤单的老人和孩子。或许在深层次也还启示着我们应该多一点的童真,少一点老成与世故,打开心扉与人交往。
然而,小说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孤独的老人与孩子的人文关怀上,小说的结尾提升了小说的意义。小男孩的一句“时间坏了”,足以引人深思。“时间坏了”这是作者有意留下的,小男孩在看到一排的石英钟里,时间不一,很可能会说“时钟坏了”而不是“时间坏了”。而“时钟”与“时间”显然是不同意味的。时间构成的多种可能性,也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多种可能性,甚至也构成了时代的多种可能性。“时间坏了”,坏了的仅仅是时间吗?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时代是否也坏了呢?我们不禁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人生,对我们的人生选择,对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进行思考,而不是快节奏地生活着,忙碌一生,到老时却还是感觉空虚。如同文本所描述的“要说他们(老铁和虞姬藻)这一辈子有什么建树,有什么成就,除了用‘桃李满天下这样的空话去概括一下,别的也说不上什么。”很显然事业上的成就并无法填补老铁和虞姬藻孤独感,他们想要的是孙儿绕膝的天伦之乐,却无法得到。也许在多年后,小说中缺席的儿女与父母,也会感慨生活的空虚。在现代都市里,人们每天紧张的工作,象机器一样不停的运转,追逐财富、权利、名利等东西,忽略了亲情、爱情、友情。而当人们获得的财富、权利、名利等东西在时间流逝中失去了意义,人生的价值便失去了依托,于是人们便不得不反思自己的人生。至此,小说的意义就拓展到人生的意义,而并不仅仅时都市人的孤独感。
《彩虹》所叙述的故事很简单,但是毕飞宇通过睿智的叙述技巧让一个简单的故事充盈着意义。他从人的孤独感切入,直面人与人之间隔阂,在切入人们心中柔软的情感后,引领人们对人生进行反思,在有限的文本中“烤”出了味道。在简单的故事背后写出了不简单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昆仑出版社,2002,32页
[2] 毕飞宇:《写一个好玩的作品》[J],《北京文学》,2005
[3] 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昆仑出版社,2002,27页
[4] 张均 毕飞宇:《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J],《小说评论》,2006年2期
[5] [6]洪治纲:《短篇是一种技巧的运动》[J],《上海文学》,2004年第2期
[7] 海德格尔,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56页
作者简介:杨素蓉 (1986--),女,汉族,福建师范大学200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