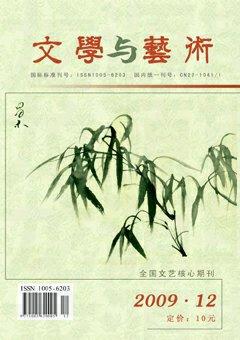中西女性主义诗学的背景差异
张 鑫
【摘要】由于,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的产生和成长不具有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得天独厚的学术背景,使得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只能是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横向传播、移植后变形的结果。因而与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和自己鲜明的本土特征。
【关键词】女性主义;诗学;差异
女性主义诗学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在欧美各国崛起的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模式与理论话语,它以对历史文化、文学现象、文学文本的深入反思与创造性阐释,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及对历史传统、文学乃至生活的既定认识。当代法国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代表人物之一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有一句名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别即使算不上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1] (P372)作为一位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露丝·伊利格瑞的表述显然不无夸张之处,但她准确道出了女性主义政治运动以及包括女性主义诗学在内的女性主义学说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领域与文化思潮中占有显著地位。
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女性主义不仅成为西方左翼文论的重要分支,亦与当代重要的文化理论相互借鉴,彼此声援。在中国,虽说人们一般以朱虹发表于1981年第4期《世界文学》杂志的《 美国当代的“妇女文学” 》作为中国学术界最早引介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标志,但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约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发端。1986年,西蒙娜·徳·波伏娃《第二性》中文版的问世,作为女性主义诗学进入中国的真正标志。从该年开始,翻译、介绍与尝试进行批评实践的文章不断增多,最终致使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在1989年左右达到第一次高潮。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重要契机,更使该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女性年”,女性文化空前繁荣。
随着译介的深入,学术界先后涌现了一批自觉借鉴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理论的与批评方法并努力使之与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现象的学者与著述,对中国现当代、国外文学乃至古典文学研究均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但是中国女性诗学的成长并不存在西方所拥有的那种得天独厚的语境。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拥有自己鲜明的本土特征,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敏锐的看到了这点。陶丽·莫依如是说道:“1984年秋,我对中国的短暂访问使我懂得一件事情:把西方的女权主义树立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权威不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任务。中国妇女在为把自身从她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英勇斗争着—在我声明与她们团结一心、并肩战斗的同时,我必须承认,我在这个领域并不能俨然以先生自居。”[2] (P3)
相比较之下,我们发现由于女性主义在西方和中国发展的背景与环境不同,其形态与重心并不完全一致,产生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也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直接受到了欧美历史悠久且波澜壮阔的女权运动精神的滋养,本身可视为女权运动在学术领域的自然延伸。它是以西方妇女长期以来对自身处境所进行的文化反思为基础,在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弗吉尼亚·沃尔夫、西蒙娜·徳·波伏娃、贝蒂·弗里丹等数代先驱人物的号召与推动下形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两次浪潮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为女性主义诗学奠定了强有力的历史文化基础,妇女文本则以对女性生活和情感体验的丰富表达,为研究妇女文学的历史、传统与美学特征,反思文化观念中的性别歧视,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20世纪西方文论的多元发展,又为女性主义诗学提供了多种思维模式与方法论的参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诗学是西方启蒙思想烛照下理想精神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与西方女权运动反抗父权制的鲜明目标与决绝姿态相比,诞生于列强觊觎和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背景下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自始就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血肉相连,成为有关阶级、历史与民族的宏大叙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五四以来由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男性先觉者首先倡导妇女解放的独特背景,1949年以后执政党有关男女平等的行政立法,使男女平等的观念普遍超前于女性群体的思想觉悟水准和社会普遍的心理认同程度,成为一篇华丽包装的官样文章。父权制文化背景先在的决定了妇女解放具有先天不足的不彻底性和依附性,女性群体和个体宿命式地被男性解放者居高临下地设定于接受启蒙的位置,并被局限在“为奴隶的母亲”、“党的女儿”等空洞的能指和“妹妹找哥泪花流”的行为程式之中。其间,中国妇女被他者决定命运的被动状态始终没有获得彻底改变。她们因之缺乏个体与群体的独立意识,缺少对女性文化传统的认同,将解放自身的愿望寄托于社会及男性的恩赐。20世纪30年代以后民族矛盾日益严峻、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情境,更使中国现代史上昙花一现的“启蒙”主题隐退为背景,“救亡”主题凸显于历史的天幕。涵盖于“启蒙”主题下的女性解放问题再度被搁置。正因为此,中国学者刘思谦激进地人为:“中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3]
1949年以后,行政律令下“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深入人心,以及“大跃进”与“文革”期间令人匪夷所思的“铁姑娘”现象的出现等等,有时人们在盲目乐观心态的支配下将妇女问题视为过去,仿佛再提此类问题已不合时宜。女性不得不以压抑自身的性征与心理感受为代价以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新时期以来,虽然五四启蒙传统得到接续,但科技的发达与物质的富足又激发起社会的普遍对金钱和物质的欲望。在商品泛滥和物欲横流的的背景下,是女性为性对象的封建主义沉渣再次泛起,女性再次被推入物化的陷阱。
傅立叶指出:妇女的解放是衡量一个时代人类解放的尺度。从这个意义看来,中国的文明发展形态就整体水平而言尚未达到自然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阶段。女性主义要成为中国公众普遍的自觉还有待时日。作为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人们普遍认识水平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观念在中国只能局限于高等学府、科研院所中部分开放的知识分子和女作家的范围之内。而且,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浸润,中国知识群体中虽不乏对女性主义或妇女解放持欢迎、理解和同情态度的男性与女性知识分子,但愿意公开亮出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却不多。以上所述,便是女性主义诗学进入中国并逐渐展开的过程中无可回避的背景与现实。
由此我们得知,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的产生,只能是西方女性主义诗学横向传播、移植后在中国土壤的变形。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磨合,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期待与知识结构对立与错位之后形成,并受到中国本土妇女问题的独特性所制约。它在横向传播与发生影响的过程中,势必会不断产生意义上的损耗、术语理解上的分歧、形式上的变异。译介者自身文化心理、知识结构与理解兴奋点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国情的需要等,又可使其意义不断被发挥而产生增值。这就使此女性主义与彼原汁原味的女性主义必然并已然大相径庭。
【参考文献】
[1]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3]刘思谦.关于中国女性文学[J].文学评论,1993,(2).
[4]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