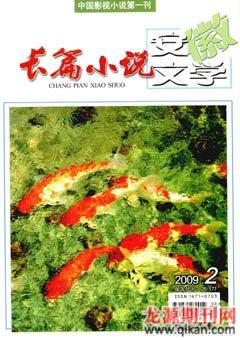那年夏天
邢思洁
入夏后,雨来雨去,惠济河水涨水落,老河湾里的野草比岸上的庄稼长得都高出一头,能把小孩和马驹淹没。清明时村民在坡上点的瓜豆,大水一过,只剩几根细细的汗毛。河湾很静,散发着瘆人的腥气。高粱因为个子高,还在水泊里露个红头,寻食的褐色斑鸠在上面叮着,边吃边咕咕地叫唤,声音古老而悠远。
爷爷从小受苦,没有机会读书,是个瞪眼瞎,后来被磨成了沉默的庄稼汉。他生活的所有乐趣就是劳动,他信奉“劳动光荣”,他经常忆苦思甜,告诉我们能够种庄稼填饱肚皮,得感谢毛主席。爷爷人老心红,各色奖状把草屋的山墙贴满了。其中一张就是淮海战役老部队奖励的,爷爷淮海战役时参加了担架队,曾是担架队长呢。等他带着大红花回来,被任命为村里的饲养员。最让爷爷骄傲的是,他带的担架队救解放军有功,老部队奖励他一匹退役的军马。
我们割草是因为村里的枣红马要生了,爷爷说枣红马是军马的后代,一定要养好才能对起老部队,听说母马吃青草可以壮奶,就计划着等到了晴天去割草。我放了暑假,就自告奋勇陪爷爷去。
尽管由于激动,我一路唠叨着问这问那,爷爷不语。“水大了鱼都能淹死。”这是爷爷路上所有的回话,还带着哲理味道,让我揣摩不透。
我们出发得早,太阳刚发威就到了老河湾。上次大水退去有一段时间,地上淤泥泛滥,鱼虾沤成了有机肥料,水洼中冒着热气,水泡连串,升起,爆炸。各种花草疯狂地长起来了,姹紫嫣红的,引来很多小鸟,有的飞翔,有的走动。爷爷是多么高兴啊,因为他的眼里尽是枣红马吃的上等草,好像枣红马下了驹,后腿间的奶袋子下着瀑布般的乳,一匹小马驹欢蹦乱跳的。
我问爷爷你笑个啥呀,爷爷说好草好草啊!
爷爷立即投入了劳动。
我只想玩,脱了鞋用麻绳系住吊在肩上,蹚水寻找滞留在水洼泥窝的鱼虾。走过浅水,感觉水底是滑腻的绿绒,踩着滋滋响,像蛇发出的叫声。能够残留下来的鱼儿都很小,不打眼。上次涨水,这些小鱼虾像是一群贪玩的孩子,在大水退回河床的时候,它们忘了跟妈妈回老家了,现在回不去了,只能在水里焦急地游动。
阳光浓了,水洼变热,鱼好像在冒汗,汗珠儿是连串飘起的泡泡,呼噜噜地往上鼓。我想抓几条,一伸手,鱼儿沉下去了,有的干脆钻泥里不动了。我用脚搅拌几下,泥浆翻上来,水浑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爷爷有条扎腰的纱布带子,长有丈余,无论冬夏都扎在腰上。爷爷的上衣从不用扣子,就用这带子扎,把人分成上下两段,是典型的清末农民打扮。我知道纱布可以做网捕鱼,要爷爷借给我用。我玩一会儿,也没有捉到什么鱼,捉了几只带尾巴的小蛤蟆。小蛤蟆个个哭丧着脸,可怜巴巴的,长满类似青春痘的小脸疙疙瘩瘩,像受气的小媳妇,我把他们放出来,唧唧哇哇跑了。
爷爷累了,脱下黑粗布衫放在草尖上,敞了怀割草。他弯腰驼背,左手抓草,右手拉镰,大汗淋漓。坏水易滋生蚊蝇,蚊蝇和飞蛾黑雾一般,一团团扑来,一抓一把。我被叮咬得无法忍受,爷爷却沉浸在割草快乐中,对叮咬视而不见。在镰刀的沙沙声里,野草一排排地倒下,爷爷顺手把草压成束,一溜朝西搁着。他六十岁了还很麻利,一会就割出了一条马路,风沿着马路吹进来,整个河湾沙沙地响,变得凉爽起来。
看到割下的嫩草成了堆,爷爷高兴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来:“割草,割草,割个元宝——嗷!”隔着密密的草棵子,爷爷竟然在唱。
我恋着捉鱼,只割出了一小片空地,捉不到鱼,又去捉草地里的蝗虫和蜻蜓,蝗虫多是刚会飞的幼虫,随便追几步就追上了,捂住,用草系住脖子。我仔细看看,竟发现蝗虫也是美丽的,头像骏马的头,我开始喜欢了蝗虫。我看到有不少蜻蜓,蓝的、红的、黄的,都很漂亮,它们结伴飞动,姿态优美,累了就歇草尖上荡秋千。有一种细细体型的叫豆娘,最浪漫,谈起了恋爱。我悄悄过去,捏住了它那晶莹的尾巴。
“都是个命。放了它吧。”爷爷对着得意洋洋的我喊。
太阳毒起来。河湾里没有大树,只有几棵杞柳。杞柳是农民祖祖辈辈编篮子用的条子,也是一种微薄的经济来源。几棵像样的大树都在岸上,远望如乌云一样,风和阳光在树头上不停地朝下跳,像透明的松鼠。由于太阳近似直射,割下的草叶子立即蔫了,整个草地像个大火坑。爷爷已割进了草地深处,牛虻多起来,蜇人。我想,爷爷怎么不怕呢?
我不好意思去乘凉,是因为我割的草太少了,我怕爷爷说我懒,因为我已经是个学生了。我必须努力,等割到一丛高高的牛草旁,发现牛草遮着了阳光,在地上形成一带荫凉。我有些困了,躺在荫凉里就睡。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等醒来,爷爷沿割出的“大马路”昂首挺胸走过来了。
肯定爷爷知道我饿了,但我们讲好中午不回家吃饭的。我们开始野炊,爷爷就地挖了个土窑,准备烧红芋吃。看到了土窑,我很兴奋,知道有吃的了。爷爷说到岸上扒几块红芋烧吃吧。我们当地的风俗是,扒红芋就地烧了吃,不算偷,行人饿了都可以烧个红芋吃,但不能往家拿,一拿性质就变了,就算是偷了。
红芋地在远岸上,隔着一片高粱地。红芋喜欢暴晒,墨绿的叶子在太阳光下放着青光,很有精神。有几只蝈蝈在与红芋地接连的豆田里嘶鸣,时近时远,隐隐约约,像是风刮似的响,又像一个孤独的少女在唱歌。风也没个正性子,东南西北地刮,让人摸不清方向。
我跑上岸,到树荫里站着,还看到不少鸟儿在树叶间休息,见了我“轰”地飞起,投向了河南岸。树上有蝉,唧唧鸣叫着。我跑进红芋地扒红芋,一连扒了几棵,弄出来的红芋都老鼠一样大,个个贼头贼脑的。我把红芋拢在肚皮上,一溜跑向河湾里。
爷爷很会野炊,就把红芋驾在土窖上,用干草烧,青烟冒起来,飘飘荡荡。我望着细长的烟浪,想起一句话——“晌午顶,鬼露影。”我好像看到烟里边有一个精灵,突然产生了恐惧。
我问爷爷,真有鬼吗?
这可是个问题,爷爷不能轻易回答。他若有所思,说可能吧,不,一定有。我问什么模样,爷爷说不清楚了。
烧好窑,太阳已偏西了,爷爷砸了土窑,闷住红芋,拉我去洗脸。他说洗净了手就吃闷面的红芋。
爷爷总不闲着,顶风割起草,在烟雾中像个仙人。我不时地抓脸,灰在脸上被汗浸湿,用手一抹,活像小鬼。我手伸入水里捧水洗脸,感到河水卷起泥浆流得很急。我在水边插一个棍子作标,一会儿棍子淹到了水中。
看起来水在急涨,河心的水头像箭朝东飞窜,河边聚集了不少水蚤,这是涨大水的征兆。
我喊爷爷。爷爷把手插入水中,一摁一抬抓出一条木梳大的鱼来。“有鱼?涨大水——要翻河了!”他对我说。
这正是村民午饭的时候,河湾极静,老远不见人影。我听得很清,爷爷说要翻河了。河水浑浊,流速加快,如万箭齐发。河面在扩大,形成巨大的漩涡,树叶、草棵子等被旋下去。
我的脸还没洗完,人已在水中一半,脚四周有鱼在窜,腿被调皮的鱼秧子咬得生疼。还有透明的白虾,长须都扬出了水面,像水草根一样扬着。一捂,就有一些虾落入掌中。
“是要涨大水了。”爷爷迎着浪头忧郁地说。
我们不割草了,我们逮鱼吧。爷爷像个孩子喃喃地说。爷爷拎起扎腰的纱带,纱布抖开飘成了一面旗子,在河面十分耀眼。我抓住带子的一端,爷爷拽住另一端,摁入水中,然后朝外慢慢拢,鱼虾多得打手。有条大鱼落入沙带后像个跳远运动员,跳起来出去了。等我们拉到岸上,剩有几条小鱼,白白亮亮的,甩着尾巴瞪着小眼。一连捞了十几网,捞了一堆小鱼虾,在沙地上虾爬鱼翻。我就地挖个沙坑把鱼虾放到水中。我们连续地拉网,等有了一些鱼就倒入水坑。
爷爷捞鱼时不像我这样快活。他不停地催我放了那些小鱼,还说鱼糟虾死是人在作孽招罪。我只顾捞鱼,像农民在喜摘丰收果。
河水更急更快了,泡沫浮了一层,一种叫卖油郎的黑色水虫划着长腿在水面上飞跑,聚集起来靠到岸边,像躲避风浪的黑色渔船。不少小鱼开始晕头转向地翻,层层漂水上,像沸水锅里的饺子。大鱼多像喝了酒的庄稼汉,东倒西歪的,我一伸手,它就下沉,停一会儿又升上来了。
有块门板从上游过来,上面竟趴一头小白猪。小白猪见了我眼泪汪汪地求救,我伸出小手,可是小猪刚跳下门板就被水冲走了。我没有救下可怜的白猪,又去救两条好像满月不久的小狗。小狗连同一个柴垛一起漂着,小狗呜呜地哭。我没有办法,爷爷踩水过去了,双手举起了小狗。
我看见了一条红鱼,大概是鲤鱼,红尾巴像旗子在摆,起起伏伏,大概不行了。我扑去抱,被它朝脸上打了几尾巴,我眼冒金星,倒在水中。
昏昏的我被水冲走了,感觉沉沉的,嘴不停地灌进水,像一个敞口容器。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会儿轻如鸿毛,一会儿重如泰山,一会儿上天堂,一会儿下地狱的,像条半死的鱼,我已经不行了。
过了好一阵子,爷爷没有看到我,才反应过来。大喊:“我的孙子没有啦!”
爷爷看见了水中的我,拿个长木棍追赶。一个岸上跑,一个水中漂,我们像赛跑一样。眼看完蛋了,也是命大,最后我被一排柔韧的芦苇挡住了。爷爷踉跄着过来抓起我,像捡了条死鱼。爷爷由于激动泪水涟涟,提住我的小腿摇晃,一股臭水从嘴里流淌下来,足有三大碗。我“哇”地哭起来,人活了。爷爷嘿嘿地笑了,把我朝背上一甩,背起来走向刚才割草的高地。
我迷迷糊糊地趴在爷爷黑胶泥一样的背上,嗅到了汗味和鱼腥气。我勉强睁开眼睛,看到爷爷背上尽是些新老伤疤,密密麻麻,地图一样。爷爷老了,心酸的日子、贫寒的生活与过度的劳累都留下了痕迹,他的皮皱着,疙疙瘩瘩,在太阳下冒黑油;他瘦弱的身子,肋骨暴露着,如恐龙骨架。终于来到了老河湾,爷爷不放心,又拎起我的小腿,头朝下几晃,晃出了最后一碗水后才放我下来。
我们辛辛苦苦割的草都落入了水中,一团团像河马游走了。爷爷忙跳下水抢草,他已经非常疲惫,游几下不动了。我哭喊着去救爷爷,那被救的小狗也帮助我把他朝岸上拽,爷爷清醒了,一脸泥巴,慢慢向高处爬。
上了岸,我跌跌撞撞地去寻那窑红芋,只摸到烧黑的河泥。盛鱼的小坑也不见了,都已变成了河水的一部分。
爷爷不说话,坐在比平日宽了几倍的河的岸上,默默地叹息。我饿极了,加上害怕,失望,想哭。爷爷拍拍我,说:“要是水中漂一个金秤砣,咱都别动心,那是河神变的,他在试试咱可有贪心呢。人不能有贪心!”
草没有了,红芋没有了,鱼也没有了,是因为我们想得到大鱼,这是贪心吗?我想问,但怕爷爷伤心。
西天有云彩升起,光暗淡了。水流减速,水也渐渐清了,翻着白眼的鱼都清醒了过来。整个河湾腥腥的。我感到有些冷。爷爷的上衣也被水冲走了,他光着又黑又瘦的上身,细心地抱起一条小狗,把另一只大手放在我的小脸儿上说:“咱带小狗回家吧!”
我抱住另一只瑟瑟发抖的小狗,一老一少踏着夕阳朝村里走去。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