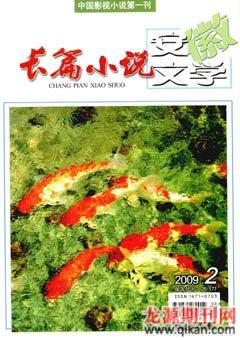老杜的精彩
张 晖
这段日子老杜老是快乐不起来,仿佛有件又沉又硬的东西横搁在心窝子里,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憋屈得发慌时,老杜宽自己的心,不就是厂里大礼堂油漆的事么?他都已经向老厂长和科长请示过好多次了,两位领导都说不急不急,领导都不急他还有什么好急的?他急又管什么用?拿钱不做事不是更好么?这样一想,老杜慌得透不过气的心里像钻进了一线清风,稍稍凉爽了一点儿。遗憾的是,这清风总在他心里待不了多久,往往是心气才稍顺畅一点点,那件沉闷的东西又飞快地挤了进来,一下子又把他心里堵了个严严实实,害得他情绪又低落起来。这两天,老杜思来想去,决定再正儿八经地跟领导汇报一次,要是再不动工,大礼堂的油漆就难保证质量,年底通不过总公司的验收怎么办?
一大早,匆匆忙忙扒了几口饭,老杜往办公室赶去。
科长一见他就笑嗬嗬的,满脸皱纹全都荡漾开来了,那样子活像办公室窗台上盛开的菊花。老杜正要张嘴说话,科长的香烟抢先塞过来了。科长知道老杜不抽烟,以前从不开烟给他,今天的破例让老杜始料不及,他赶忙住了嘴,慌乱地伸出双手。雪白的带黄色过滤嘴的香烟到手时,老杜很自然地看了看科长手中的烟盒,眼睛不由自主地鼓了鼓,平日连盒白沙都省不得抽的科长今天怎么抽起芙蓉王来了?接着,那个跟屁虫似的粘在科长屁股后的叫八毛的临时工,枯草般的长发像被大风吹乱的茅草屋顶,他咧开嘴,露出满口黄牙,一口一个杜师傅。老杜一见八毛就窝火,拍马屁的人就是想骑马,你舔科长的热屁眼还不是想捞厂里的油水?你一个外人怎么能打厂里的主意?你捞走一分职工就少一分——这想法在老杜脑子里迅速地打转。他赶忙装出没注意八毛的样子,将头转向另一边,同时把手中的烟架到耳后根。放稳了烟,老杜认真地看了科长一眼,又准备说话,科长手中的打火机突然啪地一声响了,老杜的眼睛自然地闪了一下。等他睁开眼时,科长已把火送到了他的鼻子下,他只得将烟从耳后摸出来,烟头对准火苗连吸两口,由于心里老想着油漆的事,老杜吸得过猛,结果呛得大咳起来。科长见老杜咳得流泪的狼狈相,笑得更厉害了。科长说,老杜我有事先走了。老杜赶忙吐出口里的烟对科长哎了一声,表示他有话要说,科长没待老杜开口就飞快地扬了扬手,老杜不明白科长的意思,愣了一下,科长在老杜发愣的一瞬间出了办公室,八毛也像得了特赦令一般,忙不迭地跟着科长出了门。老杜赶忙追出办公室,可是不见了科长和八毛的影子。
老杜很懊恼,他话还没说出口科长就走了。不知为何,老杜心里隐隐地不安起来,科长今天的笑好像不太自然,他出门前扬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阻止我说油漆的事?他的芙蓉王是不是八毛送的,八毛为什么要送这么好的烟给他……这些该不会与大礼堂的油漆有牵扯吧?想到这里,老杜脑顶嗡地响了一下,右手慌乱地摸了摸硬粗粗的短发,但他马上又往好的方面想,兴许科长扬手的意思是要我别说了,油漆的事他心里有数,兴许他今天的笑仅仅是心里高兴而已。再说,八毛是什么货色?一个只会扛二尺五(锄头)的外人,他几时摸过油漆刷?就算和科长好得合穿一条裤子厂里的油漆也轮不到他呀!
因为想得太用心,老杜直到额头被门碰痛了才发现已走到老厂长办公室门口。门关着,老杜连敲几下,又耳朵紧贴门听了几次,确信里面没人,只好失望地往回走。一想起老厂长,老杜又感觉自己刚才太多心了,他可以不信任科长与八毛,但他怎么能不相信老厂长呢?老厂长不光是他的老领导,还是他的知己与恩人呢!三十多年前,当他还是个小油漆学徒时,老厂长已是这个机械厂的人事主管了,见老杜能吃苦,老厂长就把他招进厂子。后来老厂长职务一路上升,对老杜的关照也越来越多,先把他送省城培训,后送他当兵,最后又把他要回厂子。老厂长信任他,凡是他做的油漆,从不说二话。这么多年的老交情,老厂长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砸他的饭碗?八毛在老厂长眼里算什么?老厂长几时正眼瞧过他?老厂长就是醉得糊里糊涂了,也不会把厂里的油漆给他做的。这样一想,老杜的心里安稳了。
老杜无聊地走出厂门,一抬头便看见了大礼堂,刚开朗一点的心不由又暗了下来。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自责得有几分心疼,仿佛自己多年前犯的错误到现在还没改正一样。他像看重宝贝儿子似的看重他的油漆质量,偏偏五年前老厂长要他赶完大礼堂的油漆迎接检查时,时间只有十来天了,他带着徒弟们没日没夜地赶,结果是事情做完了,油漆却刷得不光鲜,虽说老厂长从没说过什么,但老杜这些年一见大礼堂就心里不安,恨不得立马重刷一次,就像一个脓疱在他身上作痈多年,只有快速切掉才心里踏实一样。盼望已久的机会总算到了,今年厂子决定换掉大礼堂的油漆迎接总公司的检查,老杜一听这消息脑子就没法想别的事了,他早就买好了油漆砂布刷子,提前几个月对老厂长和科长说,大礼堂的油漆至少要一个半月,否则不能保证质量,让他犯迷糊的是,两位领导明明在他面前头点得如鸡啄米似的,现在离检查只差一个月了,他们怎么迟迟不让他动工呢?
下午,老杜又去找领导,他想好了,如果科长再不给答复,他就一定要老厂长的话。领导们也真是的,只需一句话就能搞定的事,他们却老是这样婆婆妈妈!
路过大礼堂时,老杜不由往里张望,望着望着便站住了,因为他听出里面有说话声。大礼堂的钥匙只有他和科长有,这点他很清楚,他估摸科长可能也在里面,心想正好趁此机会再催催他,于是转身往大礼堂走。
大礼堂里果然有人。老杜眼睛在房间里扫了个遍,没找到他要找的科长,却发现了八毛和几个陌生的民工。民工们手提油漆桶,正站着听八毛训话,平时缩头缩尾的八毛,此刻正双手插腰大着嗓门,样子威风得不得了。老杜惊讶地愣在门口,嘴张着,半天没法合拢。眼见民工们已提着桶走到窗口,又拿起蘸满油漆的刷子开始往窗台上抹,他才慢慢地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们……是谁让你们……老杜红着脸结结巴巴地问。
没人回答他。
这……是谁……谁让你们来做的?老杜只得重问一次。
一个民工看了他一眼,马上又掉头干自己的事去了。八毛明明听清了老杜的话,却装没听见转身折进了旁边的小房间里。
老杜脑海里迅速闪过上午的担心,接着又跳出一个十分肯定的推测,科长瞒着老厂长把大礼堂的油漆业务让给了八毛。一股滚烫如火的气体从胸腔里迅猛地上升,科长凭什么这样做?是八毛的技术比我好还是他在厂里的资历比我老?
老杜气咻咻地来到办公室。科长不在,老杜便用座机打通科长手机,刚说了句我是老杜,科长马上说他在外面,手机没电了,有事等他回来再说。
老杜火速去老厂长办公室,他揣摩,老厂长见了他这副气恼相一定会十分关心地问长问短的,令他意外的是,老厂长见了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时只平静地看了他一眼,然后静静地坐着等他开口。老杜气迷糊了的大脑陡地清醒了几分,老厂长是不是知道这回事了?未必是他同意了的?既然他同意了我说什么也没用了,我只是个做事的,事情要不要我做领导说了算。一时间,老杜痴着,眼睛看着老厂长,嘴皮子动了几下却不知说什么好。
老杜,你的油漆水平是一流的,这些年你为厂里做了很多有用的工作。见老杜迟迟开不了口,老厂长先说话了。
要在平日,老杜会为这句话浑身来劲,可是今天,这话却让他心里不安。老厂长说话时眼睛并没看他,而是望着窗外,这更让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果然,老厂长接下来说,你好好休息吧!
尽管先有预感,可这话从老厂长嘴里出来时,老杜还是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赶忙把刚才的话仔细回想了一遍,没错,老厂长确实是这么说的——可是,这是为什么啊?
这……您的意思是?老杜吞吞吐吐地问。
让八毛做吧!老厂长轻轻地说,眼睛仍看着窗外。
老杜两片薄薄的嘴唇痉挛般抖动着,脑袋左摇右晃却半天晃不出一个字,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老厂长转过身,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然后默默地走了。
老杜赌气在家,你们不要我做油漆,那我就只好休息了!他料定,不见他上班,科长很快会打他家电话。然而三天过去了,电话仿佛哑巴了似的一声也没响。老杜苦着脸在电话机旁边一个劲地转圈,两手在脑顶来来回回地摸。老伴见他愁得不成样子,就生气地说,不要你做你就休息呗,又没少你的工资奖金!老杜瓮声瓮气地说,我想不通啊,厂里这是搞什么名堂?撇下内行的正式工,偏偏用一窃不通的外行?明摆着脑瓜子进水的事,老厂长怎么就同意了呢?老伴也说弄不懂厂里的意思,她只是劝老杜,想不通就别想,这年头,厂里黑白不分的事情还少么?
老杜到底憋不住了,便往大礼堂去。
几个民工的油漆刷正在窗台上来来回回地抹,老杜悄悄凑过去一看,立即对着他们大叫起来,赶快停下来!
一个民工住了手,不解地看着他。
知道油漆要几道手续么?
民工茫然地摇头。
你们连这都搞不清还来做油漆?这样做出来的油漆捱不到三个月就会起壳!
火气灌满了全身,老杜猛地转身,反剪着双手下楼,他得去找科长或者老厂长说清楚,这些民工连油漆是什么都不懂,请他们做还不是浪费厂里的钱?厂里不要他做他没办法,但也不能这样花冤枉钱啊!这样一想,老杜心里“咝”地亮闪了一下,老厂长一定是不清楚八毛一伙是这样的货色,今天听我一说他准会暴跳如雷,训得八毛在科长尴尬的脸色下卷起家伙乖乖地走人,那样大礼堂的油漆自然归我了。
科长正好在办公室。老杜刚要张嘴,科长马上把手机放在右耳边喂喂地叫,那样子好像来了电话,老杜只好忍住火气等。老杜听见科长喂喂地叫了好几声,却听不见电话那边的回音,心想科长肯定在糊弄他,便急转身往厂长办公室去。
老厂长正戴着老花眼镜默默地看报纸,从他悠闲的神态看,他坐的时间蛮长了。老杜感到奇怪,平日忙得屁股没时间挨板凳的老厂长今天怎么这么清闲?
老厂长啊!不是我多事,八毛请来的这帮民工哪是在刷油漆……老杜一口气把民工不懂油漆的事全说了出来,而且越说越气急,说到厂里没钱进原材料而他们却糟蹋钱时,他心里很疼,右脚不由自主地往地上蹬了一下。他以为老厂长会瞪眼红脸大惊失色,当即决定和他一起往大礼堂去的,老厂长向来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没想到老厂长又是长长地叹息一声,然后漠然地看着窗外很远的地方。
老厂长啊,您是我多年的老领导,您说句实话,是不是我油漆做得不好?几天的怨气一下子涌上来,老杜的嗓音变了调,眼眶里迅速变得亮晶晶的。
厂里让你休息你就休息吧!老厂长尽力回避老杜的目光。
可是我……老杜的声音带着哭腔,他还有很多话要说,却全被老厂长油盐不进的语气和神态堵在喉咙口了。
老杜发誓再不去管大礼堂油漆的事。关我卵事!吃亏的是厂里又不是我!领导都不担心我还操什么闲心?可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没油漆做他的日子就不好打发,结果没几天他又不由自主地往大礼堂跑。一见到民工们别扭的运刷姿势他就气不打一处出,指指点点说这里底没打好,那里洞没补好。民工们起始对他有几分惧怕,后来却懒得理他了。民工越不理他,老杜就吵得越厉害。民工也来了火,反问道,你是厂长还是书记?我是——老杜顿时满脸难堪,没错,他只是厂里一个做工的,他连八毛这样的外人都争不赢,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划脚?
去大礼堂窝火,去办公室又不愿见科长和八毛,老杜只有在家里喝闷酒了。可是酒喝得越多他心里越郁闷,喝着喝着桌上的酒瓶碗筷被他一古脑扫下地,家里每天都响着碗筷落地的声音,地上这里一堆那里一汪满地都是酒和饭菜。老伴的忍耐到了极限,望着地上的碎片和酒菜哭了起来,你这死犟鬼!你跟谁怄气?东西是自家的啊!家中的酒杯碗筷快让他摔完时,老伴不得不对他严密监视了,只要他一端酒杯她就摆出救火的姿势。老杜不想和老伴闹别扭,于是成天躺在床上,任老伴怎么喊也不答理。老杜其实并没睡着,眼睛睁得很大,脑子从没离开过油漆和老厂长,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平日性子刚直的老厂长这次怎么变得软绵绵如糯米坨一般。
老伴受不了了,天天吵他,你再窝在家里,连我都会磨成神经病!气坏了身体谁来赔啊?这天,老伴的唠叨变成了大声的喝骂,说老家伙再不起床她就干脆回娘家去住。老杜不想接火,只得气冲冲地出了门。
老杜径直去了厂门口的饮食店,几个老同事正聚在一起闲聊。
什么国企改制?什么后勤服务社会化?不就是多花点钱请外边人来搞吗?
请外人搞当官的有外水,让职工搞他们就没油水捞!
胡包头承包厂里的木工才几年?他家的泥巴房都变楼房了!
你们看啰,用不了两年,八毛那两间东倒西歪的木房子也会变楼房!
……
晓得不?老厂长嫖娼时被八毛录了相,没办法了才把大礼堂的油漆给八毛做。刘木匠将嘴凑到老杜的耳边说。刘木匠早些年得过技能比武冠军,这两年因改制闲下来了,心里一直不畅快。
啊?!老杜的眼睛鼓得像铜锣,脸一时走了样。
不信你去看看大礼堂油漆帐罗!刘木匠睁大眼说,那神态好像是埋怨老杜死脑子不开窃。
尽管对刘木匠的话将信将疑,老杜还是偷偷地翻了大礼堂油漆的帐单。一看就愣住了,最多五万块的工程,还没完成一半就花了近二十万。如何得了如何得了!老杜猛地一跺脚,这样下去,不要两年厂子就会被他们玩垮!看样子刘木匠说的老厂长嫖娼的事不是谣言了!难怪老厂长这次与原来大不一样,原来是这点小把柄被八毛抓住了!咦!老厂长那老婆瘦得像根丝瓜筋,又四季吃药,老厂长去外面嫖两次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是他不该让八毛这样的家伙抓住把柄。一想起八毛那头乱糟糟的头发和满脸奸笑,老杜心里的恨又迅速地膨胀起来。这个可恨的八毛,用这样下流的手段害老厂长,还抢走我的饭碗,老子真想一刀宰了他!
考虑再三,老杜决定找老厂长好好说说,帮他想办法摆脱八毛的纠缠,只有八毛乖乖地从厂里滚蛋,老厂长才能硬起腰来,也只有老厂长硬起了腰,他才有希望继续做他的油漆。
老厂长啊!老杜边轻轻地说边关紧老厂长办公室的门,职工背后说你嫖……
老杜!老杜本想说职工说你嫖娼,但我根本不相信,可后面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老厂长就大喝一声。老杜被老厂长突如其来的大喝声吓懵了,睁大眼惊恐地看着老厂长。老厂长的脸板得像生铁,眼睛瞪得圆圆的,如凶神恶煞般。这是老厂长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冲老杜发火。老杜愣在房间里,身子筛糠般发抖,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脑袋又不停地晃来晃去,像得了偏头痛一般。
老杜拼命忍住快要溢出的眼泪往家走,直到被子从头到脚捂住身子才放开喉咙哭,沙哑的哭声随着他抖动的身子在房间里扩散开来,老厂长啊……这……这么多年……我……我哪一次不把你的话当……当圣旨……你好心当成驴肝肺……老杜哭累了,就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一张和善的脸出现在他面前,一双大手温柔地落在他肩上,好听的北方口音在他耳边响起,老杜,好好干——老厂长来看我了!老杜一喜,倏地睁开了眼——眼前没有老厂长,只有老伴。老伴眼圈红红的,正心疼地为他揩泪水,边揩边说,老头子,你死了爹娘都没这么伤心过哟!你真以为我是闲得发慌没事找事?拿钱不做事我巴不得咧!下次他就是向我叩头我也不理他了!老杜对着老伴吼了起来,好像老伴就是老厂长。老伴知道他在说气话,没回他。老杜吼了一通后也闭了嘴,眼睛呆呆地看着窗外,心想要是年底大礼堂的油漆验收不合格该多好!那时不怕他们不来找我呢!
总公司的验收班子去了大礼堂。老杜有意躲进旁边的小房间里,耳朵和眼睛却从门洞里搜索着领导们传出的信息。胡书记早就知道我是厂里的油漆大王,我的水平与这群王八崽子相比简直是一山两色,他肯定看得出来的!虽然胡书记不像老厂长,一见不如意就暴跳如雷,但他也会转弯抹角地把不满意说出来或者在脸上露出来。老杜弄得自己眼花耳鸣了,却没听见领导说过不满的话,也没从他们脸上看出任何不高兴的信息,心不由灰了下来。眼看着领导在老厂长和科长的陪同下离开了大礼堂,老杜只好安慰自己,兴许领导心里清白得很,只是碍于面子不好说而已。领导们走出大礼堂,老杜在不远处跟着,往年公司领导来厂里检查时,总是握住我的手,说我们的油漆专家辛苦了,说不定这次又有领导会提到我,他想,那样我立马走上去,握住领导的手,让他看出我心里不痛快。领导们一路上说说笑笑,谁也没有注意他,只有老厂长飞快地瞟了他一眼又赶紧把脸扭一边去了。老杜一直跟到厂门口也没听见他想听的声音。领导们上了车,往省城方向飞驰而去,老杜呆在冬风里失望地看着车屁股后扬起的灰尘,风很冷,吹得他瘦小的身子簌簌发抖。
科长和八毛往这边来了,老杜赶忙将脸转向另一边,假装没看见。紧接着二人的说话声传进他耳朵,想不到你们也能做出这水平!科长说。全靠您帮忙了!八毛受宠若惊地答。老杜立即听出他们在说大礼堂的油漆,一股凉飕飕的东西猛然直冲脑门,心窝里突然像被针扎了一般麻辣辣地疼,他感觉科长和八毛正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那眼光好像在说,你平时牛皮哄哄的!没有你厂里不是照样能做好油漆么?他身子颤了两下,心里无奈地长叹一声,八毛会拍马屁我不会,我的技术比他好领导又看不出,完了完了,厂里的油漆再也没我的份了!
从此,老杜像泄了气的皮球,成天耷拉着脸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地坐着发呆。闲下来的老同事们安慰他,当官的只晓得叫化子烤火胯里扒,老杜你看开一点,气坏了身子可没人赔。老杜感激地笑了笑,只是那笑在他脸上成了苦笑,一滴苦涩的泪在眼眶里露了一下又很快缩了回去。刘木匠这会儿把老杜看成了知音,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他说,要说油漆,莫说全厂恐怕全县也只有老杜。老杜紧绷的脸舒展了一点点。听说你80年代在人民大会堂做过油漆,还和中央领导合过影,90年代在厂里拿过技能比武冠军?有人问。老杜摸了摸满头麻色的短发,嗯了一声,那声音轻轻的细细的带着哭腔。
这样的安慰听多了,老杜心里舒坦一些了,他觉得光让人说说还不过瘾,于是把挂在客厅的两张相片取下来,放在口袋里,准备随时给人看。
听说你80年代在人民大会堂做过油漆,90年代在厂里拿过技能比武冠军?有人问闷闷不乐的老杜。
这有相片呢!老杜的声音颤颤的,好像被冤枉的小学生终于得到了老师的平反一般。
众人于是认真地打量着相片。
老杜,你就站在中央领导的旁边呢,好精彩!
老杜的脸涨红了,灰白的眼珠有了亮光。80年代在人民大会堂做油漆真过瘾,一点儿也马虎不得。他说。众人好奇地看着他,老杜的声音也越来越亮。正规的油漆要过五道关,老杜把右手举到齐脑顶的位置,把五字拖得长长的,首先用粗砂布把表面打平,再用油灰一个小洞一个小洞地补,补完后再刷三遍漆,刷一遍就让它干5到7天——哪儿像八毛手下这群王八崽子,只晓得往墙上乱糊!
众人于是大骂厂里风气不正,做事颠七倒八。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样的场景每天都有,老杜从中找到了快感,越说越起劲,一天不聊油漆他心里就像失去什么。可是听众们的兴趣却一点点地退去了。
80年代我就在人民大会堂做油漆,还和中央领导合影呢!老杜在人群中坐下来说。
有人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有人连眼皮也没往他身上抬,他们都知道老杜接着会说什么,他们对接下来的内容早没有新鲜感了。
这是我和中央领导的合影,这是厂里技能比武的相片,宣传科小马拍的。见众人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别的话题上,老杜只好提高嗓门说。
有人不得已接过他的相片,淡淡地瞟了一眼,很快又还给了他,更多的人装没听见。
老杜讨了没趣,只好顺着别人的话题说,但说着说着又回到了老话题上。
过去厂里凭本事吃饭,每年都办劳动竞赛,哪像现在,得势的尽是不做事的家伙!有人愤愤然。
是啊!90年代技能比武我连拿几次冠军呢——那时不管有文凭还是没文凭,能做事就行——老杜右手在空中划了一下,正准备描绘技能比武的壮观场面,不料旁边的人打断了他的话,接着原来的话题说下去。
那时厂子好兴旺,年货发得多,什么鱼啊肉啊羊肉啊样样有……
那是领导关心底下的人咧!咦!好的领导总是这样,80年代我在人民大会堂做油漆时,中央领导还和我们合影呢——老杜又扯到他的油漆上了。
众人谈兴骤然大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接着都把眼睛移向别处。他们对老杜这种见缝插针说油漆的做法很反感,只是碍于情面不便说出来,而老杜正说到兴头上,他觉得他的座位离人家太远,不靠近一些人家听不清楚,于是把右手伸进两腿间,将屁股下的椅子往前移一点儿。
和中央领导合影时,我正好站在他的旁边……老杜说着,又把椅子往前移一点儿。
这是我和中央领导的合影。老杜一手递相片,另一只手第三次拖椅子,他的鼻尖快挨到人家的脸了,他满口的大蒜味熏得周围人皱紧了眉头,他的口水飙到了对面那位的脸上。对方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动了一下,接下来毫不客气地起身就走,老杜举相片的手尴尬地停在空中。
老杜再也不找人闲聊了,他整天板着脸,反剪着双手在厂区乱转,长时间地看着他漆过的物件发呆。民工们不时从他身边经过,他长久地盯着他们手里的油漆桶,眼里露出悲哀的神色。老厂长偶尔出现在他视线里,他偷偷地看他一眼又赶快将目光移开。人们发现,他背驼了,头发几乎全白,脸上也不如原来灵光了,皮肤变得干燥多皱,眼角时时汪着两滴泪。
老厂长办退休了。离厂前,他特意找到老杜,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人家自己干了坏事还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总有一天公司会还我一个清白的。老厂长还意味深长地说,熊副厂长很能干呵,又有背景,让他去干吧!老杜昏花的眼睛骤然亮了一下,握着老厂长的手久久不放,沙哑着声音喊了一声老厂长,他感觉自己有很多话要对老厂长说,可是一股悲哀突然袭来,淹没了挂在嘴边的话,汪在眼角的两滴泪终于落了下来。
老厂长一走,老杜整天地将自己关在家里,连厂区也不去了,他总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痴痴地朝着某个方向却并没用心地看,老伴问他话他不理,老伴拖他下楼走走他不动脚。刘木匠和几个老同事一起来看他,他胡子拉碴,萎靡不振,看上去老了十岁。刘木匠拿出自备的好酒请他喝,他喝着喝着便大声哭了起来。
熊副厂长上任不到三年就因为经济问题被职工检举,检察院收审他那天,刘木匠嗵嗵地来找老杜报喜。这两个星期,他和几个老同事玩牌脱不了身,没来看老杜。连敲几下门,里面没反应。刘木匠赶忙问邻居,邻居说老杜的老伴一个星期前回去伺候老娘去了,但老杜没和老伴一起去,他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刘木匠把这话对老同事们说了,老同事们便分头去找他,大礼堂、老杜做过油漆的地方,连路边的水沟也找遍了,都没有老杜,他们只得报了保卫科。保卫科先打开老杜的家门,每个房间都仔细地找,床底下,衣柜里,能藏住老杜的地方都找了,没有老杜。保卫科赶紧分成两组寻找,一组去老杜曾经刷过油漆的地方,一组去少有人光临的锅炉房、水泵房、仓库,找了一天,两组人员都失望而归。
保卫科长正要派人去老杜的岳父家,只见一个油漆工脸色惨白跌跌撞撞地往他办公室来了。科长再三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惊魂未定的油漆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老杜……死……死了!一群人立马跟着民工往刚建成的新车间跑。这车间一个月前竣工,机器设备还没来得及安装,建筑队撤走后没人来过。大家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三楼,眼前的情景把所有人都吓懵了——老杜面贴着墙,两脚趴开,两手撑开粘在墙上,整个身体成了个“大”字。他穿着工作服,全身上下沾满了红的绿的油漆,粘在墙上的两手,紧紧抓着两把油漆刷。墙上的油漆已刷到一半。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力才把他从墙上掰下来,他的眼睛睁得老大,嘴紧紧抿着,脸上的肌肉往上拉紧,完全是用力刷油漆时的姿势。人们用力地掰他的手,想帮他把油漆刷取出来,然而,刷子和手指粘得太紧,任凭他们怎么用劲也无法把它们分开。一个老同事猛地一拍脑袋说,上次在老杜家喝酒,老杜说只要厂里把新车间的油漆给他做,他不要厂里一分钱。嘿!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没想他居然当真了!刘木匠也说,老杜得了技能比武冠军照相时,摆出的正是这个姿势。
作者简介张晖,女,七十年代生于湖南桃江,199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年进入毛泽东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习。其小说作品先后在《芙蓉》、《安徽文学》、《广州文艺》等刊物发表,现供职于湖南某上市公司。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