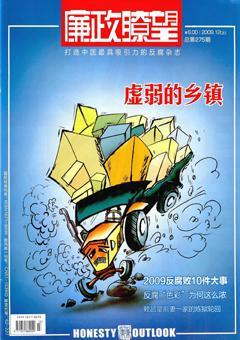从敌对迈向合作的中美60年
李因才
11月15日至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在北京举行会谈,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中美在许多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富有成果。媒体评论认为,两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合作时代。回顾近期温家宝总理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首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举行,以及中美两国在经济、能源、环境、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都体现了两国的共同利益。然而翻开历史,中美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有诸多的曲折坎坷。
危险的敌对
国民党残军退守台湾后,杜鲁门政府在酝酿“台湾地位未定”计划的同时,开始考虑抛弃国民党政权的可能性。1950年1月,杜鲁门明确表态:“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政中的途径”。
不过,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杜鲁门政府很快改变了几个月前还在申明的“不介入”台海的立场。
当然,立场转变的根本动力还是源于华盛顿对国际形势新的判断,尤其是在基于意识形态分歧而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现实后,较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被盲目的意识形态冲突的考虑所取代。杜鲁门政府把阻止中国统一的台湾看作是全面遏制共产主义、支持“民主政权”之努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扶植台湾国民党势力将给美国提供在亚洲的一个战略据点和势力范围,这正是美国国内部分强烈敌视社会主义中国,包括军方人士所乐意见到的。6月27日,杜鲁门作出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决定,阻止中国统一台湾。
美国对中国统一台湾的干预及朝鲜战争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促使中国最终参战,这场战争使两国的相互敌对迅速激化。美国也由此认识到中国的能力,将其存在及意识形态的扩散视为美国在亚洲谋求霸权的最大威胁。与此同时,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的左倾化思潮逐步蔓延到对外政策领域。尤其在经过两次台海危机后,中国对美愈加不满,舆论宣传上也更具火药味。而苏联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对美谋求缓和。中国则谴责苏联对美帝缓和是修正主义行为,是懦弱顺从的表现。这样,在美国民众看来,中国的威胁甚至一度超过苏联。
值得提及的是,这期间中美之间的唯一交流渠道是通过先设在日内瓦、后移往华沙的大使级会谈,但双方在会谈中只是各自表述自己的立场,形同“聋子的对话”。在这种状况下,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中美双方寻求和解,中间虽历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届政府,但在对华遏制的政策上一直变化不大。
曲折的建交
60年代末,中国面对严峻的安全问题,内部受到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削弱,外部受到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的威胁。而美国则深陷越南战争,并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一种劣势地位。美国急需寻求一种力量来平衡苏联,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声望、核大国的身份无疑是其最佳选择。与此同时,相对于尼克松总统在越南的战争降级,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次年在珍宝岛的屠杀及此后在中苏边境线的兵力集结,表明这时中国更大、更为急切的威胁来自北部。这样,对苏联是最大的战略威胁的共同认知,为中美两国走出敌对、互相接近提供了利益切合点。
在和解过程中,中美一开始通过设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及“巴黎秘密渠道”等方式互相传递信息。台湾问题是双方接触谈判的公开理由,尽管隐含的是来自战略方面的迫切压力,这种压力使中美双方都能暂时搁置在台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而优先改善关系。1971年基辛格在秘密访华期间澄清的美方立场是,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驻台美军将逐步撤离,但美国不会离弃蒋政权。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定于6月中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里的中方立场,决定在要求美方从台湾撤军的同时,不再坚持将美国同台湾断交作为两国开展交往的先决条件,并初步提出在中美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想。双方的立场渐渐趋近,在尼克松访华时,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1972年2月共同发表了联合宣言,中美和解的门打开了。
由于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美国的顽固立场,美中关系在1972年取得初步突破后,逐渐停顿下来,在福特政府时期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直到卡特上台后,在同样信奉权力政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帮助下,才“下了决心”。卡特政府决定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同时指示在北京谈判的伍德科克提出美方的“三点要求”,内容是允许华盛顿在正常化时刻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单方面声明,美国将在非官方基础上保留与台湾的全部经济文化关系,并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华盛顿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成为此后美国历届政府一再强调的重要原则,而在美军全部撤离后,对台军售重新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不过,整个冷战后期,着眼于共同的“敌对”目标,双方关系一直比较稳固。在里根政府第一任内,尽管两国因台湾问题不时出现争吵,但华府还是将中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政策分析人士甚至在探讨中美是否应该建立一种“盟友”关系。
两种思维间摇摆
冷战的结束,使中美关系受到巨大冲击。一方面,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消失,“为阻止苏联在亚洲和其它地区扩张而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先由于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改变对外政策而遭到破坏,后来又由于东欧共产主义的垮台及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而被彻底摧毁”。另一方面,华盛顿对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忧心忡忡。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对“红色威胁”的恐惧形成对照,美国开始扩散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对华政策再次像50年代那样,成为美国国内激烈辩论的焦点问题,民主、共和两党在七、八十年代培养的对华一致的态度也在后冷战时代慢慢消失。“美国尚不能确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未来要对付的‘战略对手”,因此,美国在“接触”与“遏制”两条路线间徘徊往复,犹豫不决。
这种摇摆不定在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及小布什政府时期均有体现,而小布什在上台之初及至“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对华政策的巨大变化,更将这种心理以夸张的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
合作谋取共赢
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在这篇题为《中国何去何从:从成员到责任》的专题演讲中,佐利克强调了“接触”的必要。他认为,寻求与中国的广泛合作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也正是在这篇演讲中,他明确指出:美国的未来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而是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以共同维护和加强现存的国际体系。
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佐利克的演讲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布什政府乃至华盛顿精英人士对华思维的重要转向,也就是更加务实、平和地看待中国崛起。这显示出,一方面,中美关系目前还很难摆脱国内政治困扰;另一方面,随着两国各渠道联系的日益密切,特别是双边对话的有效开展,美国国内冷战初期对华那种“沸腾的焦虑情绪”也在逐渐趋于平息。当然,对华思维的转向也和中国内外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中美两国都在相互建构一种更加务实、理性的合作理念。
如今,中美站在一个新时代的端口。30多年前,双边关系改善的动力主要源自两国对各自安全的关切。今天,安全问题在两国议事日程当中的重要性大为降低,两国考虑越来越多的是双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及全球和区域问题,两国合作的全球意义越来越彰显。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的“G2”概念尽管夸大了中国的实力与地位,但它也反映出了两国利益交合的复杂和全面合作的必要。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解决气候变化,无论是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还是敦促朝鲜最终弃核,在国际体系面临转型的混乱时期,全球诸多事务的治理越来越难以缺少中美之间的共同声音和身影。要做到两国的有效合作,一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国际化,另一方面,华府内部也需要更深入的思维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