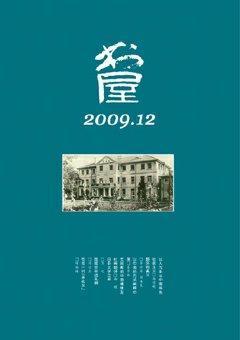日本文学之美
万 之
瑞典学院给两位日本作家颁发过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给川端康成,1994年给大江健三郎。这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风格和美学理想显然不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文化风景,看到日本文学的发展线索,也能体会到瑞典学院在前后两次评选时的不同取向。前一次颁奖,要在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冷战背景之下考察,也要在东西方文化对立的背景下体会。川端康成让瑞典学院院士感动,是因为他唱出了一个没落状态的东方文明的哀怨挽歌,是他具有地道的“日本性”,是异国情调。对于西方人,他扮演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他者,所以瑞典学院和他的关系如异性之恋;而后一次颁奖,是在冷战平息而世界迅速进入全球化的背景下,虽有不同文明的冲突加剧,但传统和现代文明也在交融汇合之中。大江健三郎让瑞典学院心仪,是因为他为传统文明融入新的现代文明开辟了一条道路,他成为一个西方人可以认同的新人,所以瑞典学院和他的关系有点像同性相怜。
川端康成获奖的年代,是所谓“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民族解放是第三世界的潮流,“反帝”、“反殖”是时髦口号,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风起云涌,在欧洲也产生巨大影响。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暴露的种种弊端不满,而以为东方的文明或可带来新的希望。瑞典学院当时有位院士马丁松,也是一位知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他就对中国的道家文化情有独钟,马丁松本人在1974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岁月流转,二十多年后,大江健三郎的获奖,和他之前墨西哥诗人帕斯、南非女作家戈蒂默尔、加勒比诗人瓦尔科特、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获奖一样,则可说明瑞典学院在东西方文化冲突问题上新的态度、新的立场和评价标准:作家既不应该屈从“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霸权”或“白人文化优势”,也要超越保守狭隘的民族主义,防止极端的种族情绪和原教旨主义,不利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名义来排斥本来可以超越东西方文化冲突思维模式的人文价值。
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国际主义
如果说在川端康成的时代,瑞典学院还鼓励立足本土的“民族主义”文学,需要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的“精华”,那么到了大江健三郎的时代,他们会强调,作家既立足于本国文学而又不囿于本国文学的局限:作家不能仅仅以本国文化传统来自我定位,而是应该以本国文化传统在当今世界国际化文化环境中的位置来定位,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民族国际主义”的立场。大江健三郎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际主义”的作家,所以瑞典学院给他颁奖,也是抛给一个“民族国际主义”作家的花环。
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瑞典学院给这两位作家的颁奖词,前者突出了“日本的”,而后者则突出了“人类的”。瑞典学院给川端康成颁奖的新闻公报虽然提到他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是更称赞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瑞典学院给大江健三郎颁奖的新闻公报则称赞他一方面是为日本读者写作,另一方面打动日本之外的读者的心,因为他的作品“用诗意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其中生活和神话浓缩成为当代人类境遇的一幅令人难堪的图画”。这里说的“当代人类”当然不仅仅指日本人民,而是地球上的人类。
“民族国际主义”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荒唐,好像是把两个截然相对的概念硬凑在一起,民族主义者不一定是国际主义者。但是,我也无法想出一个更合适的词来描述一个作家在全球化的文化互动环境中面对本国文化时的力求两全的立场和心态。其实,这个词也并非我的新创,而是借用执教于东京索菲亚大学的希腊籍哲学教授亚松·洛索斯的说法,他认为大江健三郎是一个“深刻的日本国际主义者”。这里,“日本”不仅仅是表示作家的身份国籍,而是他的立场。洛索斯说,在日本这样一个民族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大江健三郎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反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最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作家,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态度,他又比所有日本人都更日本,更具有民族性。
在这方面,大江健三郎本人的思想表述、文学方面的实践和理论都可以成为一种佐证。他本人非常强调他是日本作家,是为日本读者写作,他的作品总是描写当代日本人和他们的生活,而且主题都是针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重大社会问题。日本文学界,还有他的译者,都认为他的文学语言丰富了当代日语,其特色难以用其他语言转述,非常难翻译。同时,他强调在国际化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日本人面对的问题和生存困境,也往往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和生存困境,所以,描写日本人的日本文学,也自然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介绍日本当代文学的时候,提到一个比较著名的日本当代作家安部公房,称赞他以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心态来展现日本人的现代生活,使得作品更具全人类都能接受的普世性意义。我想,这些话也适用于大江健三郎本人。欧盟曾经在1989年授予大江健三郎“犹罗帕利文学奖”,表彰他创造的文体既能够表现作为日本人的个人体验,又与人类普遍性经验相结合,对欧洲文学给予了相当的影响。
把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做一个比较,对于日本文学从典型的唯日本之美的“民族主义”到后来这种“民族国际主义”的发展特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川端康成一九六八年到斯德哥尔摩来领奖的时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是用日语,演说时身穿典型的日本和服,题目是《日本、美和我本身》,就是说民族国家、艺术之美和作家三者之间构成一种自在的共存互属关系。只要表现为日本的独特的,就是美的,当时的瑞典学院院士们着迷的正是这种西方人不熟悉的异国情调。他的作品后来在中国还颇为流行,比如《雪国》和《伊豆的歌女》等等都有中文翻译,我想读过这些作品的读者大都能感觉到这种典型的日本特色。这和我们阅读中国的《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一样,这些作品自成一体,我们可以感觉到作品的强烈的民族性,能看到作家不可置疑的民族身份。
日本当时还有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正是川端康成的挚友。三岛由纪夫1970年剖腹自杀之时,很多日本作家闻讯赶去,而他只允许川端康成一人进入听他的临终遗言。前赴后继,川端康成本人也于1972年自杀而死。他们都是想竭力维持日本文化古典之美的唯美主义作家,而哀叹日本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堕落,我们从川端康成的文学奖演讲词《日本、美和我本身》去理解,也可以说“日本之美”之消亡就是“我”之死日,所以他们也是殉美而死。三岛由纪夫据说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来在西方还很走红,也应该算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瑞典上演过他的剧作《萨德侯爵夫人》,题材居然是取自法国那位以残暴折磨异性出名的萨德侯爵的家庭故事,性虐待的外文因此就叫做“萨德主义”。此剧由瑞典著名导演伯格曼执导,还应邀到台北演出,我还应命把演出本翻译成了中文,以便演出时同声传译。虽然三岛由纪夫写了西方文学题材,但是他还是只注意展现自己的日本式的独特心理视角,他和世界文学其实缺少真正的交流。
大江健三郎显然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有了不同的立场。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英文演讲的,身穿西服,题目则是模仿改换川端康成的题目,只改了一个词,成为《日本、模棱两可和我本身》,“美”在这里换成了“模棱两可”,也是模糊不清具有双重性质的意思,表示当代日本文化已经有了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两极对立,也是日本在世界文化格局内的一种尴尬处境。就是说,由于新的世界格局,维持川端康成推崇的单极的日本古典美已经不再可能。如果日本作家继续像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那样过于钟情日本的古典美,缺乏和世界文学其他民族文化其他艺术之美的对话交流,抗拒外来文化影响,不顺应时代潮流,顽固把守传统阵地,确实也只有死路一条。
大江健三郎在演讲词中指出,日本的现代化已经有了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日本人已经处在“模棱两可”的两极分化之间,连他本人身上都不可避免带上了这种分化的烙印。一极是现代化、西方化的日本,经济上已经归属于西方强国集团,脱离了所谓第三世界,而另一极依然还是属于东方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二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工业和科技产品带动了文化产品的出口销售,商品文化也被打上所谓“日本”标记,而这种“日本” 的文化其实已经是“模棱两可”的东西。他在演讲词中说:“我所谓的日本的‘模棱两可是贯穿了整个现代时期的慢性疾病。日本的经济繁荣也没有能摆脱这种疾病,而伴随着的是在世界经济结构的光照下出现的各种潜在危险。”
提到潜在危险,不可能不提到日本的战争罪恶。日本进入工业化比较早,而经济上的发达加上狭隘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扩张反而把日本推上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深渊,这使得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不得不深刻地反省。大江健三郎不仅是这代知识分子中的文学代表人物,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有激进左翼色彩的政治人物。除了小说,他还发表了很多政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总是态度非常鲜明。例如他反对日本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反对核武器,甚至对于整个制度也提出质疑。在文化上,他也反对国粹主义,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西方文化,反对文化封闭。他认为犯有战争罪恶的日本只有寻求和世界文化的交流,接受普世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开阔视野,才能被世界原谅和接受。
所以,著名文化批评家弗·詹姆逊曾经这样评价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最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从来不认同官方的和传统的形象。他和日本其他作家都不一样,最无日本传统的陈腐的民族主义气息,在某种意义上,他既是日本的同时也是最美国化的小说家,是开放外向的,是不受拘束的。”詹姆逊这种说法,也是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大江健三郎的“民族国际主义”色彩。
截然不同的文化资源
川端康成钟情于日本古典文学的优美,钟情于东方的神秘主义。他在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中大量引用了日本的古典诗歌,解释东方艺术的“山水”之意。他没有谈到一位西方作家,而是介绍日本禅宗诗僧希玄道元、明惠上人、西行、良宽等的诗歌,芥川龙之介和太宰治的小说,《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枕草子》等的古典传统,也介绍东方绘画、书法、花道、茶道。他特别强调东方之美才可以把他自己和西方文化区别开来,例如把自己的禅宗式空灵和西方的虚无主义区别开来。在演讲的最后一段,他说道:“这里,我们有东方的空灵、东方的虚无。我自己的作品多被论者说成是空灵的作品,但是不可以和西方的虚无主义混为一谈。其精神基础是相当不同的。”
与川端康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中,坦白承认自己受到西方文化资源的影响。他首先提到自己的文学道路追随爱尔兰诗人叶芝,他的小说《燃烧的绿树》书名就是来自叶芝诗歌的意象。他也引用英国诗人布洛克或奥登的诗歌,提到小时候就着迷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或者瑞典女作家拉戈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样的儿童故事,还引述英国小说家奥维尔,介绍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对自己的影响,如此等等,公开坦诚展现自己和西方文学的深厚渊源,显示了西方文学方面的丰富知识。
川端康成出身世家,大学时代主修国文,而大江健三郎大学本科时主修了四年法语和法国文学,也是在拉伯雷、巴尔扎克、雨果等法国作家的影响下开始写作,他对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有特殊的兴趣,他的毕业论文就是论述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初期作品如《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等也都表现出存在主义的色彩。这种学历和创作经历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如出一辙,倒是让人觉得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否法国文化最适合帮助东方培养诺贝尔文学奖水准的作家?
东西方文化虽然有很多区别,但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却能够把“民族的”和“国际的”这样的两极对立重新连接在一起,消弭其中的所谓“模棱两可”,而造就一个“民族国际主义”的伟大作家。
大江健三郎在演讲词中说,日本作家要寻求理想的新的文化身份,恢复日本人的尊严和体面,应该接受的就是人文主义。而这种人文主义,更明确地说就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他把自己在人文主义方面接受的熏陶,都归功于自己大学时代的恩师、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教授,他赞扬渡边一夫即使在日本处于对外战争的爱国狂热年代,却仍独立特行地梦想着要将西欧人文主义溶入到日本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而这是不同于川端康成的“美”的另一种观念。也可以说,大江健三郎本人也坚持着这样的梦想,并一步步在文学创作中努力把这种梦想转为可以让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体验到的形象世界。
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渡边一夫向日本读者介绍的欧洲人文主义,特别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伯雷、伊拉斯姆斯等等,都是“有生命活力的整体性的欧洲文化精华”,也正是米兰·昆德拉所定义的“小说精神”。这是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强调宽容的重要性,能看到人类的自身弱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应该反对人类互相残杀的任何战争,正如他引用的丹麦哲学家尼洛普的名言“那些不反对战争的人,就是战争的帮凶”。
理解大江健三郎的这种人文主义资源,就能理解他的大小著作中为什么总是充溢着人性、人道的气息。例如以作者自己的爱子、先天性头盖骨缺损和脑组织外溢的大江光为核心人物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虽然是描写个人独特的痛苦经历,也因为充满父子之情,其对于死亡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却能激荡世界众多读者的同情感,深得瑞典学院院士们的赞赏。
通过阅读渡边一夫翻译的法国作家拉伯雷的经典作品,大江健三郎也建立起了自己创作小说的独特形象系统,这是我们理解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的另一条重要线索。读过拉伯雷文学作品《巨人传》的读者,都能够体会到作品的奇异风格,完全不同于后来的巴尔扎克式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不同于雨果式浪漫主义文学,大江健三郎引用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说法,就是“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者文化的形象系统”。拉伯雷小说中的“德廉美修道院”,也是一个理想世界,可以算是大江健三郎后来在小说中描写的现代乌托邦的影子,而他对于民间神话传说的挖掘,也得益于拉伯雷《巨人传》的启发,这就是瑞典学院颁奖词中“生活和神话融合”的注脚。
当然,大江健三郎并非简单地模仿复制西方文化,因为这仅仅是创作方法的资源之一,而他自己建立的形象系统,还是要移植到亚洲的环境中。他说,这个亚洲当然不是如今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崛起的亚洲,还是过去的、贫瘠的、乡村而自然的亚洲,因此他提到自己和韩国作家金芝河、中国作家郑义和莫言分享同样的感觉。在他看来,文学的世界性就是要建立在这种具体形象的分享之中。 这样的形象系统使得他这样一个本来出生在世界文化边缘的国家的最边缘地区的人,能够获得普遍的承认。
无论川端康成还是大江健三郎,他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当然也都是他们个人的文学天赋,不光是他们的机遇和时代潮流。川端康成是公认的日本战后文学的领军人物。瑞典学院称赞他的作品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二是架设了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对于大江健三郎,著名的美国作家亨利·米勒曾这样高度评价:“大江虽然是地道的日本作家,但是通过对于人物的希望和困惑的描写与控制,我以为他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水准。”连政治上和大江健三郎截然对立的三岛由纪夫当年也不得不承认,“大江健三郎把战后的日本文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以大江健三郎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