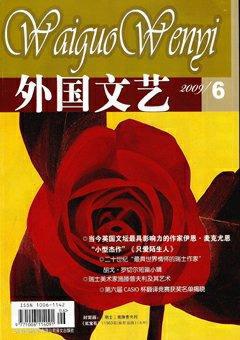爱尔兰悲歌
贺晚青 译
那个周末,在卡莱尔郡1,诺埃尔是一群音乐人中唯一没有喝酒的,于是他便成了随驾司机。他们也正需要一名司机。在他们看来,镇上充斥着奔放的学生和急待观赏到一切的游客们,要想找个酒吧简直是不可能的。有那么两三个晚上,他们想到乡村酒馆去,那里人不多,或是比较安宁的私宅也好。诺埃尔会吹锡哨2,这方面他很有天赋,但其中更多的是技法的糅合;此种乐器更适于伴奏,而不宜独自演奏。然而他的嗓音就不同了,虽然不及他母亲音质上的力度和个性,但是的确很特别。他的母亲是音乐界耳熟能详的人物,得名于七十年代早期灌制的一张唱片。但诺埃尔的特点是,他能够在一个八音度的调子里游刃有余,并自由掌控音高,以应和其他人的声音。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声音,他都可以与之完美呼应。他总是自嘲地说,自己不具备真正的歌喉,有的只是懂得倾听的耳朵。朋友们也都一致认为他的听力是无可挑剔的。
到了周日晚上,小镇开始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他的朋友乔治说,大部分去镇上酒吧的,都是属于那种把酒洒在你的爱尔兰风笛上还要幸灾乐祸一番的人。甚至在一些比较有名的乡村酒馆,也同样挤满了前来寻求安抚的外来客们。有消息称,当天下午,米利士的凯乌蒂酒馆举行了爱尔兰传统音乐会3 。所以到了晚上,他就要负责去那里带回他的两个朋友,把他们带到恩尼斯4另一端的一处私宅里,利用那儿的片刻静谧来演奏。
诺埃尔一进入酒馆,就在靠窗的墙壁凹陷处瞅见了他的两个朋友,一个正在弹奏簧风琴,另一个则在拉着小提琴。两人都朝他挤眉弄眼,示意已经知道他来了。他们正被人群簇拥着,旁边还有两个小提琴手和一个吹长笛的年轻女子。前面的桌子上,酒瓶堆得到处都是,瓶里都或多或少盛着一些酒。
诺埃尔朝后站了站,环顾了四周,然后便去吧台要了一杯苏打水和酸橙汁;音乐使得酒馆的气氛愈加活跃起来,即使是那些毫无音乐细胞的人来到这里,也会产生一种新奇的满足和自在感。
在吧台处等候时,诺埃尔发现自己另外的一个朋友也在那儿等,于是向他点了点头,样子看起来很从容。接着,他告诉这位朋友,他们不久就要整装待发了。他的朋友听说后也愿意和他们一起去。
诺埃尔又说道,“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我们所去的地方。”
他盘算着,当他们可以衣着体面地离开之时(这大概要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他将开车载着他们穿过乡下的田野,如同经历一次虎口脱险。
正要准备喝时,他的朋友歪斜着身子朝他走来,手里握着一品脱淡味啤酒。
“我看见你在喝柠檬汁,”他略带挖苦地笑道,“要不要再来一杯啊?”
“这是苏打水和酸橙汁,”诺埃尔说。“你喝不下的。”
“我已经没法弹奏了,”他朋友说道。“酒喝得太多了。等缓过来一阵,我们就出发吧。另外那个地方酒够喝吗?”
“问我的话你算是问错了,”诺埃尔说,他朋友估计喝了一整个下午。
“我们可以在路上喝,”他朋友说道。
“只要你们这些家伙准备好了,我就可以开车上路啦,”诺埃尔说着,一边冲演奏音乐的地方点了点头。
他朋友皱着眉头,又呷了一口啤酒。随后,他扬起头,试图在人群中找寻出诺埃尔的脸庞。寻觅了半天,他才看见。环顾了一下四周后,朋友凑到诺埃尔近旁,以便不被他人听见。
“还好你今天喝的是苏打水。我想你知道吧,你母亲也在这。”
“喝苏打水就行了,”诺埃尔微笑着说道。“我今晚也不想喝啤酒了。”
这时,他朋友转过身去,音乐将他吸引住了。
诺埃尔独自站在吧台旁,他算出自己今年二十八岁,这意味着已经有十九年没见到过他母亲了。他甚至不知道她也在爱尔兰。他仔细观察了四周,觉得自己应该不会认出她来。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父母离异多年,但没人能够体会这其中的辛酸苦楚,也没人能够想象那份沉寂,多年来长久萦绕的沉寂。
前不久,诺埃尔从父亲口中得知,在早些年间,母亲曾经给自己写过信,但是都被他的父亲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听说了这件事后,他和父亲说的是,他宁愿父亲当年抛弃的是自己,而不是他的母亲。事后诺埃尔懊悔不已。自那以后,他和父亲之间就再没说过一句话。随着音乐奏起,渐入高潮,诺埃尔在聆听之余,也下定决心:一等自己回到都柏林,就去看望父亲。
不知不觉间,他杯中的饮料已经喝完;再回到吧台时,发现那儿正忙得不亦乐乎。他试图同酒吧老板约翰?凯乌蒂或者他儿子小约翰搭讪,以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无所事事,这当口还可以思忖一番如何做是好。他清楚自己现在是不能离开酒吧,开车一走了之的,他的朋友们还要搭他的车呢。而且眼下,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独处。他知道还要继续呆在这儿,但是必须要退到后台区的阴暗处,这样才可能避免见到她。他想,自己每年夏天都来这,差不多有十个年头了,酒吧里认识自己的人应该还是不少的。他希望那些人都没有看到他,或者说,即便他们看到了,也没有机会去告诉他母亲,说她的儿子就在人群当中,在这个离家二百英里的地方;他碰巧也来到了这家酒吧。
这么些年,他都是通过收音机听到她的歌喉,里面总是播着她老专辑里几首不变的歌,现在则是通过唱片机来听。其中的两首爱尔兰歌曲,节奏舒缓,令人难以忘怀。她的声音如同天籁,婉转动听,充满了自信和感召力。对于她的相貌,他是凭专辑封面照片获知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来自记忆。此外还有十年前《星期日报》5在伦敦对她进行过的一次采访。诺埃尔亲眼目睹了他父亲把整个版面烧毁的情景,但后来他又悄悄给自己买了一份报纸回来,剪下其中的采访内容,连同旁边印着的大幅照片。当时给他震惊最大的一条消息是:他那在戈尔威郡的外祖母还活着。他后来获悉,母亲和另一个男的私奔到英国以后,父亲就断绝了和外祖母的往来。在那次采访中,他母亲透露,她自己经常回爱尔兰的戈尔威郡看望母亲和几位姨妈。所有的这些歌曲创作都是从她们那里学来的。她并未提及自己还有一个儿子。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经常研究那幅照片。他发现,照片上自己的母亲笑容可掬,面对照相机时神态自如,眼中流露出耀眼的光芒,一如她五光十色的生活。
十七八岁的时候,还在踏入歌坛之初,他的音质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许多专辑在录制时,都会请他来和音及衬托主唱。他的名字也和其他音乐人的印在了一起。看着唱片的封面,他常常会产生一种自己就是母亲的错觉,还猜测着她会不会买这些唱片,想象着她无意中瞥到背面印着的工作室成员的名字时,突然发现了他的名字,然后停上一两秒,去回忆他的年纪,设想关于他的一切。
他又买了一杯苏打水和酸橙汁。从吧台转身时,他面向人群,努力思索着自己站在哪比较好。猛然间,他看到了自己的母亲,而她也正凝视着自己。在昏暗的灯影下,她看起来比《星期日报》上刊登的那张照片的模样还要年轻些。他知道她现在五十出头,但是由于长刘海和赭色头发的缘故,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个十岁到十五岁左右。他仔细而又平静地研究了一番她的眼神——没有微笑,也没有任何表示相认的暗许成分。她的目光包容了一切,也对一切充满了新奇。
他抿了一口杯中的饮料,朝门口瞥了一眼,看到外面渐渐昏黑的夏日天色;回眸时,他发现她仍在注视着自己。她和一群男人在一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穿着上判断,应该是当地居民,但其中至少有两个人不是,很有可能是英国人,他想。接着,又来了一位年龄稍长的女士,看不出是来自哪里的,坐在了他们中间。
当他再次转过头回到吧台时,音乐嘎然而止。他于是回望过去,看朋友们是否在收拾乐器准备离开了,但是却见他们正对着自己,仿佛在等待什么似的。他惊奇地发现,酒吧的老板娘斯塔蒂亚?凯乌蒂也来了。她曾经跟客人宣布,她在晚上六点后就不会出现在吧台。这已经成为她的一条雷打不动的准则。她笑脸迎人,但是诺埃尔并不肯定她知道自己的名字。他认为,对她来言,自己不过是众多男孩中的一个,每年夏天都从都柏林来到这儿,而且不止一次。但是你可别看走眼了,她的眼力非同一般,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她示意他往旁边挪一下,这样她就可以看清楚在座的客人们。就在他这么做时,她唤了一声对面坐着的他的母亲,以引起她的注意。
“艾琳!艾琳!”她喊道。
“我在这儿,斯塔蒂亚,”他母亲应道。她口音中夹杂着一丝英伦腔。
“我们都准备好了,艾琳,” 斯塔蒂亚说。“要不要现在开始?待会就人山人海了。”
他的母亲埋下头去,再次抬起来时,表情显得几分凝重。她摇了摇头,面目很严肃,仿佛在告诉斯塔蒂亚?凯乌蒂,她觉得自己上不了,即便她为此准备过。约翰?凯乌蒂和小约翰此时已经停止了供酒。酒吧里所有的男人都看着诺埃尔的母亲。她突然羞赧一笑,朝后拢了拢头发,又把头低下去了。
“现在请各位安静!” 约翰?凯乌蒂大声宣布道。
随着音度的升高,她的嗓音仿佛无迹可寻,就连低音部分也被她演绎得惟妙惟肖,感觉比唱片里的声音更加浑厚有力。诺埃尔想,来这里的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这首歌另外还有一两个较为一般的版本,也许其中还会有一部分人听过他母亲的那个版本。然而现在的这种唱法更为狂野,它加入了所有的花音、装饰音,还不断地峰回路转,变换着各种曲风。唱到第二节时,她抬起头,睁开了双眼,向斯塔蒂亚投去微笑,后者双手交叉着站在吧台后面。
诺埃尔认为她起音还不够开阔,八九段唱下来,她肯定要借用假声什么的,或者不得不降音。然而,随着演唱的继续,他发现自己其实错了。她在唱到高音区的拖音时,对气流的呼入掌控得很是到位,这点实在令人叹服,但是,也由于她语言方面的熟练程度,演唱效果与唱片上的相比还是有所差异的;这是她的母语没错,也是他的母语,可是她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她还是沿袭过去的风格,其中加入了电子元素,唱起来抑扬顿挫,而曲子是否婉转美妙她倒不怎么在意。
他无意改变自己站立着的位置,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站得离她更近了,而且独自横亘于她所在的人群与吧台之间。她唱的这首歌,如同许多老歌一样,是关于暗恋的,但又别有一番苦涩的情怀笼上心头。很快,这首歌就转而以背叛为主题了。
唱到颤音和强弱拍时,她就将眼睛闭上。每小节之间,她总会时不时地停上半秒,不是因为要屏住呼吸,而是为了调动起酒吧里众人的节拍,让他们在这首悲伤之歌渐近尾声时,能够聆听得到内心的寂静。
开始唱挽歌了。他母亲再一次地直视着他。她的歌喉比过去更加奔放了,却丝毫不夸张,也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到最后一个名段时,她的目光还是没有从他身上移开。而他呢,则在脑子里构思着如果比她的再高半个八音度,怎么唱下去。他绞尽脑汁,想象着她是怎么做到的,又是如何摆脱掉伴奏的束缚,或者说故意乱其阵脚的。但是他觉得,如果他做好了升降半个八音度的准备,就像她一样,他也可以做到的。然而,他知道现在应该保持沉默,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她,而她也正注视着自己。他感觉得到,她唱到——她的爱情教她迷失了南,迷失了北,迷失了西,迷失了东时,所有的人都在向她行注目礼。尔后,她埋下头,几乎是说出了那最后一句歌词,她的爱情教她迷失了心中的上帝。
一曲终了,她冲约翰?凯乌蒂和斯塔蒂亚点了点头,然后不失礼节地走向了她的朋友们,并没有答谢众人的掌声和盛意。这时,诺埃尔瞅见斯塔蒂亚?凯乌蒂正在看着自己,脸上的笑容亲切而又熟悉,他觉得她知道了他的身份。随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在此地久留。他得去召唤他的同伴们,还要尽可能自然地流露出一种不耐烦的神情;他得让一切看起来并无不妥:他母亲和她的朋友还待在这儿,而他将和自己的朋友离开这儿。
“天啊,真是太厉害了,”他走到靠窗的墙角处时,其中一个朋友感慨道。
“她声音是很不错,”诺埃尔回道。
“那我们是留在这还是怎么的?”他朋友问。
“我跟他们说了,我稍微整一整,就将你们送到卡赛恩。他们都在等着你俩了。”
“我们喝完这杯就好了,”他朋友说。
他看着他们陆续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去,同时,他也不时扫视着斯塔蒂亚?凯乌蒂的行为。她从吧台后面走了出来,正在和几位酒客搭讪,开开小玩笑,但是很明显,她是要过去同他母亲谈话。他猜想,斯塔蒂亚聊上片刻后就会和她提及诺埃尔也在酒吧的消息。事实上,她也完全有可能对此只字不提。另一方面,他认为,这可能是她一开始就要谈到的。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母亲哪怕只要站起来,在人群中搜寻一下自己的身影,他可能就觉得已经足够了,或者,她只是微笑着,无动于衷,面不改色,岿然不动。这些,他都不希望看到发生。
他又扭头看看自己的朋友,发现他们还在喝酒;他们连乐器都还没收拾。
“我去掉个头,”他说。“待会我们就在外面会合。记得把吉米扛上车,我也要带他一块过去。”
一个朋友听后迷惑不解地看着他,这使他意识到自己刚才说得太过掩饰,语速太快了。他耸了耸肩,径直走过酒吧前门边的酒客们,谁也不瞧一眼。屋外,第一辆车前灯全打开了的汽车驶近时,他开始有点打颤。他知道自己要小心翼翼的,守口如瓶,就当这个晚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所有这些都将被淡忘;他们会继续弹奏、演唱下去,直至深夜。他掉转了车头,在漆黑的夜色里,等待着他的同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