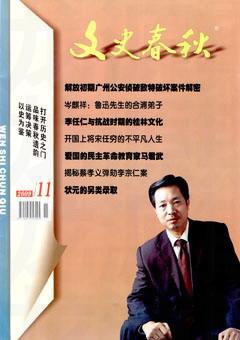配角大师黄宗洛
支 泳
“自己高兴,让别人也高兴,这辈子就没白活!”这是老艺术家黄宗洛对自己艺术人生的评价。黄老粉墨一生,以演配角为主,塑造了百余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给人间带来了欢乐。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主持人敬一丹称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演员,是艺术界的奇人,龙套大师”。
3月9日,我来到北京昌平县黄宗洛居住的王府花园,在传达室与黄老接通电话后,黄老让我们等他来接。过了一会儿,黄老脚步匆匆地向我们走来。见到老人春光满面、笑容可掬的样子,我也不禁为之高兴。王府花园居民区是一大片风格迥异的别墅,路上来往的人不多,但凡见到黄老的人都主动和他打招呼。我们边走边聊,感觉不到黄老有丝毫的名人架子,反而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非凡的亲和力。
艺术启蒙源于天津
黄宗洛出身书香门第,祖籍浙江瑞安,祖辈一门有5个进士,其父在宣统年间赶上最后一拨部试和殿试,分别获得工科进士和翰林院庶吉士两个当时的最高学位,被分配到北平任高级电气工程师。黄宗洛兄弟姐妹7人,与同胞手足相比,他自小略逊一筹,论机敏不如大哥宗江,论才气不如三姐宗英,论长相不如小弟宗汉,但他们4人后来都成了文艺界的大名人。说起来,黄宗洛的艺术启蒙还源于天津。黄父爱看戏,每逢好戏,就在戏院订个包厢,带领全家老小,驱车前往。他所始料不及、完全违背他心愿的是,他这点爱好,在子女中竟熏陶出一批“戏子”。那时宗洛不过四五岁,每逢看戏,他都跟着父亲前往。后来黄家从北平来到青岛,几个孩子在一所很不错的学校读书,学年届满,考试成绩公布,宗江、宗英都得第一名,宗淮第二名,宗洛第四名。校长很赏识黄家子女品学兼优,称他们是“黄门四杰”。过了几年,黄家从青岛迁居天津。黄宗洛回忆说:“我在天津待了6年,在树德小学念完高小、耀华中学念完初中后就回浙江老家了。但由于正处在尚未定型的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时期,对自己的个性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这个从小老实得几乎发呆的人之所以最终下海干上了戏以及在表演上有点成就,深究起来,和我在天津卫所受到的艺术启蒙教育分不开。那时候,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小戏迷,每个月都把零花钱攒起来买票看戏。经常出入小梨园、大观楼、新中央、中国大戏院等场所,迷上了刘宝全、白云鹏、侯宝林等。当年梨园差不多所有的前辈大师的精彩绝伦的表演我都赶上了,此实三生有幸!回到家里还跟着唱片一遍又一遍耐心学唱,生、旦、净、末、丑的角色我都能来上几段,至今还记得的段子仍不下十几段。”
在拍电视剧《泥人张》时,需要有天津特点的市声,而现在的年轻人对此不大熟悉,没听见过旧社会做小买卖怎么吆喝。黄老和北京人艺出身于天津的老演员李大千、牛兴丽聚在一起,一连两三个晚上,硬是根据儿时模糊的记忆,绘声绘色地吆喝出数十种具有天津特色的叫卖声来。说到这里,黄老调动嗓音给我们表演了几种小贩的叫卖声,那种独特的韵味使我大饱耳福。
屡战屡败屡败屡馁
黄宗洛的艺术成功之路比起哥哥宗汉、姐姐宗英要艰难得多,这大概与他的性情有关。他尽管喜爱文艺,平日里爱唱几口,但由于生性腼腆,是个上不了台的主儿。黄老说:“我从小就不大机灵,个头矮小,将满6岁那年,姐姐黄宗英领我参加入学考试,我紧张得要命。主考老师为缓和气氛,问我一个普通常识:‘别害怕,你在家都跟谁玩?我用蚊子般的声音嗫嚅着:‘跟小妹。‘小妹是谁呀?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小妹是我姐!老师一听,对我说:‘连姐姐妹妹都分不清,还上哪门子学呀?回家待着去吧!我们黄氏姐妹里数宗英最小,大家都喊她‘小妹,我也跟着叫惯嘴啦,因此被视为低能儿,拒之学校大门外。最后还是父亲出面让我上了学。
后来在天津读高小时,由于语音纯正,宗英姐和我同被选为代表,参加全市小学生国语演讲比赛。我毫不费力地把讲稿背得滚瓜烂熟,可一登台,见台下一片攒动的人头,就傻了眼,光张嘴不出声,最后当众号啕大哭,被抱下台。比赛结果,宗英全市第一名,我倒数第一名。
几年后,我返回老家读高中,一个业余话剧团见我国语说得好,力邀我加盟并饰演主要角色,没想到我不争气,吭吭哧哧,怎么也不灵光。“光复”后,我考上燕京大学,尽管校园内有两个学生剧社,搞得十分红火,我却望而生畏,再也不敢沾这文艺的边。我努力攻读,一门心思想当个哲学家。”
其实黄宗洛并非无能之人,从小学到大学,他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可有一样,笨手笨脚,不善辞令,怕见人,是个典型的高智商的“低能儿”。
在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时,黄宗洛投奔解放区,进入晋察冀华北联大。校方见著名演员的弟弟来了,想当然地把他分配到文艺学院三部。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命运又把他和演戏硬扯到了一起。建国以后,黄宗洛进城参加演出的第一个大戏是《民主青年进行曲》,扮演一个叫王渔的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导演以为宗洛是个追求进步的大学生,演这个角色必定手到擒来。谁知上得台去,畏畏缩缩,没有朝气,倒有潮气。支部书记以为他有思想问题,就找他谈话,大讲演好这场戏的重大意义。宗洛一脸庄重而又沉痛的神情,对书记的话点头如捣蒜。书记一看,有门:演吧,没事儿了。再一演,依然老样,导演一看没治,痛下断语:“王渔失水,不复救矣!”干脆把这个角色删掉了。此后,导演又让他演与他经历相仿的一个进步青年,他仍是朝气不足,急得曹禺院长直搓手,无奈之下只得又把这个角色删掉,改请他降格演一个微不足道的特务。也不知怎么搞的,他演出来的这个特务并非舞台上常见的那种凶神恶煞的反派,而是咬文嚼字,故作斯文,坏水藏在骨子里,作为舞台形象还相当鲜明。于是人们都说,别看黄宗洛人挺老实,是个大好人,可演正面人物总是不太像,扮个坏蛋啥的硬是没挑。真是邪门了。
黄老说,我平生一共栽了多少跟头,扳着脚趾头怕也数不清。吃演员这口饭可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对俺这号先天不足半路出家者而言。我十分羡慕那些天才,他们跟闹着玩似的就演起戏来,居然一时红得发紫。咱天生就是“蠢”才,兢兢业业,从来不敢怠慢。我的诀窍就是苦干、笨干、加傻干!对某些人来说,干艺术好比登天堂之路——步步高;而我叩响的却是地狱之门——受尽磨难,苦海无边。
“走火入魔”
黄宗洛几次出师不利,不少人认为他不是当演员的料。但是他在向艺术艰途跋涉中所表现出来的罕见的至诚精神和所下苦功,确实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上世纪50年代,北京人艺常上街演活报剧。这种剧被
称为“一脚踹”,就是演一次就完的意思,很少有人对它下功夫。黄宗洛却不。有一次他演一个蹬三轮的,大轿车载着演员赶到演出地,他却光身穿件号衣,浑身大汗地蹬着三轮追着汽车跑,为的是赶到那儿说句台词。为了逼真,他不用油彩化装,直接用黑红颜料往全身涂,涂了洗,洗了涂,直到颜色渗进毛孔。他蹬车闯进演区,群众以为他误入,大喊:“喂,蹬三轮的,人家演戏呢,瞎闯什么呀!”正在演戏的演员将错就错,“喂,这位师傅既然闯进来了,让他说说家里生活的变化吧!”黄宗洛顺水推舟演起自己的角色。他的苦肉计取得极佳的演出效果。戏只演了一次就完,可他这身黑红皮色再也洗不掉了,他足足冒了半个来月的红汗,不知染了几身衣服,才露出了皮肤的本色。
不久,北京人艺排演《龙须沟》,黄宗洛争取到一个名额,他设计自己的角色是个卖酸梨的老头儿。他整天沉浸在角色里,到梨摊上观察穷老头的神情状态,与他们唠嗑,问行情,摸门道。卖梨的老头还以为他也要干这营生,直叹气:“年纪轻轻的,但凡有条路可走,也不要寻摸着干这买卖。”黄宗洛还真干上了,他穿了一身破棉衣,弄得面目黝黑,见人就吆喝:“卖梨咧,皮薄水多倍儿甜!”有人买,他就卖。为了这个角色,寒冬腊月做了半个月的买卖,光梨就糟践了几十斤。演出时,这个角色猫在窝棚旮旯里,一声不吭,一动不动,背还冲着台口,连个灯光都打不到,观众只知道有一堆人在那里,都是来躲雨的。
就为这,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走火入魔!可黄宗洛觉得应该这么干,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艺术,对得起自己。
路边无名草怡然傲风霜
人们往往把一出戏的主要角色比作红花,把次要角色比作绿叶。黄宗洛演了多半辈子的戏,多半演的是不起眼的群众角色,他自比为小草。可是他只要逮住点戏就不撒嘴,没完没了地穷琢磨,创造角色的积极性一来,谁都拦不住。就凭这种对艺术的执著劲,开创了配角艺术的新天地,被誉为“小草”、“小角色之王”、“龙套大师”、“百面人”。
1958年,黄宗洛在《智取威虎山》里一赶四。第一幕,他演一个老山民;第二幕,他演一个小和尚;“威虎厅”一场,他演匪兵丙;下场后再出台,成了解放军。忙是够忙的,可就是没什么戏。他挖空心思要出“幺蛾子”。他为匪兵丙设计了一段“丑表功”的戏。整整十几天,他穿着黄狼皮大衣,脸上涂成烟灰色,一会流鼻涕,一会流口水,一会躺在炕上抽大烟,一会对着镜子练习下唇包着上唇说话。演完戏,下巴差点儿再也缩不回去。
一切准备就绪,导演允许演员各显神通的时候到了。匪兵丙正躺着吸大烟,猛听“座山雕”下令到夹皮沟劫火车,他一下子坐起:“啥……炸火车……”哧溜吸一口口水,“弟兄门,抄家伙,”忙不迭下山。再上来的时候,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气急败坏地报告劫车经过,端出了他那段自编的“丑表功”,他结结巴巴地说:“报告三爷,有事儿,有事儿。昨夜晚,我奉您将令,随兄弟们下山。到了夹皮沟,埋好炸药包,眼瞅着小火车开到,‘轰地一声响,火车‘趴窝啦。兄弟们赶紧往上冲,到跟前一看泄了气,尽是些皮子、拌子、药材啥的。兄弟我一想不能空手回呀,一看押车的不多,就七八杆枪,弟兄们胆子也就壮啦,都往乘客身上打主意,有什么撸什么,弄好了顺手捞个娘儿们回来。谁知这批光棍儿,个个不含糊,尽使手榴弹招呼,不一会儿,二十几个兄弟就为党国尽忠咧,要不是小子我两腿跑得快,小命也就早就完了。”
这一长段道白说的是东北怯口,借鉴“贾桂念状”的技巧,用京剧的“贯口”一气而下,急冲冲句句入耳,说铿锵却又阴阳怪气,“丑表功”凶相毕露,狼狈样可气可笑。再看那副尊容,使场上个个笑倒。他头发直立着,一只耳朵被炸飞了,用胶布粘着,两条手臂上套着抢来的镯子,帽子套在光脚上。
这段戏符合人物性格,导演一锤定音,认可了。
正当黄宗洛走出背运,出成果称奇才的时候,中国话剧的骄傲《茶馆》开张了,黄宗洛接过了松二爷这个角色。松二爷是个没落的八旗遗老(已是城市贫民),但是贵族阶级的遗风犹存。黄宗洛经过考证,此人有3大特点:硬充外场人儿,尽干老娘儿们事;已经穷困潦倒,却忘不了过去摆排场的谱;善良懦弱,讲究礼节到了可笑的地步。他给松二爷编了4句定场诗:礼多人不怪,和气难生财;命运何多乖,到死不明白。为了饰演好这个角色,黄宗洛仔细研究旗人习俗,然后身体力行,以人物姿态走向生活,接受社会考验。他翻出箱底的长袍穿上,腰带上挂了13件小零碎儿:挖耳勺、荷包、玉佩、鼻烟壶……扎上裤腿,蓄须养指甲,弄一把梳子,划拉那3根半鼠须。他又寻摸到一只黄鸟,把个鸟笼的铜挂擦得锃亮,提个鸟笼往茶馆一坐,活脱脱一个八旗子弟。除了形似外,黄宗洛在这出戏里还根据剧情的需要,通过形体语言和内心活动,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比如,当松二爷和常四爷久别重逢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有嘴唇和面部肌肉不停地抽搐;再如,他碰上两年前曾抓他的那人,慌忙上前请安,同时他的小腿肚子一个劲的哆嗦。旗人的问安礼很有讲究:进一步退两步,左腿弓,右腿蹬,收腹倾胸斜左肩,顺势杵下右胳膊。黄宗洛每日苦练,在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中外观众叫绝。
看完戏后,已故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著名导演邓止怡评论说:“人艺不仅有于是之这样的演员,也有以黄宗洛为代表的这样的演员,一点戏也要翻过来倒过去琢磨出戏来。”《茶馆》不仅赢得了国人的赞许,经久不衰,而且在国外演出也大获成功。
晚霞自多情
当黄宗洛干得正欢实的时候,不知不觉到了离休的年龄。1987年,黄老办了离休手续,怅然告别舞台,封箱戏是那出描写老年生活的《遛早的人们》。至此40余载,以跑龙套始,以跑龙套终,可谓善始善终。
然而,下了台,未容他喘息,更来不及闹情绪,便不由自主地被裹进了拍摄影视的大潮,一部接一部,马不停蹄,欲罢难休。黄老说:“我给自己算了一笔账,这几年我参加拍摄的影片不分角色轻重,约20多部,属北影厂的就占13部,难怪我会被观众认为是北影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再加上人艺与北影这两个演艺界的老字号在艺术风格上的诸多共同之处:细腻、真实、严谨,都擅长古典题材、文学名著及北京地方色彩,遂使得我这后生老头子和北影一拍即合,逐步地被演化过去,掰也掰不开啦!”
黄老自进入影视圈以后,一年下来,几乎月月有新贡献。不光跑龙套,赶上了也演一号人物;不光演反
面人物,也演正面人物,就连老娘儿们也反串过好几回,还不算那几回演太监。他在电影《找乐》、《远离战争的年代》、《月是故乡明》、《吉祥胡同》里演的都是一号人物;在《王家第一军》里演唱着山歌从容就义的地下交通员;在电视《不知其名的人们》中演归侨老妪:戏曲小品《王婆训子》里演王婆;《难得一笑》里演洋妞儿。他演的几个不同性格的老太监分别出现在影视剧《红姑寨》、《深宫疑案》、《新龙凤呈样》和《大宅门》等剧中。
在《宫廷斗鸡》这部荒诞不经的古装喜剧片中,黄老演的皇帝是一个坐天下没多少年,还没脱离农民习气的开国之君,对宫廷中那套繁文缛节很不习惯,几乎到了厌恶的程度。平时言谈话语也很随便,活像个老小孩。编导王扶林在构思这个人物时,眼前经常出现黄宗洛的音容笑貌,便让黄老来扮演这个头号人物。黄老演起来特别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从始至终无拘无束地撒开了演,足足过了把戏瘾。
黄老在话剧界名气不小,可没拿过什么大奖,而进入影视界却实现了零的突破。他因在电影《田野又是青纱帐》中扮演了丁花先生,获吉林省百花奖;因在电视剧《擎天柱》中扮演卖耗子药的,荣获第十三届飞天奖最佳男配角奖;因在《找乐》中演老韩头,在以发掘新星为宗旨的希腊塞萨洛尼基第34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表演金奖;紧接着同一角色又在法国楠泰尔市第17届亚非拉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一个金热气球奖杯。
谈到取得的成就,黄老感慨地说:“按说到了我这把年纪,已然迈过了老祖宗定下来的标志,进入暮年,古稀早过矣!可我总感觉心气儿正旺,还有好多的劲没有使出来。人们疑心我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啦?其实也没别的,我的诀窍是:精力不够,重点使用,一门心思都扑到角色身上,什么成败得失一概置之度外。再加上老妻贤惠,家庭和睦,儿女争气不让我操心,吃得好、睡得香、干得欢……才潇洒一番,不知老之将至也。”
黄宗洛的“老秘”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黄老的老伴尚梦初,黄老说,如果没有老伴的支持,自己的事业不会成功。
黄宗洛与尚梦初在北京人艺正式建院时相识,从相爱到结婚谈了四年。尚梦初多以小孩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如曹禺名著《日出》里的小东西,高尔基名著《耶戈尔·布雷乔夫》中的小修女,刘厚明作品《山村姐妹》中的小丢,苏脸作品《青年的火焰》中的红军小战士等。她曾获得青年积极分子的称号。她和黄宗洛成家后,给了丈夫很大的支持,在丈夫时运不济、净走背运的时候,她没有看不起丈夫,而是给予安慰;丈夫碰了钉子,她给化解忧愁。她退休后,成了黄老名副其实的“老秘”。黄老三天两头外出演戏,生活上的事尚老全包了,做饭、洗衣,为黄老打点行装,准备道具,事无巨细,缺一样也不行。这些年,找黄老演戏的主儿越来越多,哪些剧本好、哪些角色适合黄老去演,尚老要一一审查,决定取舍。尚老的手中备有好几大张黄老的人际关系联络图,她一查一个准,比黄老还清楚。因此,有人想找黄老的熟朋友演节目,不用问黄老,直接问尚老就行。这样一来,可省出不少时间,让黄老专心致志地去琢磨自己的角色。尚老也是黄老的戏迷,不过是专门挑黄老刺儿的戏迷。哪儿演得不佳、形象不真,她都要给指出来。为了照料黄老的生活,有时黄老到外地演出她也要跟着去,由于她比黄老小7岁,人又长得年轻,还常常闹出误会,别人以为黄老还有个“小蜜”。一次,黄老携夫人回故里参加《宫廷斗鸡》的首映式,入场时台下议论纷纷,意思是“老来花”,挎个“小蜜”出门,以壮声色,那是司空见惯……黄老面不改色地走上台去,当着观众的面指着身边的老伴大声宣布:
“这位女士芳名尚梦初,乃敝人原配夫人,别无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