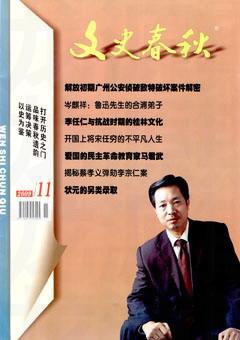换了一个人生新世界
梅家荣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发动莱芜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嫡系第七十三军和桂系第四十六军等;同时,俘获了以济南战区第二绥靖副司令官李仙洲为首的将军19人。我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俘虏(下称“解放”)而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并深切感悟到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下面是我的亲身经历。
被俘前后
我获“解放”过来后,解放军在战场上就地把我分配到第四纵队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二营重机枪连的第五班当战士,没有任何的关押。
开始我仍有点焦虑之感,但到班里后大家都叫我为“同志”,使我心神安定。部队开赴潍坊休整时,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中有“不虐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由此打消了我心中的焦虑。
更使我感到舒心的是,每周一次的民主生活会,大家都畅所欲言,既开展自我批评,也可以向战友和排、连干部提出建议和批评。每次排、连领导到班里来,都是满脸笑容听取意见,从不见有怒骂声,更不见有打人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排、连干部都是与我们同吃一锅饭,不见有任何的特殊化。当时,干部与战士享受同等待遇,都是每人每月领取津贴费1元鲁币。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到在人民军队中,战士之间、上下级之间都和睦相处,亲如手足。
上述的经历,与我被“国军”抓去当挑夫和在“国军”当兵两年多的生涯截然不同。
1944年秋天,日军入侵广西,并到了我的家乡——平南县官成区。当时我17岁,正在“杏和堂”药店当雇工。为躲避日军,老板要我和一位老雇工挑着贵重的药物送往他的亲戚家。我们走到中途时,恰遇到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北撤(后来我才知道部队的番号),部队的一个班长强行抓我。
当晚,部队抵达一个村子,煮饭吃了之后又急速行军,班长责令我挑两箱子弹,几名战士还把米袋推来要我一起挑。部队为逃避日军,向广西的西北部急行军长达1个多月,却从未给我发放衣服和鞋子。在此期间,曾在柳州市附近驻防及与日军作战近10天。
一天,日暮降临,部队住进一个小山村煮饭吃,饭后又要急速出发爬山。我因难以坚持而逃跑出来,跑到半山腰的一棵大树下睡了一觉。
天亮后,我按原路往回走,想不到仅走了一段路,恰遇桂系第四十六军一七五师五二四团二连(上述番号也是后来才懂得)拦截。我如实地向他们说出是被抓出来当挑夫,家里只有母亲一人,要求回家。一名军官用白话(粤语)对我说:“你家平南县离这里有数百里,沿途不少地方被日军占领,还在打仗,走在路上会被其他部队甚至会被日军抓住。”接着,有几名士兵虚笑:“想回家?能回到家吗?!”我听后实在感到无可奈何,只能跟随他们,成为当时抗日战争中的一兵。
在该部队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感到官兵之间如隔墙隔火,从不见有军官前来相聚,经常看见的是他们对士兵的怒骂甚至毒打,令人触目惊心,所以有不少人逃跑。我目睹逃跑离开部队的就有两人,其中一人是上士班长,不知他做错了什么,被连长勒令趴在地上,当着全连士兵的面,用竹杆狠狠地打他的屁股,打得他“唷唷”直叫,站起走路时一拐一拐的,当晚便隐逃而去。日本投降后,我本想逃跑回家,但身上既无钱,又不认识返家的路,更害怕在逃跑中被抓回来遭到毒打,所以没有逃跑。我获得“解放”过来后,就有“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同是一家人”的深切感受。部队不仅严格执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而且每到一处住地,为使居民安心,班长和其他人都热情地向群众解说:我们是“新四军”,和八路军同是一个部队(注:解放军在发动山东省的莱芜战役前,因需急行军和投入战斗,所以,在约1个多月前已撤销“新四军”的番号,但未能向广大战士作传达;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已合并统称为华东野战军,而部队所到之处战士只能向群众说自己是“新四军”)。在住处,全班同志都争抢着为群众挑水和做其他家务;离开前,又积极地搞卫生并为水缸挑灌满水。
1947年7月,部队胜利完成孟良崮战役后,奉命向鲁西南出击,直捣“国军”占领的安徽省和河南省的一些县。
有一天,部队进驻一个村庄时,看见全村的梨子树结果累累,连长说:“不摘群众的果子!”全连同志低头穿过密密的果树时都无人摘果。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在山东枣庄休整。因当时处于战争的艰苦年代,当地居民十分缺粮,多是吃花生壳磨成的粉末,连同麦片煮食充饥。为帮助群众度过饥荒,部队每人每天少吃3两小米送给群众。凡此种种军爱民之事极多,实在说不完。
至于民拥军之事,也是举不胜举。部队在潍坊休整时,经常有群众送来枣仁、花生等食物,帮助战士修补衣服和鞋袜,妇女多次组织“扭秧歌”给我们观看,还邀请我们一起参加。休整期间,我们每人分配到两双布鞋,都是当地解放区的妇女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同年5月,我们部队在攻打孟良崮战役中,当地的群众食物短缺,但他们仍倾心拥军支前,频频送来地瓜(红薯)干给我们煮吃。每次战斗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送粮食、抬担架的群众更是蜂拥而来。
谈及“国军”与民众的关系,可以说是异样的世界。我在童年时,就曾听到过“兵一过,篱笆破”这样一句流行的俗语。这说明“国军”不仅疏离冷对群众,还经常偷摸和抢劫群众的物品。
在跟随桂系四十六军时,部队在东兴县度过春节后移驻到都安县。当时,每天仅是吃两餐粗米饭,而副食品及油盐都没有。于是,全班人员在每天夜间,分批去偷挖农民的红薯、芋头和偷割蔬菜,还多次偷杀农民的牛和羊。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小空地进行练枪训练时,突然跑来十几头牛,当时无人看管,在排长的责令下,几名战士匆匆跑去将一头约100斤重的牛拖住用刺刀杀死,就地将牛烧烤吃掉。“国军”如此种种严重脱离民众的行径,如何能获得民拥军呢?
政治教育
我被“国军”抓去当挑夫和当兵的两年多时间里,从来没有听到过“政治教育”。日军投降前,我还有“抗日救国”的、思想观念,但日军投降后,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之事我却是一概不知,也不懂。
1946年秋天,当时我所在的桂系四十六军,开赴进驻广东省的海南岛,接收日军投降所交出的武器,然后我们的连队奉命上山“剿匪”。剿什么“匪”,我百思不得其解。同年冬天,部队从海南岛乘船北上抵达江苏省南通县,休整一段时间后,又乘船到山东省青岛市,接着徒步跋涉到平度县兰底镇驻下。在当地度过1947年春节后,又徒步向莱芜县开进。
当时我只知道要打仗,但
为什么要打仗?与何种部队打仗?军官不作任何的“宣传解说”。部队抵达莱芜县城时,我看见城墙上用白石灰涂写着“朱毛不死,和平难止”的大标语。何为“朱毛”?我大惑不解。我从幼年读书,随之当雇工,及后来当“国军”的挑夫和士兵,都没有受过“政治教育”,加之当兵后从未看过报纸和书刊,所以不知道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1947年2月,我所在的桂系四十六军开赴莱芜地区打内战。一天,部队从县城徒步出来抵达一片开阔地时,还没有发射一枪一炮,即被强大的华东野战军俘获。
因为我不知道也不认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以“解放”过来后,仍一度存在着“在哪里当兵都是为了混饭吃”的思想。
随解放军部队在潍坊休整时,除军事训练外,还开展了一次谈家史的阶级教育。我们全班同志的家庭几乎都是雇贫农或贫民,在谈家史时,人人都悲痛流泪。
谈完家史后,司徒教导员向全营同志作了一次讲话,让大家明白,当时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是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广大贫雇农民和工人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所以,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都十分贫困。他接着说,共产党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使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广大工农群众得到彻底的翻身解放。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解放军是为人民谋解放的军队,所以军民之间血肉相连,部队在行军和打仗中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次谈家史及聆听教导员的阶级教育,是我出生以来受益匪浅的“提神醒脑”的教育,使我从人生的浓雾中看到了光明,深深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理念,从此,树立了永远紧跟共产党、勇当人民解放军的决心和信心。在随后部队频繁的行军和战斗中,我从未有过“开小差”的念头。
光荣入党
1947年5月,部队经过在潍坊约3个月的休整后,奉命攻打孟良崮,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王牌军”的整编七十四师。在这次战役中,我所在的营担负保护陈毅、粟裕前线指挥部的任务,虽然频频遭受到敌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但我并没有惊恐逃跑。
随后,为了从战略上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对山东省的重点进攻,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部队急行军向鲁西南出击,先后抵达安徽省和河南省的一些县,并先后与国民党军队战斗十几次。在这次行军战斗中,全班同志推选我为“记功员”,记载全班同志在行军和战斗或在群众家中的行动表现和事迹。我们是重机枪连,各班都有1挺重机枪,在行军期间,有时分配我扛机身,有时与其他同志共抬枪架。在一次战斗中,排长要求我当他的通讯员,对于以上分工,我从来都是愉快接受。
行军急速,我们连续有29天不能好好睡眠。一天晚上,部队要攻打山东省的费县,为了用重机枪射击驻守在县城的敌军阵地,全班同志都蹲泡在约半米深的水坑中,几个小时后,大家背着被水浸透的背包开始行军。对于这些困难,我始终坚持克服,从无怨言。由于我在行军和战斗中表现积极,所以,在一次开大会中获得表扬,并奖给一个笔记本,连队还将缴获的1枝钢笔和1个口琴送给我。
同年12月下旬,部队奉命攻打河南省临近京汉铁路的确山县,并在该县的一座高山上度过了1948年的元旦。接着,部队向北撤退,于1948年3月到达濮阳县休整。4月,由于我表现良好,排长唐振忠和副班长罗先全作介绍人,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家乡解放
1948年12月,部队奉命配合开展淮海战役。当时我担任班长,与其他班长一起被机炮训练营的领导留下来,共同负责对在这次战斗中被“解放”过来的“国军”战士进行看护和训练。我看护一名广东籍的战士,他文化较高,声称“国军”强大,提出要我与他一起逃跑出去。我当然不会听他的,而是向他述说解放军良好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说解放军队伍中有不少是从“国军”解放过来的战士,有的已经得到提升,还有的加入了共产党。他听了我的劝导后满脸笑容,当即表示要与我一起当好人民解放军战士。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我惦念母亲之心日益深切。
一天,我从报上看到广西省“水上门户”——梧州解放的消息,心情兴奋异常,当即给以前的药店老板朱德三写信,迫切地请求他帮助寻觅我的母亲,不久即接到母亲的来信。母子别离整整10年,从此又通了音信。
后来我经常给母亲写信,也经常接到母亲的来信。我给她寄去参加人民解放军的“证明函”后,当地的官成区人民政府立即发给我母亲“军属荣誉证”。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我母亲(含养女)申报自己家庭为无田的农民,官成区人民政府即将3亩多的良田分配给我家,并分给没收地主的一幢3层泥砖楼房。
抗美援朝
1952年秋,我所在的部队奉命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斗。部队抵达朝鲜不久,我被提升为连队的副指导员,在随后的浴血战斗中,我又荣立三等功。
朝鲜停战后,1954年7月下旬,我被任命为连队特别指导员,与山东籍的连长安锡宝共同带领我们二十三军全军近300名湖南籍战士复员回乡。
在湖南期间,我写信给母亲,祈盼她前来相聚。不久,母亲真的来到我们部队的住处。她见到我时,兴奋得满脸笑容,又频频地流泪。与母亲聚别后,我便从湖南衡山乘车返回朝鲜。到达部队驻地后不久,自1955年春开始,志愿军部队所有军官都可以免费从朝鲜回国返家探亲。于是,我于1955年7月,返回已经别
2006年7月。作者与妻子结婚50周年纪念照。离11年的家乡,又见到了母亲,与她相聚了20多天。1956年8月,我再次请假回家结婚。1957年9月,我回家带着妻子一同到朝鲜居住了几个月。自朝鲜停战后,部队便转入帮助朝鲜人民从战争废墟中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直到奉命撤军回国。
1958年夏天,部队从朝鲜撤军回国,在黑龙江省驻扎6年,后来,我被授予大尉军衔。1964年10月,我转业回到广西,分配在自治区党委财贸政治部工作。不久,我调任广西艺术学院院长,从此,步入了一个与全家共享幸福生活的新世界。
——献给第一线的交警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