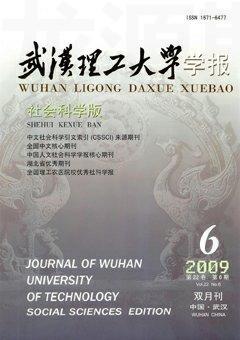日本再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分析及借鉴
肖 萍
摘要:日本法学界就再逮捕问题存在着不同学说和判例。关于再逮捕的要件,上诉审法院应当在上诉审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并且法官形成了有罪的内心确信后,方能决定逮捕。在我国,对被告人的再逮捕决定,应当由第二审法院在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后作出。
关键词:日本;逮捕;再逮捕;无罪判决
中图分类号:D908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16
一、序言
再逮捕是指依第一审无罪、缓刑等判决的宣告,不等判决生效即被释放的被告人,在检察官抗诉后的再次逮捕。在日本,再逮捕的时间和要件问题,因“东电OL杀人案件”特别抗告审的决定[1]而受社会及刑事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的规定,在无罪、缓刑判决等情况下,一经宣判,不等判决生效,被告人就应该被立即释放。但是,日本刑事诉讼法同时承认对于无罪判决等裁判的检察官抗诉权,如果检察官对逮捕状失效的无罪判决提起抗诉,继续上诉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已经因逮捕状失效而被释放的被告人是否可以再次被逮捕的问题。如果可以再逮捕被告人,由于规定逮捕要件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没有就法院逮捕被告人的时间做限制性的规定,对于再逮捕的时期及其是否需要附带限制条件也都成为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日本关于再逮捕要件的主要学说
关于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规定的依裁判宣告而逮捕状失效后的再逮捕问题,现在日本的通说是在原审级不允许再逮捕,而肯定了在上诉审时可以进行再逮捕。日本最高法院也通过“当发生新的刑诉60条各项规定的事由的情况下,不存在禁止在控诉审重新签发逮捕状的法律”的判决[2],承认了控诉审后的再逮捕。但是,关于再逮捕的时间和要件存在着五种不同的学说。这些学说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一)团藤说:上诉审法院可以随时按照第一审的标准再次逮捕被告人
团藤重光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上诉提起后,上诉审法院可以在不特别附加其他条件的情况下,随时按照与第一审相同的标准再次逮捕被告人[3-5]。即使被告人在第一审中被宣告无罪,也不能否定被告人尚存有作为逮捕理由的嫌疑。因此,被告人即使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的规定被释放,也可因存在逮捕的理由,随时被再逮捕。但是,此学说的结果就是造成对被告人的人身羁押的继续,使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确认的对于所规定的裁判的逮捕状失效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日本最高法院东电OL杀人案件的特别抗告审决定即采用了此学说。日本最高法院认为:“法院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犯有罪行的情况下,如存在刑事诉讼法60条1款各号规定的事由(以下称为‘逮捕的理由),且有逮捕的必要性时,依照该条款,可以依职权逮捕被告人,就其时间没有特别的限制。因此,第一审法院即使以没有犯罪的证明为理由宣告无罪,控诉审法院通过笔录等的调查,经过研究上述无罪判决的理由,尚认为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时,就存在逮捕的理由。并且,为了控诉审的公正、迅速的审理,只要认为有逮捕的必要性,不论其审理的阶段,均可以逮捕被告人,并不像论点所说的必须等到调查到新的证据。”[1]这就肯定了控诉审法院有再逮捕的权限,并且明确了对于逮捕的时间和要件在法律上没有特别的限制。但是,本决定同时还包括远藤光男法官和藤井正雄法官的反对意见。
此外,最高法院昭和41年(1966年)10月19日决定[6]、最高法院平成11年10月13日决定[5]和驳回对东电OL杀人案件的逮捕裁判的异议申请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平成12年(2000年)5月19日决定[7]也与此学说一致。
(二)青柳说:上诉审中出现新的逮捕必要时可以再逮捕
青柳文雄教授认为,上诉审中发生新的逮捕事由时可以再逮捕被告人[8]。但是没有明确“发生新的刑诉60条各项规定事由的情况”具体指什么。最高法院昭和29年10月26日判决与此学说观点一致,是控诉审法院在接受检察官对第一审法院的缓刑判决的控诉后,在第一回开庭日前,将被告人再逮捕的判例。对于本判例,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即使在第一审判决因对逮捕中的被告人宣告了缓刑而使逮捕状失效(刑诉345条)后,当发生新的刑诉60条各项规定事由的情况下,不存在禁止在控诉审中发布新逮捕状的法规。”[2]
(三)小泉说:上诉审预计撤销一审判决后可以再逮捕
小泉祐康法官认为,只有在可以预计上诉审会撤消一审判决,而且其内容只能是需要羁押的例外情况下,才允许再逮捕[9]。这种学说虽说条件是预计撤销一审判决,但是就其时间和方法都没有提及。那么,如果只是阅读一下诉讼笔录就预想会撤消一审判决的话,此时的再逮捕也将变为可能。这种学说只是限于单纯的运用理论①[10],对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几乎没有意义[11]146。
(四)村井说:上诉审法院获得有罪的内心确信后可以再逮捕被告人
村井敏邦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经过实质审理,控诉审法院获得有罪的内心确信后,方可允许再逮捕被告人[11]153[12-14]。这种学说要求再逮捕的前提是存在更加高度的有罪判决可能性的嫌疑,并且,增加了再逮捕时间上的制约。
东电OL杀人案件的东京高级法院第五特别部的决定与此学说观点一致。东京高级法院认为:“根据无罪判决释放的被告人的人身,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再次羁押的解释太过缺乏通融性。但是,为了再次羁押依无罪判决而被释放的被告人,应当认为需要某些条件使再次羁押正当化。而且,在以前的司法实务中,第一审的无罪判决后由控诉审逮捕被告人的案件也被认为是在控诉审经过审理得到有罪的内心确信后进行的。没有见过连实质审也没有进行的上级审只通过在无罪判决后马上借出笔录,就再次颁发逮捕状的先例。” [15]
(五)岩田说:当上诉审撤销原判决后可以再逮捕
岩田诚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逮捕状失效的情况下,就作为该判决对象的犯罪事实,在包括上诉审在内的案件审结以前的同一诉讼中,除了上诉审撤销原判决,判处禁锢以上的实刑后;或者退回原审重新审理后,有逮捕的事由及逮捕的必要性外,不能再逮捕被告人[16-17]其理由是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规定的裁判都是以旨在不对被告人的人身进行羁押为内容的,只要上诉审不撤销原判决,再逮捕就与第一审的裁判效力相矛盾,因此不能被允许。
三、对于日本再逮捕要件的分析
引起再逮捕问题争论的东电OL杀人案件的被告人是非法滞留日本的外国人,如果不及时对释放后的被告人进行再逮捕,按照日本《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规定,作为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将随时有可能被遣返回国[18]。检察官为了确保该被告人能够留在日本接受审判,希望尽早再逮捕被告人。如果抛开此案被告人的特殊身份,上诉审法院在决定再逮捕时应依据怎样的再逮捕要件呢?以下结合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逮捕要件的规定,以第一审无罪判决后检察官抗诉的情况为例,探讨再逮捕的应然要件。
(一)严格限制上诉审中的再逮捕要件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了逮捕的要件,但并没有对逮捕时间加以限制。而且如果从第60条是位于总则中的规定这一点出发,有逮捕权的是诉讼所属的法院,并不需要考虑其所在审级是显而易见的[11]149。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上诉法院要对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的规定逮捕状失效并被释放的被告人进行再逮捕的时候,只要法律上对于逮捕的时间没有特别的限制,也就能够导出直接适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的结论(即团藤说)。但是,正如东电OL杀人案件特别抗告审决定中藤井正雄法官的少数意见和东京高等法院第五特别部决定所指出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将变为“实质上的空洞条文”。第一审无罪判决情况下的控诉审法院进行逮捕时的嫌疑,至少应该比第一审逮捕时的嫌疑程度更高。
青柳说和小泉说均对再逮捕设定了条件,往往被认为在学说上较之团藤说更加有力。但是,这两种学说所提出的要件在解释上还留有余地,因没有明确再逮捕的具体时间,在司法实践中有被肆意运用的危险,因此也是不妥当的。
只要日本现行法律存在上诉制度,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就是以在控诉审中有可能出现撤销无罪判决为前提的规定[16]。如果是这样,关于无罪判决后的被告人再逮捕就不应该只是与第一审一样的适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的逮捕要件,而应该受到某些严格的限制。
(二)明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要件在再逮捕中的适用标准
第一,无罪判决后的控诉审中的“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的判断基准要求比第一审具有更高的嫌疑。
关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作为逮捕的要件被要求,无论是基于检察官的请求而由法官进行的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还是第一审法院依职权对被告人的逮捕,还是控诉审法院的逮捕,至少从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是没有区别的[19]。
如果只是简单地就怀疑的程度作为问题,那么作为逮捕实体要件的“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的怀疑较之为宣告有罪判决的“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确信”的怀疑程度更低。至少有“合理怀疑”存在,就应判为无罪。那么,无罪判决后检察官上诉的情况下,控诉审法院仅从笔录中就找出“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只通过对笔录的审查就再逮捕被告人是不妥当的。
东电OL杀人案件特别抗告审中发表了反对意见的远藤光男法官和藤井正雄法官也在决定中阐述了“被告人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且存在刑诉法60条1款各项规定的事由及其必要性时,法院可以按照该条规定,依职权逮捕被告人”的观点的同时,认为再逮捕时的“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的判断基准要求比第一审更高的嫌疑,再逮捕的判断时间也应被限制。
第二,无罪判决后的控诉审中存在再逮捕事由和再逮捕的必要性可能降低。
逮捕被告人需要具备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的逮捕事由和逮捕的必要性。该条款规定的逮捕事由中,第1项“住居不定”和第3项“有逃跑的可能”都需要从逮捕的必要性角度出发进行探讨。而关于同条款第2项“有隐灭证据的可能”在控诉审中出现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检察官在第一审的时候就应该完成了举证工作。而且,日本的控诉审作为事后审,对于调查取证是有限制的。对于误认事实的,只有在由于不得已的事由在第一审辩论结束前没能请求调查的证据,且是影响判决的能够证明事实的误认证据,才必须加以调查(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3条第1款但书)。因此,第一审无罪判决后被告人出现新的隐灭证据的可能性非常小。
逮捕被告人还要求被告人必须有逮捕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即使被告人具有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的逮捕事由,但是没有逮捕的必要性时,也不能逮捕被告人。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的规定,第一审审判时被告人有出庭的义务。因此,在被告人具有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第1项“住居不定”或者第3项“有逃跑的可能”的情形时,原则上认为具有逮捕的必要性。但是,在控诉审中,被告人没有出庭的义务,只有为了实体的真实发现,出现需要讯问被告人等有确保被告人在开庭日出庭的必要性,且被认为通过传唤难以保证被告人出庭的情形下,才具有逮捕的必要性。
(三)日本再逮捕理论的总结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在审判过程中,不能出于保证刑罚执行的目的而逮捕被告人。逮捕的目的是保证裁判的顺利进行,而不是保证刑罚的执行。也就是说,只要能够保证在需要被告人到庭的时候,被告人能够按时到庭,并且被告人没有隐灭证据的危险性,就不应该对被告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
综上所述,关于控诉审中的再逮捕问题,应当作如下考虑。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是判决的内容直接反映到对人身处置的规定。第一审进行了无罪判决后,判断是否满足逮捕要件及必要性时,要求必须比起诉前和第一审审理时的逮捕更为严格。即使存在逮捕要件的“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以前存在“合理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控诉审的逮捕要件与第一审的逮捕要件相比,需要更加高度的怀疑。为了确认这种更加高度的怀疑,作为事后审查审的控诉审法院需要经过实质的审理。正如村井说的主张,上诉审法院应当在实质审理后,否定一审中夹杂的合理怀疑,获得有罪的内心确信后,决定再逮捕。
四、日本再逮捕理论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无罪等判决后立即释放的相关规定,并且承认检察院的抗诉权,同样面临着再逮捕的问题。但是由于司法实务中的运作方法规避了该问题。
(一)我国的再逮捕问题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73条第2款也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如果被告人在押,公安机关在收到相应的法律文书后应当立即办理释放手续”。根据上述规定,我国与日本相同,在第一审无罪判决宣判后不等无罪判决生效,就应该立即释放被告人。
那么,针对再逮捕问题,我国为什么没有如日本一样引发理论争论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规避了此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9条中的“立即释放”应该理解为完全解除强制措施。而在司法实践中,一审判决被告人无罪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并立即释放后,为保证一审后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人民法院一般对被告人采取变更强制措施的方法,即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尽管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均是“限制”但“不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它们毕竟都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对于已经被法院宣告无罪的人,无论采取何种的强制措施,都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此外,由于司法行政上对于办案指标的要求等因素的影响,也使无罪判决的案件所占比率极低,从而使再逮捕的问题显得并不那么突出。但是,这并不能表示不存在再逮捕问题。
(二)再逮捕的决定应由二审法院的法官在形成有罪心证后作出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的规定,逮捕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那么,一审被判无罪的被告人在二审时的再逮捕应该由哪个机关来决定呢?
就此问题,2001年1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由谁决定对原审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并通知其出庭等问题的复函》中指出:“由于人民法院已依法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并予释放,因此不宜由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认为其有罪并提出抗诉的,应当由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再逮捕的决定权赋予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商榷的。其一,检察机关对于无罪判决提出抗诉,理所当然的是认为被告人有罪。这就难于避免检察机关在抗诉的同时,对被告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这样一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规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5条对提出抗诉的方式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将抗诉书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抗诉不当,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撤回抗诉,且需要出庭支持公诉。如果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决定对被告人进行逮捕,而上级人民检察院又撤回抗诉,不仅造成司法浪费,也会有失检察机关的威信。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拥有再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它的合理性值得再研究。
就逮捕权限而言,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对象应该是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中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对象则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需要逮捕的被告人。对于二审中被告人的逮捕决定,也应该由人民法院作出。由于一审法院作出了无罪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不应该也不适宜作出与判决相悖的逮捕决定。因此,再逮捕的决定权应该赋予第二审人民法院。
借鉴对于日本再逮捕要件的分析及结论,第二审中的再逮捕要件应当有更为严格的限制。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社会危害性条件。对于一审被判无罪的被告人,已经不再具备或者至少是在一定阶段不具备“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逮捕条件。只有在进入第二审实质审理阶段后,才会对逮捕条件的认识发生变化。因此,对于再逮捕的决定,应当在第二审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后,当法官形成了有罪的内心确信后,由二审人民法院作出。
随着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合法权益保护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以及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案件应有的增加,再逮捕的问题将会逐渐显现出来,也必将会受到司法实务部门及学者们更为广泛的关注。
注释:
①在该文中明确指出是“司法运用上”的基准,主张东电OL杀人案件的特别抗告审的决定实质上与此学说相近。
[参考文献]
[1]最決平成12•6•27[J].判例時報,2000(1718):19-21.
[2]最決昭和29•10•26[J].最高裁判所裁判集刑事,1954(99):507-508.
[3]团藤重光.新刑事訴訟法綱要(七訂版)[M]. 東京:創文社,1967:401.
[4]横井大三.新刑事訴訟法逐条解説Ⅲ[M].東京:司法研修所,1949:143.
[5]小川新二.第一審で無罪判決を受けた被告人を、検察官控訴後、実質審理開始前に、控訴裁判所が勾留することを適法とした最高裁決定[J].法律のひろば,2000(11):50-61.
[6]最決昭和41•10•19[J].判例タイムズ,1967(198):112-113.
[7]東京高決平成12•5•19[J].判例時報,2000(1718):24-25.
[8]青柳文雄.刑事訴訟法通論五訂版下巻[M]. 東京:立花書房,1976:468.
[9]小泉祐康.勾留状失効後再勾留した場合の勾留期間[J].判例タイムズ,1973(296):232-233.
[10]福崎伸一郎.第1審裁判所が犯罪の証明がないことを理由として無罪の判決を言い渡した場合と控訴審における勾留[J].ジュリスト,2001(1201):114-115.
[11]多田辰也.無罪判決に伴う勾留状失効後の被告人の再勾留[M]∥光藤景皎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巻. 東京: 成文堂,2001.
[12]村井敏邦.無罪推定原則の意義[M]∥光藤景皎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巻. 東京: 成文堂,2001,23.
[13]上口裕.第一審裁判所が犯罪の証明がないことを理由として無罪の判決を言い渡した場合の控訴審における勾留の適否——東電OL殺人事件[J].法学教室,2001(246):86-87.
[14]川崎英明.東電OL殺人事件無罪判決と勾留問題[J].季刊刑事弁護,2000(23):15-19.
[15]東京高決平成12•4•20[J].判例時報,2000(1718):22-23.
[16]岩田誠.刑訴345条による勾留状の失効と再勾留[J].法曹時報, 1955(3):329-340.
[17]伊藤栄樹ほか.注釈刑事訴訟法〔新版〕(五)[M]. 東京:立花書房,1998:514.
[18]肖萍.日本における刑事手続上の身体拘束と出入国管理法制の関係[J].一橋法学,2007(1):325-368.
[19]松田岳士.第一審裁判所が犯罪の証明のないことを理由として無罪を言い渡した場合と控訴審における勾留——東電OL殺人事件特別抗告審決定[J].阪大法学,2002(5):969-996.
(责任编辑 高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