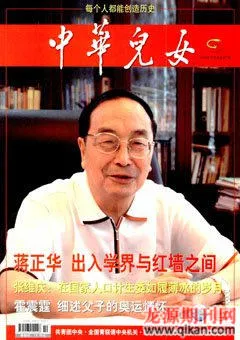我的风雨岁月
刘冰,原名姚发光,河南省伊川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共产党,曾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抗大六分校、太岳抗日根据地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豫西工作。解放后历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委常务书记、第八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从1964年至197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大学处于风口浪尖,刘冰作为清华大学的领导成员之一,亲历了这场铭心刻骨的风雨,而其中的众多内容系首次披露,如上书毛主席。本刊从2008年第10期开始,对刘冰新近再版的《风雨岁月》一书中的部分文章进行选载。
与迟、谢的斗争公开化
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总理的病情加重,听说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8月中旬,学校教改处的负责同志在市委听了邓小平同志8月3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回校向我作了汇报。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讲了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他说:“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听了汇报,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特别是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对学校工作,尤其对知识分子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我决定按市委规定,于当天下午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作了传达。我在会上强调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夜里迟群、谢静宜回到学校,他们安在党委办公室的“钉子”向他们报告了下午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邓小平同志8月3日讲话的事。第二天上午,谢静宜来到我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我和迟群都告诉过你,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向下传达时要经过我们,而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就传达呢?”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着:“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着传达?”这明显是无理取闹,以势压人。我压着怒火,先请她坐下,然后说:“邓小平同志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而且这个讲话是北京市委在专门会议上布置让传达到各单位党委的,你是市委书记,你应该遵守市委的纪律,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难道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副书记没有权力和义务进行传达吗?”在我强烈的反驳下,谢静宜语无伦次地喃喃地说:“不是说你不可以传达,而是说你应当先告诉我们一声。”我回敬说:“传达后再告诉你们也可以吧?你为什么对‘传达’这样恼火呢?难道就因为没有事先告诉你们吗?”我的尖锐反问使谢静宜无言以对,气呼呼地甩了甩头发,站起来扭头走了。
当天晚上,我向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位同志通报了上午我和谢静宜,当面锣、对面鼓干仗的情况。当时我们正在紧张地研究草拟向毛主席告发迟群的信稿,我和谢静宜的正面冲突自然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柳一安同志说:“你顶得好,就要她谢静宜知道,违反党的原则是不行的,刘冰这样的老同志是不好惹的。”吕方正同志说:“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咱们对谢静宜认识还不够。”惠宪钧同志说:“她是帮助迟群的。”柳一安说:“干脆这封信把谢静宜也挂上。”我说:“咱们还是按原先商定的,把她和迟群有所区别,集中反映迟群的问题。”最后我们商定还是维持原议,对两人有所区别。
策划给毛主席写信
关于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还得从头说起。写信的最早发起人是柳一安同志。当时,柳一安同志受上级指派,进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学部领导小组组长。他对于迟群政治上、思想上的恶劣品质和作风早就不满。从1973年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开始,迟群明显地投靠了江青,充当了江青的打手和急先锋,柳一安同志从社会上和干部中听到了不少对迟群的非议和责骂。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提出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整顿。对这些精神,迟群非常抵触,背道而驰。那时候,无论是学部还是清华大学的工作,都是在迟群的直接领导下,柳一安同志在迟群手下工作,要贯彻中央精神感到非常难办,思想上很苦闷。1975年6月之后,老柳患严重失眠症,经常在深夜吃了安眠药后仍然睡不着觉,就把在学部办公室工作的李兆汉(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的干部,后曾任中国教育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任彦申(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部干部,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找来,诉说心中的矛盾和苦闷,分析政治形势,议论对迟群的看法,商量采取何种对策。在日复一日长时间的议论中,逐渐地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迟群怎么看。觉得迟群人很聪明,但心术不正,政治上越来越“左”,是个野心家。迟群是站在江青一边,反对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
第二个问题是该怎么处理同迟群的关系。如果继续跟着迟群走,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如果跟迟群保持距离,进行决裂,要冒很大的风险,准备可能被打倒。但宁可选择后者,也不能跟着迟群干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采取何种行动。柳一安同志曾经提出要找迟群当面谈话,把社会上和党内对迟群的意见统统端给他,用压力加规劝的办法迫使迟群改弦更张。李兆汉同志认为老--柳的办法不可用,他说:“要看透迟群的本质,这个人心狠手毒,他如果知道你有二心,必然把你置于死地。迟群在清华大学一手遮天,称王称霸,单枪匹马地同他斗争,肯定不行。在清华领导班子内部,反对迟群的人是多数,但敢怒不敢言,没有上级领导的介入解决不了迟群的问题,唯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他认为,要在中央直接过问下,才能解决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反映迟群的问题。当时清华大学是毛主席抓的点,是“斗、批、改”的样板。向中央写信要避开“方向”、“路线”问题,以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线索,集中反映迟群有野心、骄横、搞阴谋诡计、破坏民主集中制和党的优良传统等个人品质和作风上的问题。
就这样,1975年7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告发迟群问题的构思形成了。对此,李兆汉、任彦申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随后,柳一安找惠宪钧、吕方正同志商议,意见完全一致,并决定联合上书。
这三位同志意见如此一致,断然作出这一抉择,决非偶然。除了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解放军,长期受到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教育影响这些基本方面的原因外,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三位对于迟群专横跋扈、阴一套阳一套、背离党的原则的恶劣品质早已不满。
7月下旬,北京市委在全国政协礼堂召集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会间休息时,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位同志把我拉到休息厅一旁的座椅上,告诉我他们三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要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迟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反映,我们就要犯错误,也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共产党员的称号。因为我是位老同志,信得过,因此把他们的决定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然早就考虑同迟群、谢静宜要进行斗争,但一直没想好斗争的方法,此时三位宣传队的负责人“杀”了出来,真是太好了,“正合吾意”。我当即下定决心要与江青在清华的哼哈二将公开较量,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他们三位的主张,并自告奋勇,由我来牵头。
政协礼堂的干部会后,当天晚上在惠宪钧同志的办公室,柳一安、吕方正我们四人,就给毛主席写信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的宗旨是:一定要实事求是,给主席反映问题决不能有丝毫粗心或不实。
信稿审定之后,决定由惠宪钧把稿子交给军代表安恩奎同志,嘱咐他尽快复写几份,争取尽早发出。鉴于过去寄给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的教训,我们又议论了如何保证信能让主席看到的方法。经过研究,认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为那样容易落人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之手,信应经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呈主席,只要小平同志能在我们的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江青、毛远新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主席的批件。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定会转送主席的。接着又研究信如何能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想到了胡耀邦同志。
1953年到1956年,我曾在团中央负责办公厅的工作,那时耀邦同志是第一书记,我经常同他接触,深知他为人耿直,乐于帮助同志,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志,与小平同志来往较多。
曲折投书,胡耀邦助一臂之力
信复写了几份。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给耀邦家里打电话,他夫人李昭同志告诉我耀邦不在家,到科学院上班去了。我告诉她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看什么时候合适。李昭和耀邦一样是个爽快人,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4点钟到家里来好了。”第二天,我准时去了,耀邦、李昭和子女都不在,只有一位老保姆看家。老太太在他们家好多年了,我来过几次都看到过她。老人家热情地接待了我,说:“耀邦上班去了,你到房里休息。”她一边说一边领我穿过院子来到过厅旁边的书房里,给我倒了满满的一杯茶水。我向她表示感谢,问:“今天是星期天,耀邦还上班呀?”她说:“耀邦、李昭星期天都上班,耀邦中午也不回来,带个饭盒,午餐时让人给热热就吃。他呀!对自己严格啊!”老太太离开后,我靠在沙发上,陷入了往事的回忆:1964年我来看耀邦,那时他兼任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因为他对农村“四清”一些“左”的东西有看法,受到批评、责难和排斥,回京呆在家里。但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我说:“对基层干部要有正确的估计,在我们党领导下,大多数基层组织,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遍地是虱子,到处有问题,我们党在农村取得的伟大成绩怎么解释?!我历来主张对人对事要公道,要实事求是。”1974年我来看耀邦,“文化大革命”中批了他好几年,那时还未分配工作,又是待在家里。见到我,他说:“我没事就看书,想问题。王明路线是1931年到1934年共四年,林彪从‘五一八’(1966年5月18日讲话)到‘九一三’(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是五年多一点,这两次都使我们党受到大损失,尤其是在干部问题上,这次受到的损失比王明路线还严重。这是教训啊!”耀邦同志的深刻分析,至今言犹在耳。就是这次谈话,他说到了迟群、谢静宜,想来他不会料到,今天我来找他就是为了这两个人的事。我看到他书桌上放着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走过去翻了一下,看到书中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论述用红铅笔画了圈圈杠杠,很显然,他是在研究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问题。联想到1974年我来看他时,他正在读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也是在书中画了许多圈圈、点点、杠杠。那次他从这本书说到王明和林彪,说到他没事就看书、想问题。现在他有事干了,更是要看书想问题了,这是耀邦的习惯,也是他的性格。
“啊!刘冰来了!”是耀邦亲切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我说:“4点钟我就来了,你星期天还上班?”耀邦说:“有事就上班嘛!你有什么事?”我说:“有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然后我把这两人的问题概略地讲了一下,说明我们写给主席的信想请他帮助送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耀邦从茶几上拿了一支烟,边找火柴边说:“记得去年我给你说过这两个人,刚才你讲的他们那些事是必然的,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的干部队伍中不是个别的。”他吸了口烟,接着问:“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我一边回答“带来了”,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信稿说:“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给了他。他戴上老花眼镜,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后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我说:“耀邦同志,你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要用事实说话。”“你们信中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是形容词,是空话嘛!”耀邦回答说。我解释说:“这不是形容词,他当时的具体情形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才能描述他的真实情况。”他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他接着说:“我支持你,能帮助就帮你。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和咱们在团中央时不一样,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我说:“小平同志不认识我,那怎么行呢?”他说:“你与南翔在清华,名字他会知道的。”我说:“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给捉起来,那才不好呢!”耀邦笑了:“这样吧,你从邮局给寄去,行吗?”他问我。我说:“那样不牢靠,我怕丢了。”他说:“这样吧,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耀邦告诉了我王瑞林秘书的电话号码。我当即拨通了电话,正好是王秘书接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单位、职务、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听出,王秘书很客气,他说:“你的信可送国务院。”我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他说:“你从邮局寄也行。”我说:“我怕信件遗失。”他说:“那不会的,你寄好了。”在电话上我不好意思和王秘书再讲下去了,我对他表示感谢,把电话挂了。打电话时,耀邦亲切地站在电话机旁边,这时他问:“王秘书最后怎么说?”我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那你就寄嘛!”耀邦恳切地说。“不能寄,我不放心。”我回答说。他说:“我看你直接送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住在X街XX号,门前面是个小胡同。你大胆些,怕什么。”耀邦同志该做的都做了,对于他的真诚相助,我打心眼里感激。已是6点多钟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便说:“耀邦同志,我就按你说的办吧!谢谢你。”和他握手告辞了。
出了大门,坐到车上,我改变了主意,觉得贸然到小平同志家里太冒失了,先回学校再说。我告诉司机回学校。在返回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到底怎么办?忽然想到通过警卫部队是个办法。负责警卫小平同志住宅的是什么部队?八三四一还是卫戍部队?不管是哪个部队,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复思索着。车子到了家门口,停了下来,我还坐在车上,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经司机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回到家里,我给惠宪钧打电话,要他们三人晚8点在办公室等我。在老惠办公室,我把见到耀邦和给王秘书打电话的情况作了通报,并讲了我在车上考虑的送信办法。听后,他们三人对耀邦同志的支持感到鼓舞,并表示赞成我提出的通过警卫部队送信的办法。惠宪钧说:“我给参谋长打电话问问是不是我们师负责警卫。如果是就好办了。”接着老惠给马清沅副参谋长拨了电话,当参谋长得知是送信的事,他热情地告诉老惠,是他们师负责警卫。然后,他告诉司令部值班室,把惠宪钧去送信的事通知驻地警卫部队。为了更落实,他又亲自给那里的警卫部队负责人打电话。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副参谋长电话告知惠宪钧,要他第二天上午9点准时赶到,要穿军服,军风纪要严整,下车后告诉警卫人员自己是师部的,在清华支左,来这里送信,警卫员会接待他的。按照副参谋长的嘱咐,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齐,格外精神,驱车从清华园出发,准时赶到邓副主席住宅门前。老惠下车后,警卫人员礼貌地问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长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副参谋长昨晚打过电话。老惠对排长同志的支持表示感谢,把信交给了他。排长请老惠休息,他进院里送信去了。过了不久,他满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对老惠说,因王秘书正在忙,让他转告清华的同志,信收到了,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把信交给他。老惠说,这时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邓副主席今天就能看到我们的信,真是高兴得没说的了。他再一次感谢排长和警卫同志后告辞了。对老惠的送信之行,我们三人和他一样,“高兴得没说的了”。
焦急盼望主席的回信
紧接着,我们研究了信送走后的工作。我们认为,虽然已与迟、谢公开较量了,但不能大意,要谨慎,在未得到毛主席对信的指示之前,从组织原则上不能给他们留有空隙,对这两人即使表面团结也要注意。同时还要注意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含糊,学校工作今后主要靠我们来做,一定要按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精神抓工作。现在开始准备,一个星期后去向市委报告这两人的问题。到市委一个“台阶”也不隔过,要按组织顺序,先向科教组负责人口头汇报,然后把给吴德同志的信交给科教组转呈,并请科教组负责人转告黄作珍(分管高校的书记)、吴德,我们随时听候召见,争取向他们口头汇报。一切研究妥当之后,真是如释重负,美美地睡了两晚上好觉。我们精神上的愉快,尤其在于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认为主席马上要看到我们的信了,主席定会惩恶除弊,定会使我们大喜过望。
信送出已经一个星期了,按原定计划该去北京市委了,但主席是否看到了信呢?如果还未看到,去市委是否有点早呢?还是慎重为好,在时间上要有足够的保险系数,做到十拿九稳,等主席看到信后,再走第二步。这样就往后推延了两天,第九天我和惠宪钧去了市委。那天下午2点半,市委科教组组长肖英和军代表接待了我们。因为迟群、谢静宜一向就不尊重市委科教组,在工作上常给他们出难题,相互之间有着较深的隔阂和矛盾,所以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时,显露出格外高兴的面容。肖英同志说:“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对迟群的传说,那是从别的学校传来的,好像大家对这个人都有意见。”军代表说:“我去看看丁国钰同志是否在办公室,请他也听一下汇报。”我们表示非常赞成,常务书记丁国钰也能来听听,那是最好不过的。但他使我们失望了。军代表回来说:“老丁在办公室,他说工作忙,不听了,让我们听汇报时作下记录。”这位丁书记是真的那么忙吗?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推脱的遁词罢了。在那个年代,一些干部用这种办法回避矛盾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我们也就不介意了。在肖英同志主持下,汇报了两个小时,我们主要讲了信中写的那些问题,所不同的是,口头讲的比文字更详细。汇报完了之后,肖英表示,要把记录整理一下,向市委作汇报,有什么意见和指示,他一定及时转告我们。我们当然对肖英和军代表耐心听取我们的汇报表示感谢。因为这件事对清华来说关系重大,因此我又作了如下的说明:第一,反映清华领导班子中的问题,我们是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先给科教组汇报,并请你们也向市委汇报,肖英同志刚才说的,正是我们所希望的;第二,因为关系重大,除口头汇报外,我们还给吴德同志写了信,请你们二位务必把信转给他;第三,黄作珍同志是分管高等学校工作的书记,请你们二位将我们的汇报也报告给他;第四,我们要求吴德同志接见我们,随叫随到,我们静候通知,如果他没空,委托黄作珍同志也行;第五,请肖英同志和军代表给我们保密。肖英对我说的几点,表示凡属科教组的,他们都可办到,至于吴德接见的事,他们只能转告。
回到学校,我们除了负担着紧张的日常工作,天天都在盼望毛主席老人家那里的信息,盼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接见。我们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焦急地等啊,盼啊!日复一日,但没有任何消息。我想,毛主席已是耄耋之年,日理万机,对于我们的信,可能不会马上处理,我们要耐心等待。可吴德同志尚在壮年,最多60岁,又是我们的直接领导,难道他会对直接领导下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负责人反映的重大问题漠不关心、不予理睬吗?如果那样还谈得上有群众观点吗?还像一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吗?经过思考,我否定了无根据的猜想,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吴德同志的接见,但一直没有音信。
(未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