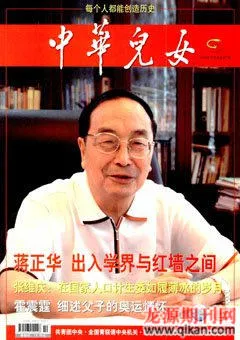胡松华长歌人的书画情缘
提起胡松华,嘹亮的《赞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吉祥酒歌》等耳熟能详的歌曲会立即响彻人们耳边。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歌唱家,胡松华当年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把酒放歌的磅礴大气与真情实感让几代人难忘,如今已是77岁的胡松华,歌声却更胜当年。而且,他还常回归空气清新、民风淳厚的边疆大自然中,云走四方。并大家展示着他生活中的另一面——书法与绘画多彩内功的长东世界。
奔腾的骏马、振翅的雄鹰;高原上质朴的康巴汉子、昆仑岩石中抖着龙鳞的古松……胡松华的书画与他的歌一样,在劲道的笔法中透出对生命的感悟、感恩和求索。然而,少有人知的是,胡松华的书画,先于声乐。多年来,书画滋养了他的歌声,歌唱也赋予书画以音韵的灵性。
书、画、歌,三者在胡松华的生活中归于同源。
自幼习书画,悟得“入境”法
书画家兼中医的父亲,令胡松华自幼苦读了四年私塾,然后才上的洋学,与此同时,大父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熏陶中,胡松华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练字习画,这是他从小的功课。胡松华不断地对绘画产生着兴趣。此间,父亲特许他课余读古文体《聊斋》,而每读一篇,他便会凭着想象将里面的人物画在小片纸上。时间久了,笔下的人物也有了不同的性格和姿态,“不千人一面”,是严父对胡松华的最高褒奖,这也让父亲感到胡松华作为长子,确为可塑之才,于是对他书画的教育更加严格有序。并安排胡松华先后师从赵梦珠、徐凯、金毓远三位中、西画师,字承颜柳诸体,在十三年中打下了扎实的书画基本功。
父亲常带他到孔庙、太庙等处观察古松翠柏的高洁风骨,并随父辈们体会到远郊驾鹰行猎的生动气氛,回家默画兔滚鹰翻等片段,这叫做忆画之功。当年北京德胜门外马甸,是个马市,蒙古族和回族的卖马人、驯马师齐聚于此。胡松华时常跟着父亲来这里,一边观赏驯马,一边将各种场景绘于纸上。画册虽然是用父亲废弃的宣纸边做的,但是胡松华仍旧聚精会神、乐在其中。就这样,胡松华练就了写生的本领,同时不断领悟着父亲“沉气、凝神、入境”的六字书画基本要诀。这六字箴言,让他在日后从事声乐事业时,有了一种入境而忘我的追求境界。鹰、马,两种草原民族崇敬的神圣之物,也成了胡松华一生的喜爱。
建国前拿着画笔参加革命队伍的胡松华,按当时形势的需要,经历了登台演出秧歌剧、话剧等的洗礼,建国之初又投入了边疆多民族歌舞艺术七彩情炉的熔炼。1952年后才开始了他长达六十年的正规歌唱生涯。其实,熟悉他的人才了解,先于歌唱多年的书画,才早是他第一的真正“本行”。
长歌万里画千幅,更得师友情意长
1987年,胡松华应《人民日报》之邀撰文《书画歌同源之我见》,论述了自己“苦练书画养歌气,勤使歌声润书画”的感悟。这种感悟,绝非闭门造车的冥想,而是胡松华在长期实践与体验中的真实感觉。
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组建了中央民族访问团。胡松华随团来到云南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进行“四同”式的生活工作。在这里,胡松华接融到了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他不但向民间艺人学习歌舞技艺,也将自己的情感容于书画中,两相呼应,更加深了他与各民族兄弟的感情。在丽江,中访团看过边疆纵队多民族骑射表演汇报后,胡松华与另外一位画家为滇西北游击骑兵大队长苏那尼玛画像,身穿藏袍、解放军裤、腰挎银饰子弹袋、胸佩护身符的藏族骑兵队长煞是威武,为了让他在“当模特”时不寂寞,胡松华一边请他教自己唱山歌,一边为他画像。在对歌声中,苏那尼玛不但不觉枯燥,反而更显神采奕奕,而胡松华也一举两得。因画相识,以歌相知,两个人自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从苏那尼玛那里,胡松华学会了很多地区的山歌唱法,受益匪浅。而且由于苏那尼玛的唱腔广纳多地精华而典型化,故唱到各地都受到藏胞欢迎。
多年后,两人仍保持着密切的往来。1996年,胡松华《长歌万里情》摄制组再次来到香格里拉,两人都年过花甲。再相见,不禁感慨万千。胡松华特为此赋诗“长歌夙愿万里情,高原雪域几驻行。斑鬓相拥多感慨,酒歌声中泪纵横。”他另一位良师益友是蒙古族歌圣哈洽布。胡松华与哈老并骑放牧,多年学习“长调”绝艺,把孕大含深的草原魂歌长吟至今多年来,胡松华书画技艺在长期深入边疆的多彩生活融汇妙用,与他溶中西于一炉的宽广歌风互为吸收、努尔哈赤起事奋进的白山黑水,在游侠阿凡提出没的天山丝路……放歌中西妙曲,纵笔古今墨情。他在多元文化的马鞍上,长乐无极地跋涉着,并深化感悟着老父亲和关山月等前辈提出的:一支毛笔能画出乾坤万象的真谛。
很多少数民族群众都亲切地喊胡松华为“我们自己的歌唱家”,而他的下笔也因这些跋涉长途的所见所感而更加生动、大气。胡松华一生爱马,唱马又画马,他画的马正是得益于他的纵览博知而兼具蒙古马的膘实悍壮、伊犁马的长耳秀腿和青藏马的狮鬃长尾,彰显开疆扩土的大气概。
1964年,胡松华以歌唱家的身份成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直至第九届。在长达三十年间,他为国家大政建言献策,也和同为政协委员的启功、叶浅予、蒋兆和、关山月等书画界前辈大师们建立了师友关系,深受前辈关爱,点化习染之益。1980年,胡松华与夫人、舞蹈家张曼茹举办“胡松华张曼茹独唱独舞晚会”之际,著名画家李苦禅特贺画《并蒂花开》。胡松华五十岁生日时,从不送人以画的蒋兆和与叶浅予二先生同时寄赠画作。
1982年,胡松华经黄苗子、刘炳森介绍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并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活动。多年来,胡松华书画技艺随长期深入边疆的多彩生活而融汇妙用,在师友的点染与自身的中探索,一直以“歌唱乃有声之书画,书画为有形之歌声”为理念而追求。
三艺本同源,共练一口气
胡松华北京的寓所书房名为“养气斋”。这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亲笔。“养气”二字,正道出胡松华多年来保持良好综合状态的内功“秘诀”。2007年,淡出小舞台、拥抱大天地多年的胡松华应邀参加了北京新春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时隔43年,于同一舞台上,用76岁的歌喉再唱《赞歌》——隽永的长调、高亢的主歌,胡松华更胜当年。
平时,胡松华常在长歌之后提笔书写,此时歌喉暂息而沉气未断,则运笔益发神清气爽;写过一会儿再唱,更感歌喉爽利,气足声壮。他认为,书画与歌唱同源同宗,互为渗透,歌唱中的力度强弱、音色明晦、节奏顿挫、色彩对比、速度张弛等等诸多变化,都与书画有着共同的审美情趣。而书画中的间架构图、布局,落笔的虚实、粗细、曲直,着色的浓淡等都有对比变化,这种辩证法则,书画需要,歌曲同样需要。从沉气技法讲,共同修炼一口气,只不过一行于笔端,一行于歌喉;一行于青案之上,一行于音乐厅堂,于是他的歌声宏亮中富圆润、豪放中蕴深情,且常唱长新,他的理论的先进、鲜活,他的书画诗词文赋所表现的意境,承载的力度都将以一个历史性的高度耸立在九州文化之林。
1992年,年逾花甲的胡松华与夫人开始了一次令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界震惊的“自我挑战”,他报请国家、自筹资金,自组摄制组,着手拍摄多民族音乐电视艺术专题片《长歌万里情》,用唱十万里歌,谢十万里情的跋涉,报恩予各民族母亲的哺育之情。片中重新精录了近百余首多民族优秀歌曲,其中85%是他多年的心血之作。历时三年,行程14.2万里,胡松华完成了这次可载入史册的“壮举加创举”。而拍摄过程中,他又有多幅诗、书、画作品问世。
近年来,胡松华在社会活动之余,更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更为广泛的层面。1999年以来,他曾参加全国政协抗洪义唱义书大型晚会与多次类似活动;今年5·12汶川地震之后,他又挥毫创作书画作品,多次参加义唱、义书、义画活动,捐助灾区,并在人民日报、中国艺术报、北京日报等报刊用书画的心血之作为中国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致贺、助威、加油。
同时,他总结自己多年的声乐经验,重到边疆将多位贫困少数民族青少年带到自己的艺术研究室,进行“一条龙”地免费培训,同样取得了感人泪下的成绩。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盛赞胡松华“把几十年‘广学古今中外法,扎根边疆保元真’的学术思想,艺术观点乃至独特的技法都精心传授给各民族的后继人才。”
时至今日,胡松华仍可在演唱一曲蒙古族长调《圆蹄子紫骝马》的时长内,令两匹野性十足的骏马跃然纸上。他还习惯于随身携带几本格纹式的线装宣纸簿,不论远行何处,都强令自己将所见所感凝炼成诗,用毛笔写在簿上,以练脑、练心、练腕、练气、更寄情思和怀愫于大爱之中。这已成为胡松华常保艺术青春的“独门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