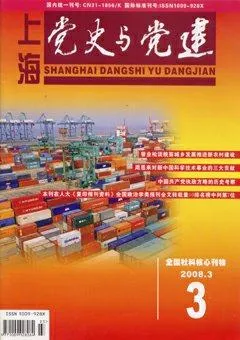卢新华:直面“伤痕”的心灵直白
口述:卢新华
采访、整理:汪建强
采访时间:2008年1月8
卢新华,1954年生于江苏如皋。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8月11日在《文汇报》发表小说《伤痕》一举成名。大学毕业后任职于上海《文汇报》,不久下海经商,被称为“中国文人下海第一人”。1986年自费赴美国加州大学读书,获文学硕士。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紫禁女》。在美期间,干过多种职业,现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往返于中美两地。
1、学校墙报上张贴了我写的小说
1978年4月的一天,我起床后拿了洗漱用具正要去盥洗间洗漱,忽然发现我们所居住的学生宿舍4号楼底层的拐角处人头攒动,男男女女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地拥挤着,争睹新贴出的墙报左上方头条位置的一篇小说,他们中有些人尤其是女生甚至还泪流满面。我忍不住好奇地探过头去,方知道大家看的原来是我入学不久后新写下的一篇习作——《伤痕》。
看到自己的创作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并引起了这样热烈的反响,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惶惑。因为就在作品刚刚完成后,我曾经满怀信心地请一位本系教写作课的老师帮我提意见并推荐投稿,谁知老师给我的评语却是:“小说虽然写得挺细腻,也很感人,但根据我曾经在编辑部帮着看稿的经验,你的小说也存在着不少的理论问题,肯定发不出来的。我倒建议你多读一些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论文艺的著作……”。我于是听从老师的嘱咐,马上去系资料室借书,并很认真地加以阅读。然而读后,我对这篇小说却越来越失去信心,最后终于将它锁进了抽屉。
《伤痕》叙述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文革”时期,一个叫做王晓华的女中学生,在母亲被张春桥一伙定性为叛徒后,为表白自己要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于是大义灭亲,毅然与母亲决裂,还未毕业便主动申请到临近渤海湾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然而,在她坚忍不拔地努力改造自己和世界的过程中,尽管作了十二万分的努力,仍然无法摆脱“叛徒母亲”带给她的“政治阴影”。磕磕绊绊的入团经历,曾经向往终于又不敢期待的爱情,让她原本一颗火热的心变得越来越灰冷,红润的脸庞也渐渐地失去了血色。
8年后,单位的一纸公函告诉她,所谓母亲的“叛徒问题”其实是一起冤假错案,她这才满怀惶恐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探望母亲的归途。未料母亲身心俱遭摧残,沉疴难医,竟未能看上女儿一眼,便撒手尘寰。
故事是以悲剧的形式结束的。当王晓华看着母亲写下的日记,读到“虽然孩子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要深得多”时,心灵受到无比强烈的震撼。
为什么想到写《伤痕》?起因是入学不久,有一次上作品分析课,老师讲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提到许寿裳先生曾评论说:“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段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和启发。那时,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我们的报刊杂志讲得最多的便是说“四人帮”将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我则忽然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贯穿始终的那条极“左”路线,给我们的社会造成的最深重的破坏,其实主要是给每个人的精神和心灵都留下了难以抚慰的伤痕。由此,下课后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有关《伤痕》的故事和人物便开始躁动于我的腹中。
2、小说被《文汇报》看中
《伤痕》最初的名字叫《心伤》,我曾经起过两个头,因为不甚满意,就没有再写下去。后来我是在未婚妻家的阁楼上,趴在一部缝纫机上,从晚上六时许写到零晨两点,最终以泪洗面,一气呵成的。
为什么会把王晓华插队的地点写在靠海边的村庄?这是因为我父亲是军队干部,我们全家曾经作为随军家属在山东长岛一带生活过好些年,我对渤海湾,对海边的生活比较熟悉和了解,写起来人物和场景会感觉着比较得心应手。
小说完稿后,我一遍遍读过去,心里很满意,甚至还有些自负,以为至少会是写作课上的一篇范文。未料不仅写作课老师的评语不佳,几个看过的同学的反映也不很热烈。这样,我连将这篇小说展示给别人看的勇气也渐渐丧失了。
然而,在一个即将熄灯就寝的晚上,沉静、稳重的小说组组长,班级墙报主编倪镳同学轻轻地敲开我们宿舍的门,对我说:“嗨,过两天要出墙报了,你小说写好没有?得交了。”我因为信心尽失,最初并没有想到拿《伤痕》去交差,而是想重写一篇,后来因为时间太紧,实在来不及,才迫不得已用《伤痕》去滥竽充数。我最近在国内见到已经成为“国际友人”的倪镳同学,说起往事,他告诉我,他在拿到我的稿子后,曾仔细阅读过,觉得挺好,于是又给另外几个同学看了,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两个同学持肯定态度,另一个同学则有比较多的批评意见。然而,他还是决定将它安排在最醒目的左上方头条位置。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倪镳同学的慧眼独到,或者小说被处理在墙报上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所有有关《伤痕》的故事可能都将无从叙述了。
由此,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也悄然改变了。那以后,复旦大学学生宿舍4号楼底层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墙报俨然成了复旦大学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每天聚满了阅读的人群,先是中文系的,继而又扩展到外系……后来通过中文系新留校的女老师孙小琪以及她的女友俞自由的渠道,敏感的《文汇报》编辑部编辑钟锡知先生了解到了《伤痕》在复旦校园引起轰动的情况,旋即托孙小琪老师要去了我的一份手稿。
我后来才知道,稿子到了《文汇报》后,为慎重起见,报社马上打出了小样在上海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当时,整个社会都处在剧烈的新旧变革时期,一方面,“两个凡是”的禁锢还在,另一方面,初步解冻后的思想界已日显活跃。终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了,这不仅给思想界,也给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带来了一股春风。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本来就倾向发表《伤痕》的《文汇报》编辑部更加受到鼓舞,于是,1978年8月11日,《伤痕》终于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在《文汇报》发表……
3、小说发表后带来的轰动
真可以称之谓“一石击起千层浪”,小说发表后,一下子“洛阳纸贵”,我的同学刘开平和我一起骑着自行车去大学附近的邮局买报,结果处处被一抢而空,只能失望而归。发表的第二天,我们班的信箱里就塞满了各界寄给我的读者来信。据不完全统计,《伤痕》发表后,报社和我共收到近三千封读者来信。这些信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小说和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故写信对作品和作者表示支持的。很快,文艺界也随之兴起一股类似的创作思潮,后被中外评论家们广泛地称之为“伤痕文学”或“伤痕流派”……
值得一提的是,《伤痕》发表前,责任编辑钟锡知先生曾代表《文汇报》编辑部和我谈过一些比较重要的修改意见。依稀记得,意见大约有16条。重点的是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故后来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又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亦遵嘱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着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又有了我笔下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的光明结尾。现在看来,这些修改意见尽管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思维的某种局限,却也真实地反映出《文汇报》同仁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来发表《伤痕》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极其细致和负责的精神。
《伤痕》发表后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文革”后中国作家协会所吸收的第一批年轻会员之一,后来又被推荐和选举为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常委,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这些纷至沓来的荣誉,曾令我陶醉,继而则引起我的警觉。为了更坚实地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抱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我后来决定放下所谓的“作家”的身段,从一个普通人重新做起,先是辞职下海经商,继则出国留学。这期间,我陆续收获了《森林之梦》《细节》和《紫禁女》三部长篇小说。而今,我正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往返于中美两地。因为血管里涌动着的毕竟是中国人的热血,所以,我更关注的还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并期望能用自己的笔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尽一点绵薄之力。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