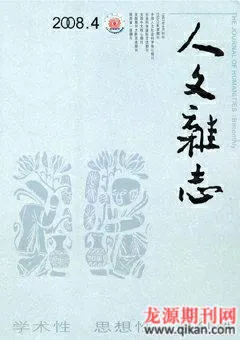困境中的坚守与奋进
内容提要 本文从反思当代陕西文坛长期缺乏对诗歌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为切入点,全面梳理与反思陕西诗歌30年的发展历程,指认陕西当代诗歌的总体成就,无论是不断涌现的有影响力的代表诗人,还是总体创作的质与量,以及在现代诗学方面的贡献,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方重镇,其真实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影响,无论在本省还是在国内海外,都并不逊色于陕西的小说与散文。进而指出步入新世纪的陕西文学界与陕西文化界,应该尽快结束陕西诗歌多年失于呵护、流离困顿的尴尬局面,从而使陕西文学整体性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新时期,让历史的遗憾不再复生为遗憾的历史。
关键词 陕西当代文学 诗歌发展 “三大走向” “四大板块” 梳理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4-0116-03
一
诗是文学中的文学,是作为语言艺术的各类文学体式中最为重要而精粹的艺术。从古到今,我们中华民族都一直以辉煌的诗歌传统为荣耀、为自豪。改变并造就了现代中国人新的思想、新的精神、新的审美情趣的百年中国新文学,也是经由新诗的率先开启和不断推动而发展壮大的。正是新诗的破晓之声,为我们民族的精神空间,撞开了新的天地,继而成为百年中国人,从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尤其是年轻生命之最为真实、自由而活跃的呼吸和言说。尤其在被当代思想史称之为“二次启蒙”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新诗潮所迸发的新的美学思潮,几乎成为开启和推动包括文学、美术、电影等所有艺术形式在内之复苏与新生的原驱动力和不断发展的坐标与方向。在当代文学史及美学史的书写中,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然而,作为号称“文学大省”的陕西当代文学,却一直疏于对诗歌的重视与关注。在陕西文坛,诗歌的发展之艰难、生存之困窘及所处地位之低下,早已与“文学大省”的名分极不相称,从而造成难以弥补的种种遗憾。
从表面现象看,造成这种遗憾的原由,似乎来自当代陕西文坛在小说和散文方面的重要成就之巨大影响,掩盖了陕西当代诗歌的实际成就。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从创作到理论,从体制内到体制外,陕西文学及文化界长期缺乏对诗歌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而一再疏于正视、梳理与宣传所致。同时,反映在陕西小说和散文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如文体意识的薄弱、美学趣味的偏狭、语言品质的陈旧及诗性生命意识的欠缺等,也正是由于这一整体文学观的偏失所造成。
说来陕西几代著名作家中,不少都是与诗结缘而成就了后来的文学事业的:六十年代的魏钢焰,八十年代的路遥、杨争光、高建群,最早皆以诗人身份名世;贾平凹出过诗集且反响不小;成为跨世纪亮点的新锐青年小说家红柯,也是以诗歌创作为起点,并在后来的小说写作中,因有机地融合了诗的意识诗的品质而风格独具奇峰突起的。有意味的是,作为个人,几代作家能如此敬重诗歌心仪诗歌,但作为整个陕西文学界(包括出版界及各种媒体),却一直难以善待诗歌更别说厚待诗歌,其内在的诸种原由,确实耐人寻味!而这已是将近半个世纪的缺憾,现在,是到了该为之反思和校正的时候了。
二
仅以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降、被称之为“新时期文学”以来的陕西诗歌进程来看,其实并无愧于“文学大省”的称号——
由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陕西有伊沙、李汉荣两位青年诗人入选,占新时期青年诗人入选额的百分之八;
由台湾张默、萧萧主编的《新诗三百首》,被两岸专家学者誉为“跨海跨代,世纪之选”,陕西有沈奇、小宛、李汉荣、赵琼、李岩、仝晓峰、南嫫七位中青年诗人入选,且占到全书百年入选诗人的百分之四;
其他海内外多年来各种各类重要诗选,也从来没有少过陕西诗人的份额,且见诸于英、德、法、日、瑞典、拉脱维亚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的译介,并先后有伊沙、沈奇应邀出席瑞典、日本、拉脱维亚等在国际上有名的世界诗人大会,为陕西诗歌走向世界扩展了影响;
素有新时期中国诗歌“黄埔军校”之称的诗刊社“青春诗会”,陕西先后有近十位青年诗人入选参加,比例也不小;
另外,新老几代陕西诗人,在生存条件十分艰难的境况下,出版个人诗集也不下千种。
可以说,除北京、上海、四川、广东之外,陕西当代诗歌的总体成就,在全国算是名列前茅的一大板块,无论是不断涌现的有影响力的代表诗人,还是总体创作的质与量,以及在现代诗学方面的贡献,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方重镇,其真实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影响,无论在本省还是在国内海外,都并不逊色于陕西的小说与散文。只不过这种影响,因为其特殊的进程和受文化转型的冲击,更多呈现为一种潜在的、离散的、边缘化与体制外的状态,很难为与主流为伍、与时尚共进的人们所认领而已。
三
综观三十年陕西当代诗歌进程,大致可以“三大走向”、“四大板块”概括之:
“三大走向”中,其一为延承“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之诗歌观念的余绪,以官方诗坛和体制内写作为寄生的创作走向,其创作队伍与作品在不同时期都颇为繁盛,但因其所依循的诗歌意识比较陈旧,同时受狭隘的时代精神所限,也便随时代的急速变化而事过境迁。这一流向可称之为“主流诗潮”,发挥一时代之影响,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但缺乏真正有分量的诗学价值,并逐渐由主流而边缘乃至无效。
这一走向的前期阶段,以玉杲、田琦、毛琦、雷抒雁、闻频、晓雷、党永庵、马林帆、王德芳、谷溪等为代表,后期阶段以子页、刁永泉、商子秦、朱文杰等为代表。其作品影响大体局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渐次淡出诗歌界,难以为继。
其二为秉承朦胧诗以降的“现代主义新诗潮”之诗歌观念,以民间诗坛和体制外写作为旨归的创作走向,其创作队伍多离散性地分布在大学、城市和青年诗人群体中,以纯粹的艺术追求和诗性生命体验为准则,与横贯整个新时期及跨世纪的先锋诗歌相为伍,潜沉精进,默默崛起,其不凡的成就,既具有文学史意义,又有诗学价值的贡献。
尤其重要的是,正是这一走向的艰难拓展,才使得陕西当代诗歌彻底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地域文化视阀的双重挤压与困扰,以不可阻遏的探索精神,和充满现代意识与现代诗美追求的诗歌品质,融入百年新诗最为壮观的现代主义新诗潮,进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这一流向的前期阶段,以胡宽、韩东、丁当、杨争光、沈奇、杜爱民、岛子、赵琼等为代表,后期阶段以伊沙、秦巴子、李岩、南嫫、朱剑等为代表。其作品影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横贯八、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近年渐由边缘而主流,成为陕西当代诗歌发展之本质力量的真正代表。
其三为可称之“中间道路”的另一大走向,其代表人物有沙陵、关雎、渭水、李汉荣、耿翔、王宜振、孙谦、吕刚、刘文阁、阎安、远村、尚飞鹏、刘亚丽、杨莹等老中青三代诗人。
这一走向的诗歌立场和美学趣味不尽统一,大体在体制与非体制、传统与现代、“常态写作”与“先锋写作”之间游离摆荡,或后浪漫,或新古典,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守“常”求“变”,孜孜以求,并保持了各自不同的精神特质。其作品影响,有不少远及省外与海外,但总体上还局限于本省,有待新的突破。
不过,也正是这一走向的纷纭辈出,成为当代陕西诗歌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与平台,虽常因缺少新锐的诗美追求而稍显滞后,但其写作目的的纯正和诗歌理想的高远,有效地保证了其持续发展的精神资源与创造动力。
以上三大走向,形成当代陕西诗歌的三大主体性板块,代表着近三十年陕西诗歌发展历程的基本样态。另外一大板块,即从陕西高校之大学校园诗歌起步,而成名于其他诗歌版图的一茬又一茬的青年诗人,他们是有效推动陕西诗歌发展的另一潜在源流,虽变动不居而生生不息,以其青春色彩与纯粹心态,不断提供新鲜的活力和勃勃的生机。这一板块的代表诗人有马永波、杨于军、夜林、方兴东、谭克修、蔡劲松、陶醉等,有的已成名家,并反馈性地影响到陕西校园诗歌乃至整体诗歌运动的更新发展。
进入新世纪,陕西诗歌界更是异彩纷呈、成就斐然:除上述其二、其三两大走向,依旧保持着坚卓精进的态势,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与影响外,更有一批新锐青年诗人活跃于陕西民间诗坛,如之道、黄海、三色堇、周公度、武靖东、王琪等,并于2006年底,结集出版了展示新世纪陕西诗歌尤其是活跃于基层的青年诗歌创作状态的第一部大型诗选《长安大歌》(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影响盛大;从陕南安康走出来的年轻女诗人李小洛,以其丰瞻而别具一格的创作实绩,荣获由《诗刊》社等单位主办的全国“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评选大奖,并受邀成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年仅十二岁的西安小诗人高璨,天赋异秉,以其敏慧的语感和超常的想象力,以及对现代诗令人惊叹的理解,得以较快形成自己的格局与风采,显示出璞玉浑金的不凡品质。作品一经发表或印行,便获得从专家到普通诗爱者的广泛好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儿童诗创作(其实已远远超出传统“儿童诗”的美学范畴)的一个令人惊喜的重要收获。
四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陕西文学界及文化界对诗歌发展的漠不关心:近二十年没开过一个像样的诗歌研讨会,没出过一部像样的陕西诗选,仅有的一部比较完整、有一定文献价值的诗选《长安诗家作品选注》,还是由日本汉学家前川幸雄先生编著,1995年在日本用日文出版的!向以“长安”(在世界文化史中,这个名称不仅代表着汉唐帝都,也代表着诗国之都)为荣的所谓“文化大省”之陕西,按说,早该有自己的诗歌节、自己的经典诗选、自己的当代诗歌史以及当代文学史、当代艺术史、当代文化史等,让世人不仅是从口号上而是从文本上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文化大省”之博大精深,但至今仍是痛心者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点理想而已,现实的状况未见有什么大的改观。
如此困窘的生存条件,多年来,迫使陕西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们西出阳关、东出洛阳、南下北上以及远赴海外寻求出路,或“墙内开花墙外香”,或自生自灭,都似乎与陕西无关,难得有什么本土性的反响。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个诗的时代,普泛的公众远离诗歌,是文化转型之过渡时空的必然现象,真正的诗人也不再幻想成为时代的宠儿,而只寄希望于“无限的小众”,更不会为现行文学体制的功利计较与偏狭心态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也从来没有希望从现行文学体制中去获取一点什么。但作为体制本身,它有责任为文学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呵护与激励。而所有这些问题,实际解决起来并不难,只是我们多年已习惯于有几位著名小说家、几部获奖作品撑足了门面而了事,从不细究这门面后面是否还存在什么缺陷和危机。
中华自古有诗国之称,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诗与生活与人生的关系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密切。可以说,诗的存在,已成为辨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价值属性与意义特征的重要“指纹”——为陕西以及我们所有中国人常常引以为荣而津津乐道的所谓“大唐精神”、所谓“汉唐气象”,说到底,其核心所在,无非是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与主导——没有诗为其精神、为其风骨,没有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为其底蕴、为其主导,无论是昔日的“长安”还是今日的“唐都”(西安),都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城而已。
中华文化传统的灵魂是诗,“汉唐气象”的灵魂更是诗。尽管到了近世尤其当代,因了文化语境的巨变,这样的灵魂的存在,已不再为国人看重而呵护,但正因为如此,才是一切真正为历史亦为现实负责任的文化人与文学人,重新出发而再造国魂之处啊!
总之,步入新世纪的陕西文学界与陕西文化界,应该尽快结束陕西诗歌多年失于呵护、流离困顿的尴尬局面,从而使陕西文学整体性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新时期,让历史的遗憾不再复生为遗憾的历史。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文艺系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