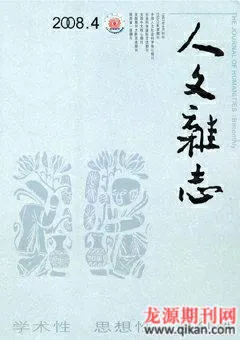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意象诗学的发生
内容提要 意象是中国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现代诗学继承中国古代意象诗学传统,接受西方现代意象诗学影响。本文阐述了影响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发生的中国古代意象诗学源流与西方现代主义意象诗学资源,探讨了中国现代意象诗学的发生期的理论形态及其特征。
关键词 意象诗学 中国古代 西方现代主义 白话新诗 新格律诗 象征主义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4-0096-11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学中一个重要范畴。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现代意象诗学开始逐渐影响了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中国意象诗学出现了异质于中国古代意象诗学的某些现代性特征,这些特征又直接影响着20世纪中国诗歌意象艺术乃至整个诗歌创作的面貌。中国现代诗歌意象接受了中外意象诗学怎样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现代意象诗学什么样的特征?它又有哪些具有诗学意义的东西值得我们阐释与总结?这些对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现代意象诗学的古代传统渊源
中国古代诗学中,意象说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黑格尔说过, “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全部证明只存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页。)意象说是由哲学关于“意”“象”关系的阐释逐步演变为诗学范畴的。从上古人们“尚象”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物象”的出现,再到汉魏六朝“形象”、“意象”的提出,直到唐代的认同,意象说才演变成为较成熟的诗学范畴。《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和“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观象制器”,魏晋时期王弼等关于言、象、意关系的哲学探讨,为意象说的形成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诗经》、《楚辞》与汉魏时期的诗赋创作是意象说产生的文学实践基础。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提出,是对意象说的一次诗学意义的推演,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艺理论著作则是意象说的一次较系统的理论总结,标志着意象说理论形态的初步形成。唐人对意象说的丰富,使意象说趋于成熟。意象说的理论形成可以说经历了两次大的基础建构与三次大的理论提升。
意象说第一次建构是先秦诸子对“象”的认识。意象论的本原与“象”有着密切的关联。老子提出的“象”与“大象”的概念,使之从具体的事物发展到哲理思想,并成为其“道”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老子认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章)老子阐述了“道”与“象”的关系及其表现形态。老子所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意为主体通过体察“象”可以得“道”,“象”也就成了老庄哲学中呈现本体,领悟本体的一种图式。首先把“意”和“象”联系在一起的是《易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上》)《易传》提出的“立象以尽意”的思想,一方面承认言不尽意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通过象是可以尽意的。它是为了尽意而立象,这个象是意中之象,意不是言所能尽的,惟有象能尽意,即象具有特殊的表意功能。“立象以尽意”对后世意象说影响深远。首先,从思维方式看,易象这种卦象思维是融感性和理性为一体的直觉思维,“立象以尽意”是意念和物象的浑然整合。其次,从审美特征看,“立象以尽意”这一思维表述体系是客观观察与主观体验的融二为一,其目的在于通过象而显意。另外,从审美表现来看,“立象以尽意”的特点是,“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系辞下》)它具有以小喻大,以少总多,以简寓繁,由近及远,深远幽隐的表现特点,接触到了艺术形象以个别表现一般,以具象表现抽象,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审美特性。
第二次理论建构是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从哲学的高度对言、象、意关系的论述,充实了意象说的理论基础。秦汉时期,天人合一,心物说的兴起,以及佛教的传入,对意象说的形成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合流,崇尚老庄,谈玄论道成为时尚。玄学源于“三玄”,就书而言是指《周易》、《老子》、《庄子》。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对意、象、言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释: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王弼所论乃是哲学认识论的命题,但是具有审美认识论的意义。他不仅是对《周易》卦辞、卦象、卦意三者辩证关系的论述,也从一般的哲学意义上揭示了言、象、意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阐明了“言”的媒介工具作用,“象”的符号载体功能,“意”的统帅核心地位。在他看来,言和象都只是意的载体,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表达意,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相生相成、相互递进的内在联系。他的“忘象”说,旨在说明“寻象”时不可拘泥于某一特定的“象”,要超脱有限的“象”,可从“象外”求之,只有这样方能得“意”,这是一种得意忘象的极致。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是对“立象以尽意”的一次哲学认识论的更深入的推衍。当然,并没有实现意象论从一般哲学论到文艺美学范畴的转换。意象说的转换及其形成具体的意象学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推导问题,而是要在一般哲学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文艺创作的实践,经过历代文人学者的探索才可形成的。
意象说的形成,经历了三次理论的提升。第一次是汉代学者解经释骚的比兴说。汉儒解《诗经》总结出赋比兴的三种表现手法。郑众曰:“比者,比方于物”,“兴,托事于物”。认为比兴是借助于客观外物以寄托主观情志的手法。王逸序《离骚》:“《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它们都是对《易传》“立象以尽意”观点在诗歌领域的运用与展开。王充在《论衡•乱龙篇》中第一次将“意”“象”结合使用:“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其义是说君臣上下的礼仪,通过画布上的兽象的寓意体现出来,“象”成了显示君臣上下不同地位的象征。他所谈的不是文学创作,而是说的同类事物之间的象具有的相互感应作用。然而,他将意象联缀成词,第一次形成了完整的意象概念,为意象范畴内涵的认识提供了语源学的依据。
第二次是陆机《文赋》的“隐”“曲”“喻巧”说,是对意象内涵的发展。陆机提出:“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若夫丰约之栽,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曲折委婉巧妙地抒写情志,词句看似粗拙,实则比喻巧妙。虽然陆机没提及比兴,而他的隐曲喻巧说,是对汉代《诗经》、《楚辞》研究比兴说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次是《文心雕龙》首次将意象运用于文学领域,使意象正式成为文艺美学范畴意义上的学术概念,诗学意义上的意象范畴得以完备。刘勰对艺术构思过程中意象的内在生成,艺术表现中意象的外在实现,意象的思维特征,意与象之间的辩证关系等进行了总结与阐发,使意象说从体制理论总的阐述到创作过程的具体探索,鉴赏过程与批评标准的论述等方面形成了较系统而完备的理论。他在《神思》篇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是意象在文艺美学范畴中的第一次出现,是文论史上首次将意象运用于艺术构思中。“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他这里揭示的是艺术构思过程中的联想特征,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以致“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这是想象超越身观限制而达到的神思的极致境界。所谓“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则是一种心物交融的思维活动规律。在《比兴》篇中不仅对比兴作了新的阐释,还指出了意象思维特征是“拟容取心”,即通过描摹生动具体的形象反映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在《隐秀》篇中阐述了“意”“象”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意”应该“隐”,“象”应该“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义为工,秀以卓绝为巧。”作者的“意”只有隐藏在鲜明具体的形象描写之中,才能给人丰富持久的美感。在《情采》篇中强调“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在《物色》篇中阐述了情景辞三者的关系:“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诠赋》篇的“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明诗》篇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探讨的是客观物象触发并影响作者思想情感,使之进入构思想象活动的情景。刘勰完成了意象理论从哲学向文艺学的转变,《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意象说集大成的学术著作。
唐代以后,意象说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其标志为,唐代的诗论大多为诗人之手,与创作的联系尤为密切,使意象理论的内涵得到了认同、丰富、充实。除诗论外,意象理论向书论、文论、画论拓展、融会,形成了其理论形态的互补与深化。一批与意象相近的概念与范畴的出现,拓展了意象诗学的领域,促进了意象诗学的发展。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的“境象”说,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提出的“兴象”说,皎然《诗式》中阐述的“象下之意”说,贾岛、白居易的“内意”、“外意”说,司空图在《诗品》中提出的“三外”说(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丰富了意象诗学的内涵,中国意象诗学在唐代已臻于成熟。意境诗学也在唐代开始形成。此后,意象论与意境论互相渗透影响,并行共生,成为了中国诗学体系的两块基石。
由于意象说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关意象的理解丰富而繁杂。概括来看,古代意象说的涵义大约有五种。一是表意之象(《易经》中的卦象);二是意中之象(刘勰的“窥意象而运斤”);三是意与象的二元指称,意指主观,象为客观,两者契合为意象(明代何景明的“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四是接近于意境(姜夔的“意象幽闲,不类人境”);五是有艺术形象的意思(刘熙载的“画之意象变化不可胜穷”)。古代典籍中意象概念的运用有很大的随意性,外延相当宽泛。中国早期的意象论主要是在文化学、哲学意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内涵,到《文心雕龙》的出现,意象内涵开始了向文艺审美认识论的转变。
二、现代意象诗学的现代主义诗学资源
到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开始接受了西方心理学以及文艺心理学、意象派、象征派等诗学的影响。20世纪初期欧美学术界中,意象作为一个术语首先是在心理学中出现的。心理学中的意象指的是感知在大脑皮层形成的表象。后来从文艺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把意象看作是心理表象、知觉表象、记忆表象,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留下的感性形象性的表象,或指头脑中创造的想像性表象或想像性形象。康德认为,天才“能够把某一概念转变成审美意象,并把审美意象准确的表现出来”。他还说:“审美趣味的最高范本或原型只是一种概念或意象,要由每个人在他自己的意识里形成,他须根据他来估价一切审美对象。”(注:转引自汉斯•摩根素《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他明确把意象看作是内心之象,在《资本论》中强调“内心意象”是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区别的标志。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中对思维活动中的心理意象作了全面分析,他注重思维中意象的视觉形象因素的参与作用,把具象性、视象性看作是心理意象的基本特征。
荣格的“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或“原型”(archetype)意象论认为,意象不是外部对象的心理反映,而是一种幻想中的形象,与对外部世界的知觉只是间接相关,更多来自于无意识心理内容,并突然显现于意识之中。他特别强调意象的幻想性及其与无意识的联系。他认为每一个原始意象都是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活动中的一块碎片。他肯定了原始意象与神话原型、文化原型的联系。黑格尔说:“诗人的想像和一切其他艺术家的创作方式的区别”,在于“诗人必须把他的意象体现于文字而且用语言传达出去。所以他的任务就在于一开始就要使他心中观念恰好能用语言所提供的手段传达出去。”(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3页。)萨特在《想像心理学》中说:“艺术家最初便有一种以意象为形式的观念,而后他则将这个意象体现在画布上,……艺术家并没有完全使他的心理意象得到实现。”他们所持的这种心理或观念意象论在西方美学中广为流行。不过到了克罗齐那里,他认为“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成立。”(注:朱光潜:《诗论》,《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此处的意象再不仅仅是审美心理学上的意中之象了,它泛指艺术审美创造的形象。苏珊•郎格认为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肖像性符号,即“情感形式的意象”(image of the forms of feeling ),这种意象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显现出生命活力和思想情感活动过程的式样,这是一种动态的生命形式意象,强调了艺术意象传递或承载情感表现的动态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宏观的意象表现观。
20世纪初期出现的英美意象派诗论接受了中国古代意象诗论的影响。他们注重意象的直接性、精炼性。意象派认为,中国诗人满足于把事物直呈出来,而不加以说教和评论。弗莱契说:“正因为中国的影响,我才成为一个意象派,而且接受了这个名称的一切含义。”他还说:“我在《辐射》和《蓝色交响曲》中所倾心的那种美学上的精神,并不是没有哲学背景的,但这种哲学背景是中国式的而非欧洲式的。在《蓝色交响曲》中有老子的‘清静主义’、无为精神和谦卑态度,也有佛教精神,它们的原则有效地隐藏在自然之中,比华兹华斯在自然中找到的福音有效的多。”(注:转引自赵毅衡:《远游的诗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9页。)庞德在1915年说,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希腊人那里寻找推动力。意象派在对中国诗的接受过程中找到了英美现代诗歌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诗形成了对美国新诗的有力影响。
意象派诗学的渊源是多方面的,其中直觉主义与象征主义就是两个重要的源泉。庞德说,意象不是图像的重现,“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感情的复合物的东西”。意象不是客观之物象,意象是诗人借助客观物象或图像完成自己对心理世界的呈现,是主观之思与客观之象的复合体,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客体化。在意象派诗人那里,“不把意象用于装饰,意象本身就是语言”(注:彼德•琼斯编:《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33页。)。作者用意象,是因为他通过这个意象来思考来感觉的,意象是物态化、知觉化了的思想或情感。意象派接受了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影响。柏格森认为,艺术是一种直觉,艺术家的心灵在于能以直觉超越理性。对诗人而言,他应该以诗来统万端于一体,将大千世界的一切,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声光色彩,抑或是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都如其本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有欣赏力的读者透过眼前语言呈现的直观形象体会到语言之外的东西。意象派诗人休姆认为,诗中的意象不是装饰成分,而是直觉语言的根本要旨。梅•辛克莱也认为,意象不是替代物,它是表现而不是再现,你无法分开事物与意象。意象论直接借鉴了直觉主义,直觉主义构筑了意象主义的哲学基础。
意象派诗学与象征主义诗学关系密切。象征主义诗学把世界看成是自我的影子,诗人应该是一个具有超常智慧的幻觉者。人可以通过非理性的内心世界,在梦幻般的状态下体会万物之间的种种互通的神秘感应。强调诗歌的真谛是寻找思想的客观对应物,建立情绪的相等值,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架起具象化的桥梁。法国象征主义诗论主张“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内生命的反射”,他们批评巴那斯派诗人,仅仅是全盘地托出事物,缺乏神秘性。威尔逊在《阿克尔的城堡》中阐述象征主义本质时指出:“去暗示事物而不是清楚地陈述它们乃是象征主义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叔本华认为自我意志是世界的本质与核心,而意志是非理性的,只有通过直觉梦幻才能达到。康德认为,纯然感受外物是不足的,真正的认识论必须包括诗人的想像进入本体世界的思索,必须由眼前的物理世界跃入(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直觉主义与唯意志论哲学观皆是象征主义与意象派意象论的理论背景。
20世纪英美现代主义意象诗学提出了“思想知觉化”的主张,认为“诗不是感情”,“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页。)。叶芝认为“诗人应有哲学”,但不是说明哲学。他们所努力的是在感性与理性、感觉与抽象的两极对立中找到诗的张力,实现诗的情感的知性化,达到感性与知性的契合。他们具体地探讨了一系列有关意象诗学的具体范畴。瑞恰慈在他的《文学批评原理》中指出:“一个孤立的语像(相当于意象)在文本中的意义是由它所取代的东西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代替某事物或某思想而存在,它就是那个意义。”这里,语象具有了取代事物或思想的符号意义。他所代表的新批评派还讨论了比喻性意象与象征性意象的区别。瑞恰慈提出了比喻的“远距”原则,“比喻是不同语境间的交易,如果我们要使比喻有力,就需要把非常不同的语境联在一起。”他认为,比喻意象的“喻指和喻体之间多少有相同之处,而象征的两造之间往往没有相似点,它们主要靠由于各种原因而形成的联想来连结。”(注: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2-94页。)按照他们的看法,比喻的两造之间距离越远越好,如果二者的连结是完全违反逻辑的逻辑,那就含义更见丰富。他们称之为“不相容透视”。传统修辞学认为是语病的错逆比喻(oxymoron)、矛盾误用(catachresis)、和混杂比喻(mixed metaphor),在诗中完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