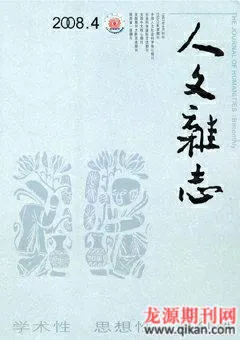儒家道德的德欲对立性
内容提要 中国人对儒家道德情有独钟的事实,重视其正面的价值已是潜规则。其实,这是非常失理性的举措。紧贴世界发展的现实和儒家文献的事实来审视儒家道德思想,我们不得不重视的是,中国悠久的道德文化积淀,不仅使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水准上与其他民族存在巨大差距,而且道德的现实水准也存在巨大的反差。这一现实要求我们认真反思和重新审察儒家道德,其实主因就在儒家道德本质上内置的德欲对立的价值尺度;在欲望只有符号的价值地位的氛围里,道德只能成为舞台的唱本,骗人的把戏,现实中没有道德的丰收季节也属正常。事实上,德与欲分属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的主题,道德资源的开发,要求我们在认识儒家道德哲学本质的同时,还德欲的本来面目,以便有效地润滑中国现代化的实践。
关键词 儒家道德 德 欲 公义 人欲
〔中图分类号〕B222;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4-0044-08
绪论
在先秦儒家道德思想的长河里,尽管有告子、郭店楚墓竹简中反映出来的对何谓本性问题的关注,但是,这种倾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思想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个人在成为具备仁德之人问题上装备自信心,其结果就是在原点的本性上就赋予个人都具备成为仁德之人的能力,人的本性善的理论就是具体的凸现。显然,这是理论上的设计,是从外在的主观臆想出发的,既脱离人的生物性特征的运思,又无视个人实际情况的考量。本来,能否成为仁德之人,完全决定于个人的情况,而不是外在的臆想。无论是人的先天本性是善的,还是人本性的后天发展现实是恶的,但都具备成为尧舜的可能。长期以来,学者都忽视了一个悖论:现实生活里存在两种人,即圣人和一般人。圣人为什么可能的问题,一直为人所忽视。而在这一定式里的道德实践也总是给人屡战屡败的感觉,不停的道德实践运动是因为现实道德低靡而来的冲击波所致。问题的关键,为我们所称道的儒学,关注的仅仅是理论的演绎,根本没有问津现实效果。
在没有依据人性特征和个人的现实而得出的理论里,个人永远只能是关系中的被动者,根本没有内在动力可言,这发展到后来就更为严重,“确实,对于像朱熹和王阳明这样的新儒家来说,一个形而上学的事实是:我(在任何时刻)总是有现成的能力认识正确的行动,并有动力去做正确的行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动力不足的问题被新儒家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排除了。但是,相关的问题仍然存在。”(注:《孟子的动机和道德行动》,〔美〕倪德卫著,y3LGjFyaSoEZsSGI2ji9Kfv1nrgjvb2A7bARNC9xOxs=〔美〕万百安编,周炽成译《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50页注释45。)不是“动力不足”,而是根本没有动力;也并非到朱熹和王阳明的时代是这样,其实在先秦儒家那里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儒家对本性的设定,把人带入了一个飘然欲仙的轻松境遇,既然本性是善的,无论如何都与丑恶没有干系了。这是对人极不负责的行为,是异想天开的犯罪。美国学者对此有精彩的概括:“德这个原始概念的结构结果产生了一种悖论:为了取得‘德’,人必须已经有了它。更坏的是,追求德就是追求一种优势(好处),而这种优势是非德的。”(注:《德可以自学吗?》,〔美〕倪德卫著,〔美〕万百安编,周炽成译《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67页。)这是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的总结。
为了有德,必须已经有了它,实际上这在人的本性里已经得到孟子和荀子的内置。内在德性的设置,为外在的有德追求做了理论演绎上的支撑,在这一特殊的系统里,德行和欲望呈现对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一
在词义上,“欲”是形声词,从欠,谷声。“欠”的意思是有所不足,故产生欲望;本义是欲望、嗜欲。《说文解字》解释“欲,贪欲也”,显然存在不当之处,仅从消极面上进行把握,其限制暴露无遗。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思想里,“欲”表示的是个人的欲求,而且最初多用作动词;离开个人就没有“欲”存在的理由。“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注:《吕氏春秋•情欲》。)人不仅有欲望的存在,而且存在贪欲的情况。欲望具体是通过情感表现出来的,圣人与一般人的不同,就在于能够通过节制情欲而达到“得其情”,这是客观的事实。
在本质的意义上,欲望除了私欲以外,并不存在“公欲”,这跟日语对“欲”的解释是一致的。日本汉学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欲”,就是做私欲来理解的。先秦儒家也用“欲”来讨论人的欲望,因此,我们在孔、孟那里找不到“人欲”、“私欲”的概念。“私欲”概念的最早出现在《荀子》,约有3例;“人欲”概念的最早使用当是《礼记•乐记》,仅约1次。儒家所体现的德欲的对立,正是贯穿在对欲望的认识和规定的演进过程之中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究明,正是对本问题的回答。
孔子虽然有对“欲”的详尽论述,但并没有正面回答何谓欲的问题。就现在掌握的资料,关于欲望的产生,有“欲生于性,虑生于欲,倍生于虑,争生于倍,党生于争”④
《名数》,李零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69页。)的阐述。也就是说,欲望产生于本性,有欲望就有谋划,有谋划就会出现背弃,背弃必然产生争斗,争斗自然偏私成伙;另一方面,“贪生于欲”、“喧生于欲”、“浸生于欲”、“急生于欲”④,欲望还是贪婪、喧哗、沉溺、狭窄的源头。
在荀子那里,“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荀子•正名》。)。情感是本性的内容规定,欲望是情感的应对,或者说,欲望是情感的具体化;追求欲望是人情所不可避免的课题,无论是谁,无法离开欲望的满足,欲望使本性变得完备。与竹简的意思是一致的。
由于欲望产生于本性,是本性的因子之一,而本性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所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注:《论语•里仁》。);“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注:《荀子•荣辱》。)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注:《孟子•告子上》。)。富贵是人人的共同追求,饥饿了要吃饭,寒冷了要穿衣,劳累了要休息,爱好利益、厌恶祸害,这些都是不需任何外力推动的,无论谁都一样,可以说是人之自然。不仅如此,而且人与人之间具有相同的味觉、听觉、视觉爱好,即“同美”。所以,追求欲望是人性的必然内容。而相同的味觉、听觉、视觉的满足,使人与外物建立了客观的联系,这外物就是“人之所欲”。由于人的生物特性使人与相同的外物形成联系,这又为争斗的产生埋下了伏笔,或者说,从另一个侧面回答了上面提到的争斗产生的原因。
二
只要是人,就都有欲望,满足这些欲望也是平衡人性的课题之一,只有保持人性的平衡才能实现健康的生活,这应该也是黄金规律之一。在本性的特征上,不得不注意的是,人性本身存在极尽欲望的因子,即“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注:《荀子•王霸》。)。眼睛要欣赏不同的颜色,这是人的需求之一,但是,“目欲綦色”说的是要看尽一切颜色,“綦”是“极”的意思,其他的器官诸如耳、口、鼻、心也一样,这种“欲綦色”、“欲綦声”、“欲綦味”、“欲綦臭”、“欲綦佚”的情况,是人情之自然,人情之必然。
以上是理论上审视人性得出的结论,实践上的情况也一样。“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注:《论语•公冶长》。)有人认为申枨是刚毅不屈的人,但孔子认为他贪欲太多,无法达到刚毅不屈。所以,如果对本性“欲綦”的因子调控不宜的话,就容易走向贪欲。在上面说到,“欲”本身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一般意义上的欲望,二是专门指嗜欲即贪欲。因此,“欲”有时就是在贪欲的层面上切入的,如“李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注:《论语•颜渊》。);“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⑤《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亦可以为成人矣”
⑤。这里列举的“欲”都是贪欲的意思。对人而言,如果不贪欲的话,即使奖励你,你也不会去行窃;但要做到这一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可以为难矣”,即使做到了也不一定就是具备仁德的人。不过,不贪欲即“不欲”是“成人”人格的因素之一。
在贪欲意义上使用的“欲”,那“不欲”就是“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中所说的“五美”之一的“欲而不贪”,有欲望是可以的,但不能贪婪。“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注:《孟子•离娄下》。)。对耳目之欲不加任何限制的话,必然带来祸害,戮及父母,这是五种“不孝”行为之一。而且,“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埶不能容,物不能赡也”
⑩《荀子•荣辱》。),在客观的层面,如果不对欲望进行必要的节制,情势也无法容忍,物产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这也是上面已经分析到的“人之所欲”相同的原因。
人有欲望的本性基础,人必须满足一定的欲望,但又不能贪欲;尽管贪欲是必须否定的,但贪欲的事情是客观存在的;根据什么基准来施行“欲”,即如何把握欲望的分寸?的确是一个难题。所以,先秦儒家提出了以下的设想,“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⑩
心的育养最好是“寡欲”,即利欲之心少一些;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寡欲”,即使遇到意外的不测而危及生命,造成“不存”的后果,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如果利欲熏心的话,即使能够存活下来,也是非常少见的事情。在一般的意义上,人在食、衣、行、住上,都希望“刍豢”、“文绣”、“舆马”、“余财蓄积之富”,而且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是“人之情”的现实。但在现实的人生里,才得知生活的艰辛,即使有条件也“食不敢有酒肉”、“衣不敢有丝帛”、“行不敢有舆马”,这并非“不欲”,只是担心“无以继之”的原因,并通过“节用”来调适欲望即“御欲”,实现实在的“收敛蓄藏”,来保障以后的生活。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御欲”不是控制、制御欲望的意思,而是治理、调适欲望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性理之必然与实现性理之现实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必须依靠“御欲”,因为物产本身难以保障人们欲望的满足。
三
以上只是对欲望的一般性讨论,以及如何通过“节用”来达到不贪欲的运思,现实物产丰富的程度无法满足人们欲望,这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来实现社会的稳定?于是,思想家又运用惯用的伎俩,搬出了君子,“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埶也;安燕而血气不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注:《荀子•修身》。)“求利也略”就是在追求利益的问题上保持简略的尺度,做到体现“隆仁”的“贫穷而志广”,“杀埶”的“富贵而体恭”,“柬理”的“安燕而血气不衰”,“好交”的“劳倦而容貌不枯”,“法胜私”的“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在此,应该特别引为注意的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喜怒是欲望的表现形式之一,“不过夺”、“不过予”显然也是遵循简略的原则后实现的自然结果。
“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的结果,“私”就是“私欲”,“法”就是“公义”即仁义之理。这里就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即从对欲望的一般论述,进到了以仁义之理对欲望的层面,而且把欲望说成“私欲”,而仁义之理就成了公法。显然,这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私欲”这一概念的,“公义”与“私欲”成为事实上对立的两极,而且树立了能够为了公法而牺牲自己“私欲”的典型的形象君子。但是,君子为何可能?“公义”代表什么?“公义”与人有什么关联?当我们质问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是中国公私开始对立的现实印记,本来公应该是实现私的保证,是私人利益的保障,但现在这一切在原初的时点上就踪影荡然无存了。荀子虽然看到“欲”就是“私欲”的本质,并提出了“私欲”的概念,但一开始就把它置于和抽象空洞的仁义相对立的地位,否定了客观存在的公私所属不同领域的事实,是荒唐和昏庸的举措(注:参照“夫主相者,胜人以埶也,是为是,非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荀子•强国》);“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荀子•解蔽》))。
毋庸置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实际上就看到了对欲望节制的必要性,他认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注:《论语•为政》。),人到70岁虽然可以“从心所欲”而行,但不是没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不能逾越规矩即“不逾矩”;因此,面对欲望,“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注:《论语•里仁》。),把“道”作为规范欲望的天平。孔子这一思想为荀子所继承并发挥,荀子说:“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注:《荀子•正名》。);“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注:《荀子•乐论》。)穷尽欲望虽然“不可”,但追求可以“近尽”;去除欲望虽然“不可”,但是可以“节求”;“近尽”、“节求”的基本标准就是“道”。在对待“道”和欲望的态度上,君子和小人正好相反:君子“乐得其道”,时时以“道”为依归来运作欲望,达到的客观结果是“乐而不乱”;小人“乐其欲”,追求欲望,根本没有“道”存在的位置,达到的客观效果是“惑而不乐”。显然,君子是身心的快乐和愉悦,小人是身心的困惑和劳累。
“道”的内涵在实质上就是上面提到的“公义”,形下的样态就是“礼义”,“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注:《荀子•王制》。);“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注:《荀子•礼论》。),都说明这一点。人有相同的欲望即“欲恶”,欲望不能自然得到满足。所以,人必须向外追求,如果没有任何规则可依顺的话,在追求的过程里必然出现争斗,最后走向混乱。社会混乱是统治者所厌恶的。所以,他们制定“度量分界”,即“礼义”来明确人们的分际,一方面维持社会贵贱等级的稳定,按照不同等级的标准满足该等级序列里人的需求,保持欲望在人性轨道上运行的条件即“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另一方面则维持人需要与自然物产之间的平衡,使物产与欲望“相持而长”,也就是在人的欲望与“人之所欲”之间保持共作互存。
德行与欲望的对立,实际上,孔子就开了先河。孔子把“欲仁而得仁,又焉贪”(注:《论语•尧曰》。)作为解释“欲而不贪”的内容。在孔子看来,欲望就是“欲仁”而已,诸如“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论语•述而》。);“李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注:《论语•颜渊》。),都是具体的证明。只要“欲仁”,就可以“得仁”、“仁至”;只要“欲善”,就可以“民善”。欲望的讨论完全局限在仁德上,仁德以外的就是荀子所说的“私欲”,这是完全应该禁止的,德欲已经处在对立的位置上了。
实际上,在欲望的问题上,社会的等级“礼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特权。所以,在原本的意义上,欲望是人的私人事务,针对人性内存的贪欲的因子,即使要加以抑制,自然必须首先依据人性的特点来进行设计。但是,儒家的思想家背其道而行之,关注的首先是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和自然物产的现实,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社会等级秩序、自然物产这两个因素作为“礼义”决策的依据,但是,把人本身排除在外的做法,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是毫无道理的,而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礼义”成为虚设,成为躯壳,中国后来的事实就是最经典的讽刺和回答。
四
把欲望看成私欲,个人以外的其他一切都与它对立,自然就没有其合法的位置。《周易》里也有“君子以惩忿窒欲”(注:《周易•象传下•损》。)的观点,“窒欲”就是熄灭欲望的意思。众所周知,“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提出来的扭曲人性的观点,作为道德的“天理”和人欲完全对立,人欲没有丝毫的位置肯定。既然人欲离不开人,在原本的意义上,它是人性的内在因子,没有了人欲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在科学的意义上,没有了人欲,就没有人本身这个载体了。所以,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在本质上只能是对人的屠杀,人成了躯壳,别说活力了,其用处只有一个,就是玩具、玩偶,如果要冠上其主体的话,那只能是统治者的玩具、玩偶。
理学家虽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但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下面的资料就是具体的证明,“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注:《礼记•乐记》。)上面已经提到,在先秦儒家的著作里,“人欲”约有一个用例,实际指的就是这里的文献。这里回答了圣人采用礼乐来节制人的欲望的目的,绝对不是“极口腹耳目之欲”,简言之,就是“极欲”,因为,在上面提到人的欲望具有“綦”的特性,“五綦”是人情之必然,“綦”就是“尽”的意思,与“极”基本是同义的。礼乐是为了“教民平好恶”,这里是民而不是一切人。应该注意到的变化是,前面荀子的情况,只是人为地搬出圣人、君子,封他们为节制欲望的楷模,能够“公义”胜“私欲”。为什么圣人、君子能够做到“公义”胜“私欲”?因为他们是圣人、君子,这仿佛与在前面提到的“为了取得‘德’,人必须已经有了它”的逻辑如出一辙。
礼乐是为了保证人们返回“人道之正”。人道告诉我们,本性虽然是虚静的,这是天性的一面,但在外物的作用下,本性的内在因子就会运动,这是“性之欲”即本性具有欲望的因子。所以,当外物出现时,人的理智就会自觉认知,然后就把爱好和厌恶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一个人如果不能节制自身内在的“好恶”,在外物不断引诱的情况下,加上不能躬身自问,其结果只能造成“天理灭”。换言之,在外物感人无穷,人的好恶无节制的境遇里,人只能成为外物俘虏的对象,或人为外物所化即“人化物”;“人化物”的情况,是“灭天理而穷人欲”的情况,也就是毁灭“天理”、穷极人欲的情况;并最终产生“悖逆诈伪之心”、“淫泆作乱之事”,在这样的处境里,呈现的是一幅“强胁弱”、“众暴寡”、“知诈愚”、“勇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的图画。由此看来,礼乐可谓任重而道远。
但是,虽然搬出礼乐来控制人欲,是人为的“公义”胜“私欲”的做法,但如何可能的问题,仍然非常尖锐地存在着。不过,在儒家道德哲学不注重“何谓”和“如何为”的天地里,事实上并不存在我说的疑问。在上面的“灭天理而穷人欲”的概念里,“穷人欲”是非常明确的,没有必要说明;但是,“灭天理”的“天理”指什么?还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大家知道,宋明理学家的“天理”指的是与人欲相对立的道德礼仪等一切符号形式,这里的“天理”是否就是礼乐?我认为,不全是。从上面的引文来看,“灭天理”的提出是在人不能在外物的引诱下顶住压力而成为外物的牺牲品即“人化物”,人为外物所化,“人化物”的结果自然是“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状态遭到破坏,而趋于“穷人欲”的境地,本性失却平衡;所以,这里的“天理”应该包括礼乐和人之天性两个方面。这也显然与后来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用心相异,这里表明的是:要存天理,就得灭人欲;灭人欲必须通过存天理来完成;这是动机论上的立论。“灭天理而穷人欲”是从结果上立论的,也就是说,天理毁灭了,人欲就会趋于无穷的追求外物的过程中。理学家把“灭天理”变成“灭人欲”,把“穷人欲”变成“存天理”,虽然是概念的简单排列上的改变,但这一改造把天理人欲对立的倾向推到了至高点,从而也在明确化的程度上埋下了儒家道德无人性化、无根源化的种子。
但是,《礼记•乐记》里人欲的提出,在中国道德杀人的历程里,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因为,孔、孟只是有单词“欲”的使用,他们主要把欲望依归在仁义道德上面,诸如“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到荀子那里,不仅提出了“私欲”的概念,而且把“公义”置于“私欲”对立的地位,不是对应的位置,并在价值论上赋予绝对的意义,因为,在中国古代关于公私的界定里,“公”不是“私”的集合和凝聚,“公”不包含“私”,“公”仅是“私”的克星;在一开始,“私”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内涵规定和权利赋予,畸形的开始,不可能有正常的发展,只能是越发畸形;应该说,荀子敏锐地把握住了孔子的价值追求取向,很快说出了孔子在说却没有明言的思想观点。到《礼记•乐记》“人欲”的提出,道德杀人完成了普遍的理论基础的奠定,从“私欲”到“人欲”不是简单一字之差,而是根本性的变革,“私欲”本来有道出欲望特征的方面,因为欲望的初衷就是私人的事务,不涉及他人的方面,荀子对人性的犯罪就是拙劣地硬把“公义”罩在“私欲”的头上,使得中国人的欲望只能在畸形的航道上得到畸形的发展;“人欲”把本来是私人的事务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人的事务,为道德杀人完成了一般理论前提的设定,中国的历史,也从此把人欲视为洪水猛兽,一直在公义的穷追猛打之下,没有合法安身之处。
结论
以上描绘了儒家在欲望问题上的演变发展的轨迹,尽管是粗略的,但却是非常明确和感触人的。实际上,德欲的对立,在先秦儒家这里就已经完成了理论的设计,人们只知道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实在是喧宾夺主的举措。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不仅是无穷的,而且其任务也是非常沉重的,因为,在中国的现行研究里,仍然出现不顾历史事实的情况。把德(德行)抬到至高的地步,把欲(人)安放在最低的地狱之中,这样的结果是,人性没有合理发展的一切条件,人也不可能出现完满的人格发展。人欲是人性的必然内置因子,只要生命本身存在不出现问题,满足欲望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即使你把标准确定在最低点,但也无法否定满足欲望的事实,而且越是不让人尽情满足欲望,欲望本身越发对人存在神奇的魔力,不管是谁,只要是人,都客观存在去探索、探知这个神奇魔力的欲望,这是欲望之中的欲望,本来不属于人性内置因子的范畴,这是中国人的专利,是天理、人欲对立而生发的例外人性伪因子。“灭人欲”的愿望自然只能是痴人说梦,本身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因此,在天理人欲对立的氛围里,出现满足人欲的情况是非常自然的行为之举,也不可能在法律上对此严罚,如果严罚,最终的结果是人本身的毁灭,即使是民众的先毁灭,圣人也逃不掉最终毁灭的命运,圣人无法自食其力。因此,聪明的圣人往往对违反“灭人欲”的情况,采取的是道德上的惩罚,以与推行的理论保持形式上的一致,当然是不顾及任何实际的效果的,所以,“对罪恶的态度坚决而认真,但除了道德上的惩戒外,没提任何惩罚措施。”②《多元信仰》,〔美〕亚瑟•亨•史密斯著,陈新峰译《中国人的德行》,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年1月,第341、342页。)而道德上的惩戒是无力的,在这种互相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境遇里,中国人的自然收获是“现世现报,无形中培育和鼓励了利己主义,不是贪婪,就是野心勃勃”②,这与我提出的儒家道德的本质是“自己本位”相吻合参照许建良《自己本位——儒家道德的枢机》,《人文杂志》,2006年第2期,第66~71页。)。
“公”与“私”的对立,最终是两者的完全脱离,无关系。作为个人,既看不到自己的一私之身在“公”那里得到寄托的任何希望,也看不到自己的一私之利益在“公”那里得到实际满足的任何曙光;接着的质问是,生命如何延续?既然“公”不可依赖,就只能依靠自己来进行延续生命的实践。人欲的事务就完全变成了私人的事务,在事实上回归了“欲”的语词本义,这是一幅理论与事实相悖的图画,无疑是对儒家思想的讽刺。在相悖的现实演绎里,个人与社会在两个不同的场域里各自实施着自己的行为,客观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两者力量的消解,个人的力量没有能够有效地汇聚到社会之中,社会的合力自然无所附丽,人也不可能产生爱社会、爱“公”的情感,当然更不可能有实际的增强社会合力的行为。中国不存在具有独立价值地位和意义的集体,因为集体都是某些个人的财产,所以,事实上的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只能是沙子和水的关系,个体仿佛沙子,不可能融化到水里去,虽然浸泡在水里,但与水是分离的状态,绝对不是一体的。客观的事实是,只有真正一体时,个人才能为集体出力和流汗,中国后来的社会发展的现实图画就是最好的回答。我们今天的人均力的现实,也无法排除来自与先秦儒家道德在德欲问题上强调对立的价值取向的直接关系的影响,而人均力不提高,就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听到我们本该有的声音。对这种本质情况的描绘,日本思想家岛田虔次的总结可以作为参考:“对于既成的社会,对于作为通常观念的社会,对于作为名教的社会来说,对之有威胁的新兴社会,屡屡被作为‘个人’而受到贬低。相对于君子的是小人;相对于士大夫读书人的是庶民、愚夫愚妇;相对于天理性社会的是人欲的社会;这样的对立曾经被置于极其幸福的秩序之中。根据儒家的古典理论,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充实与缺乏的关系——这里的所谓缺乏是在原理上几乎不可能充实的缺乏——而成为极其自然的上下阶层。也就是说:君子
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郑玄所说的‘民,冥也’(《论语•泰伯注》),是一语道破了天机;荀子把人分为‘有礼为士君子,无礼为民’(《礼论》),总而言之也是归于同样的意图。不以诗书为事的庶民,既不具备认识理之当然的知性能力,也不具备履行礼mlKYqPi6FSEb4gHvgwbQ2I+gq/pkSTWomrrURi4FYOM=之要求的道德能力。不!更正确地说那是极度的缺乏。于是,天下就有治野人的君子和养君子的野人所组成;大人有大人之事、小人有小人之事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天下之通义’(《孟子•滕文公》)。这样的人的社会的秩序,就是被称为‘礼’的东西;那正是与天地自然之秩序相一致的(‘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或者不如说那就是天地自然的秩序本身。”(注:〔日〕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17~118页。)
在德行与欲望问题上的行为和举措,同在东亚文化圈里的日本的情况,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他们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初在唐代开始从中国引进的典籍里,《论语》《孟子》《孝经》等就是其中的内容,他们明锐地洞察到了儒家思想无视人性的现实,把人无限神话,只做表面文章而不顾事实的缺陷,立足于人的现实,对人的欲望的满足表现了少有的宽容。以下两个资料就是西方人做的最好的总结。
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即“和魂”与“荒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没有注定一个灵魂要进地狱,另一个则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须的,并且在不同场合都是善的。③《人情的世界》,〔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131、123页。)
像日本这样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似乎坚决要把私欲谴责为罪恶并要求从内心根除它。古典佛教的教义就是这样。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却对感官享乐那样宽容,这就更加令人惊异。日本是世界上有数的佛教国家之一,但在这一点上,其道德伦理显然与释迦及佛典对立。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侵入人生重大事务。③
人不能离开善恶,同时把善恶看成人的两个不同的部分,并区分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把人的活动领域区分成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事实,前者是私人生活领域,后者是与他人发生关系的领域;拿现在的言语来表达的话,前者就是工作以外的时间,后者是工作时间;区别对待不同的关系主体情况,显然是比较合乎人的本性特点的,尊重了人的多种需求,并为人在不同场合承担不同义务、达到人生创造的最高价值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我初到日本的时候,到京都的寺庙、神社里参观的时候,发现日本的和尚有家室,过着常人的生活,对此有些不理解,现在就没有存在疑问的任何理由了。
儒家道德哲学在本质上设置了德欲对立的价值尺度,欲望只有符号的价值地位,在现实生活里完全从属乃至消融在德行之中,所以,道德成为舞台的唱本,骗人的把戏,现实中没有道德的丰收季节也属正常。事实上,德与欲分属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的主题,道德资源的开发,要求我们在认识儒家道德哲学本质的同时,还德欲的本来面目,以便有效地润滑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使道德真正产生作用,彻底取缔它只是摆设的角色功能。
作者单位:日本国立东北大学
责任编辑:刘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