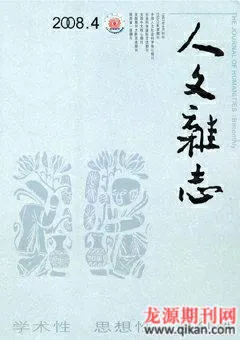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内容提要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 自由意志 道德 应该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4-0016-07
“我应当做什么?”这是康德谈到的哲学“四大问题”之一(注:康德在《逻辑学讲义》中这样写到:“在这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能够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学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这一问题可以引申为这样的伦理学问题:如何才是“应该”的?道德上的“应该”由什么决定?自由意志素来被认为是道德评价和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具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中因为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因而要背负道德责任的重荷,也由此彰显出行为主体高尚的人格和人性的尊严。但是,自由意志并非行为主体选择道德行为或不道德行为的绝对根据。哪些事是应该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的?是否应该对某事承担道德责任?这些道德“应该”既与人的自由意志不可分割(否则就无道德“应该”可言,一切皆由必然性决定),又不能完全认为是因这“一个理由所引起”的(否则道德责任便沦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迫使道德主体的自由意志成为一句空话)。如何确定道德实践中的“应该”是行动哲学和伦理学领域中一个基础而重要的问题,也是道德活动的逻辑起点,贯穿于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始终,也规定和制约着伦理学中诸如“善”与“恶 ”、利己与利他、个人与集体等关系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道德哲学从而也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一 、自由意志作为存在之存在性意义
哲学视阈中的存在性意味着哲学言说的起点,意味着哲学阐释系统的第一个事实或第一原理,是超越因果系列的本有或原初之性。自由意志的存在性意指自由意志乃为人与生俱来拥有的一种生命冲动或能力,是人之为人的原始根据。对于自由来说,胡适曾认为中文里的自由是指“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做主;西方的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制裁之下解放出来。依此来看,自由就意味着没有外在障碍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行为。“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行为”的说法就将自由这个神圣意义的词汇赋予了人这个存在物。非生物、植物、动物都不存在自由问题。 “从外力制裁之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就是通常所说的消极(或外在)自由;“由于自己”的自由则是一种积极(或内在)自由。自由与意志紧密相连,而与知(认知、理解)、情(愿望、理想)的关系则较意志为远。王海明先生在他的“论自由概念”一文中曾举例说,我的腿跌断了,但是,看见别人踢球,我便也极想望去踢;可我却不能按照我想望的去踢:由此显然不能说我无踢球的自由,而只能说我无踢球的能力。人只有在他认为有能力做某事时,才会有去做某事的意志,也才会显示出自由的意义。比如你的腿是好的,你有踢球的能力却因其它阻力或障碍的存在而不能去踢球,你的目的(意志)无法实现,这时我们就可以说你是不自由的(注:参见王海明著:《论自由概念》,《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因此,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非想望进行的行为。可以说,自由就是人的存在意义。在心理学的概念中,意志是指人有意识地确定目标、根据目标调节和支配行动、克服困难以实现目标的心理过程;而哲学意义上的意志,其最基本的内涵是人的内在欲求,是生命的冲动与渴望。意志面对自由的存在意义,则是人对自由的坚守和祈望。自由意志即由生存欲望生成的一种能力,是人的一种类本质,是原始的、也是本原的。一个人拥有自由意志,就是赋得了这样一种权能,能够把自己意愿什么和不意愿什么完全置于自己的意志支配之下,根据自己的意志决断,而不必以他者的意志为根据。
作为存在性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的思想缘起于古希腊哲学。可以说,苏格拉底以德尔斐神喻“认识你自己”为导引,打开了通过心灵的内在原则来推知外在世界的窗口。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以及对灵魂中理性、激情和欲望的区分,为我们描述了自由意志的意义图景。亚里士多德以“更爱真理”的态度审视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理念说,认为个别事物的存在是“第一实体”,从而使个体存在有了独立身份,这种思想为自由意志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而真正对“自由意志”的概念作出描述的是伊壁鸠鲁。伊壁鸠鲁认为,原子会脱离直线而偏斜,而且这种偏斜恰是原子更本原的性质。原子偏斜理论否认我们的世界是出于某个至善的目的而被制造的,这个世界拥有太多的缺陷,不可能是神圣的造化,它只能是原子偶然的、散漫的和徒然的运动碰巧达成的一种排列方式。自由的根据进入到原子的运动当中,自由意志被看成构成万物的第一因,它永远在自然因果律之外,且永远不进入因果律,自由意志的本体地位得以确立。伊壁鸠鲁曾经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对上帝的至善至能提出了质疑:“上帝或者希望消除所有的恶事而不能,或者他能而不愿意;或者,他既不愿意又不能;或者他既愿意也能。如果上帝愿意而不能的话,他是软弱——这与上帝的品格不符;如果上帝能而不愿意的话,他是恶毒——这同样与自由的品格相冲突;如果上帝既不愿意又不能的话,他就既恶毒也软弱,因此就不是上帝;如果上帝既愿意又能——这唯一符合上帝,那么,恶事到底从何而来?或者说,他为什么不拿开这些恶事?”(注:参见赵林著:《罪恶与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原罪”理论辨析》,《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伊壁鸠鲁的这个悖论成为奥古斯丁毕其一生所要解答的问题。
奥古斯丁从基督教教义出发,对罪与责的根据与来源进行了哲学意义的追问,开显出人的超验性存在即人的自由意志。在《论自由意志》中,奥古斯丁指出,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受蛇的引诱,偷吃了伊甸园善恶树上的果子,违反了天条,被上帝降罪并逐出伊甸园,于是有了人的“第一罪”,而这“第一罪”成了人类共同的“原罪”。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人被赐于了自由意志这种能力。人是按必须遵从上帝的旨意被造的,但同时人也被赋予了自由意志。上帝在造人时,也知道他会受诱惑,但是,由于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使他有能力经受住诱惑,能够对任何诱惑说“不”。事实上,人的自由意志既可能对诱惑说“不”,也可能选择接受诱惑。人的“偷食禁果”其实蕴涵着这样的意义:一是人不再听上帝的话了,人以自由的意志挑战了上帝的权威;二是人自己想成为上帝,想拥有像上帝一样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因为上帝造人时,虽然要求人必须服从上帝的意旨,但同时给人以自由意志,因而把人是否愿意服从上帝的权利交给了人自己,因此,上帝对人背弃天条的行为进行定罪,并施以惩罚才是有理由的、正义的。对“原罪说”的信仰和理解隐含着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觉悟,而这正是人的存在问题。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创造的一切事物都是善的,包括自由意志在内。上帝之所以把自由意志赐予人,是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就不可能正当地生活,就不可能超越自然事物所遵循的必然性而成为真正的人;人滥用自由意志来作恶错不在上帝,而在人本身。他把罪恶与自由意志联系起来,并且把自由意志提高到人之为人的根本。没有自由意志,人就不可能正当地生活,不可能超越一般自然物而成为万物的灵长。罪恶生于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
关于自由意志及其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康德可谓是集大成者。康德指出,“大自然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意志赐给了人类”(注:参见赵林著:《罪恶与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原罪”理论辨析》,《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自由(不受他人意志的束缚)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惟一的原始权利,是人的存在和本质的体现。康德所讲的自由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人具有的选择的能力,不为必然性所支配,能够在多种选择面前作出抉择,从而使人有了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意志有可能摆脱感性欲望的束缚,这是消极的自由;另一种是积极的自由,指的是意志的自律,即法则由自己制定并自觉的遵循。康德说:“有意选择行为的自由,在于它不受感官冲动或刺激的决定。这就形成自由意志的消极方面的概念。自由的积极方面的概念,则来自这样的事实:这种意志是纯粹理性实现自己的能力。但是,这只有当各种行为的准则服从一个能够付诸实现的普遍法则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注: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3页。)。积极的自由是遵守自己所立的普遍法则的自由即自律。意志的自律构成全部道德法则的唯一原理,也构成遵守这些法则的全部责任的根据。康德为人类的道德设立了三个基本的准则:“普遍立法”(只照你能意愿它成为普遍律令的那个准则去行动)、“人是目的”(无论是对自己或对别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决不只当作工具)、“意志自律”(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当作普通立法的意志,即自己为自己立法)。这三条道德律令的原理是同一的,它们从不同角度指向着一个中心——自由。道德律令作为普遍必然的绝对命令,主要规定的是道德律令的形式,是一种避免不公的方法,要每一个人都按其行事,它的本质是自由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谈的是道德律令的内容,要求承认他人与你同样有目的,要尊重他人的愿望和决定的权利,道德行为应为了帮助实现这些目的而行动,而不是仅把他人视为利用的工具,人作为理性的存在是自由的;意志自律则是自由的直接表现和高级形式,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真正的存在,是道德评价和道德责任的基石。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脱开了道德领域的一切经验欲望、感性因素,把自由作为本体理念提了出来,使其成为道德律令的先验基础。但是,自由并不只是与人无关的先验理性而已,它还实实在在地体现、展示在日常的道德事实之中,从而凸现出“自由”的尊严。因此,一方面,自由既是绝对命令的根源和依据,是道德律令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道德律令又是自由体现出来的途径,自由离开了道德就不能被人感受到。所以康德说:“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而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注:《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