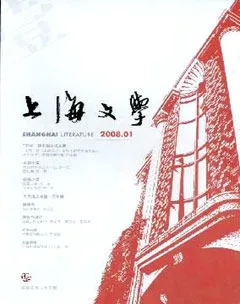辛西娅·卡特
1989年初的一个夜晚,美国南方。在我刚踏入这片陌生土地的第四天,一辆灰狗巴士载着我们寥寥几位乘客,从中部城市堪萨斯向南方腹地驶去。友人见我人生地不熟,极力挽留我在中部城市,但为了能保持学生身份,早日接家人来美团聚,我仍然踏上了南下的巴士。黑乎乎的夜,笼罩着黑黑的车厢。当时并不明白乘灰狗的多是穷人,作为新来的中国学生,买一张九十美元的巴士票要划算半天,乘一次灰狗,已算奢侈的了。车缓缓地颠簸,望着黑黝黝的窗外,时而一些不知名的小镇闪烁着昏黄的灯光一晃而过,我的心不由忐忑起来。那位白人司机哼哼着从未听过的地名,带着浓重的鼻音,车门吱地开了又关上。不知从哪站开始,上下的客人全是黑人!他们和她们的皮肤黝黑,略微肥胖的身躯从我座椅旁挤过,可以听见他们沉重的鼻息声。巴士载着美国黑人,在这无边的夜里,向遥远的南方疾驶!我只有把胸前背包再抱紧些,眼睛死死盯着窗外。透过窗子,我看见了父母苍老的面孔,女儿和丈夫期盼的眼睛。思念家人与对陌生国家的强烈反差交织在一起,不知不觉中,汗水与泪水湿透了面颊。
美国南方明媚的阳光下,美国黑人的家乡。
当车驶过田野,古老黑人灵歌的韵律时不时从耳边飘过:
轻轻摇摆,甜蜜的大篷车,
来把我带回家。
我遥望约旦河,我看见了它,
来把我带回家……
初次来到密西西比州的时候,看见如此广袤的蓝天白云,心头不由微微颤动。大片大片的棉花地顺着州际公路两旁无垠伸展,偶尔有一群黑人农工身着白衫在南方的烈日下劳作,恍惚间仿佛回到了《根》和《飘》的时代。农场主和奴隶的旧日纠葛已不复存在。但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州仍有不少早年遗留下来的农场,农场主祖上留下的老屋——好莱坞电影《飘》拍摄过的房子就是其中之一,老黑奴的年轻后代们,今天仍为生计奔波。
南方仍是那片热土。
学校有一次组织活动,开车去阿肯色州,不说黑夜,白天一路上经过的小镇和村庄都令人心寒。小镇的中心一概为陈旧的红砖房,少说有上百年历史。街道一律从主街(main street)开始,其他街巷第一、第二、第三街排后。没几家店是开着的,有的干脆用木板钉死,开着的铺面店门虚掩,有一两家烤肠热狗店、洗衣店和锁匠铺(black smith)。街心里,吱吱作响的烤肠和喷香的洋葱味在湿热的空气中充满诱惑。往往火车站设在镇中心,轨道旁常见一些破落的木屋,看上去已多年没有列车在此停留。唯有孩童们仍在炎炎烈日下嬉戏,偶尔有几位带着浅色礼帽在大热天穿着过时西装的黑人老绅士在街角溜达,给这些南方破落小镇带来一丝生气。镇头清一色的小教堂,有着油漆斑驳的木质大门,刷了白漆的钟楼顶部,十字架高高矗立,在星期天早晨,远远地就能听到它们清脆的钟声。
到了夜晚,校车穿过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交界处,不时穿过远离文明的黑人们集聚的小村庄,那里满是shotgun house(铁皮屋)(后来辛西娅·卡特给我解释得更清楚)。不知是缺电还是由于贫穷,年轻人个个聚集在门外,三五成群,有站有倚,像是在门外集会般度过没有空调机的难熬夏夜。车灯下看见老人们坐在门口的摇椅上,夜色里只见他们的眼睛闪闪,雪白的牙露出笑容,没有人为铁皮屋里缺少空调犯愁。当我们的车走近,人群安静下来,闪闪的眼睛注视着,尾随车远去。车从一群友善的黑人村民中穿过,不敢停留。周围没有任何其他市镇和建筑。不知别人感受如何,我的心可提到了嗓子眼。
南方小城镇的萧条和明媚的蓝天白云,给人的视觉反差是如此强烈!
每个人都知道,全美就业率最低的是密西西比州,其次是路易斯安那州。出于历史、政治、文化和种族的原因,没有大财团在那投资。穷黑人们实行了中国伟人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穷则思变。黑人的“革命”便是背井离乡,由南向北迁移,“跨过约旦河”寻找自由的乐土,到能改变命运的地方去。从南北战争时起,年复一年,迁徙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于是,喜讯又把更多的密西西比人带到了北方。
辛西娅·卡特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我的春卷呢?你给我做的春卷在哪里?”辛西娅把我堵在走道里,那是1994年我到芝加哥郊区一所学校上班的第二天。她高挑个头,黝黑肤色,健壮的体格显出她强烈的个性。她的头发高高挽起,当她把脸凑到我跟前,那浅棕色的眸子闪闪着。“替我做春卷了吗?”初次见面就这样问我,令我瞠目结舌。“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春卷也会……”我可不愿为不熟悉的同事做吃的,尽管美国同事已经把中国同事与中国美食连在一起。尤其美国黑人是一些家庭式中餐馆的常客,他们的最爱是价廉物美的脆皮春卷,和酱油色过浓的虾炒饭。“哼,可别忘了!……”她又说。
在美国每接受一份新工作就得打起精神,鼓足勇气去结识一批新同事。这一过程有时累过上班本身。学校坐落在芝加哥西郊,伊利诺伊州的杜佩郡,共和党及其支持者的伊州大本营,这儿居住着大量白人中产家庭。作为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富有的芝加哥西郊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所有有利因素。从杜佩郡驱车三十来分钟,可直达芝加哥市中心。在那儿工作的律师和大医院雇用的医生们,相当多住在西郊。每逢周末,朝市中心去的高速公路堵得水泄不通,郊区的男女老少们一律向东,到市中心的密西根湖畔去享受生活,去放游艇,或是去House of Blues(蓝调之家)听诺拉·琼丝和斯汀的音乐会。然而从美国南部贫穷州来的人们,大多集聚在芝加哥南端。他们不胜西郊的高昂房价,住在黑人区,却爱在郊区上班。连接市中心和西郊的艾森豪威尔高速是芝加哥利用率最高的路之一。每天的早晨和傍晚,富人们和穷人们在高速公路的两侧相向而驶,进城和出城两股反向的车流载着两种命运截然不同的人们。
我新任教的学校里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妇女担任教师助手,她们当然不属于郊区的部落。优越的福利,安全的杜佩郡环境,吸引她们长期保留这份工作。辛西娅·卡特遇见我时,她已在此任职十五年之久,是少有的住在郊区的黑人。我,一个只有三年美国教龄,凭着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准则,面对黑白混杂的张张笑脸,正走在学校走廊里。脑子如同雷达扫描仪一般,试图辨别“敌友”。
“嗨,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
“哈罗,您的名字和姓怎么这么简单?”
“哈罗,我的嫂子也是中国人,和我哥哥住在台湾……”
“小心!你看上去是个好人,小心人心叵测……”老教师凯伦给我一个拥抱时连带一个忠告。什么?有这么复杂么?
暑期后的学校,人事调动频繁,各种会议众多。芝加哥初秋一个闷热的夜晚,我正在聆听校长召开家长会的开场白,忽听窗外雷声隆隆,雨点重重地打在教室的窗上。时针正指着七点,倾盆大雨之间,似乎有其他异样的声音。
“不加工资,不签合同!”
“我们要,新合同!”“我们要,新工资!”喧嚣的人声激昂,声势就像是罢工的前兆。
不顾校长的尴尬脸色,家长们纷纷起身看着窗外。教师助手们穿着黄色雨衣,夜色里“工会”两字赫然醒目。她们一个个手举标语牌,冒雨在校门口示威!长胳膊长腿的辛西娅走在前头,雨衣快遮不住她身体,她领头喊,大伙应,她手中的标语牌舞动着,看上去十分有煽动力。校长的开场白不了了之,家长会不久就散了。当然第二天学校里愁云惨雾,会议室的门紧闭了一天。白人老师们窃窃私语,好几次向我确认昨夜的见闻。这下要辛西娅们的好看了,我想。可是微妙的事发生了,会议室的门砰地打开,辛西娅和她的伙伴们雀跃而出,欣喜的脸色向大家宣告:目的已达到。以辛西娅为首的教辅人员工会获胜。迫于家长们的压力,校方与她们签了新的加薪合同。这个刺儿头!难道这就是凯伦的忠告么?
不久我亲爱的老公拿到一个五百强公司offer回中国任职,也就是现在说的“海归”。同事们认为我也会搬回中国,于是我的两个助手都“跳槽”去了别的班,只剩下我和弗吉尼亚。在凯伦小姐班上的辛西娅自告奋勇来我班接替。老师们窃窃私语:辛西娅太难弄了。没人对付得了她,何况是中国老师!辛西娅去新老师那儿是别有用心,是占她的便宜。凯伦小姐同情地对我说:“可怜的你,可怜的你!”
但我别无选择,“可怜的我”必须接受她。
新老师,新助手,加上两个新来的难搞的学生,在我们这所特殊教育学校里,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我们班。长达近两百天的新学年开始了。黄色校车每天来接送我们去十六英里外的春木公立学校。我们必须在九点到达,赶上他们的课程。弗吉尼亚年龄略长些,口齿也不太清楚。她老把“我们”念成“偶们”,“孩子”念成“伢子”,最不能容忍的是她把ch发成sh,太可笑了,一个说不清英文的美国黑人!老弗吉尼亚抱怨太忙太累,新来的辛西娅从不。辛西娅来后,总是让孩子们在八点三十分都准备好了,坐在厅里等候校车。“我们来得及,我们快些,再快些孩子们!”她身上潜在的那种魅力——争强好胜和领导能力,在同伴和孩子们当中同样有吸引力。
按照我的要求,辛西娅根据她的理解把图片列成有趣的故事,让孩子们按图索骥。她把图片留出空白,让孩子们去拼成句子和片断,把象征性图片贴到教室各处,桌椅门窗上,让孩子们练习新字。不久,相比其他班大人们跟着孩子转,我们班渐渐形成大人掌握孩子的习惯,指导孩子进步的局面。教室里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很顺利。“你说,我们做。不要担心,我们都能生存的!”辛西娅对我说。为了避免成为“刺儿头帮”的嫌疑,我掩饰了自己的喜形于色。
辛西娅具有天生的教育者特质,她的耐心细致和对孩子们的爱,对当班老师的绝对服从令人折服。可能是刺儿头本性还未露脸吧?我想。别得意太早。不久校长来视察,对我班孩子们的独立性和行为上的进步感到吃惊。
“嘿嘿,你毕竟是硕士毕业的!”校长说。
消息就这么传了出去:辛西娅和新老师干得不错!每天放学,凯伦小姐总守候在走廊里给我一个诡异的微笑:
“你,今天过得如何?”
“还可以。”我说。
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了:
“喔,你有什么秘诀吗,镇住了她?你得让我知道。”
我没有秘诀。我只是工作和微笑。渐渐地,我感觉到辛西娅喜欢同我在一起工作。希望她不要太喜欢我!我不想成为“刺儿头帮”的一员!!但我暗暗庆幸:我的团队看上去不错!
“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是谁说的?”黄校车颠簸着,我手中的公民考试题落在地上。十六英里的路程成了我复习公民考试的机会。弗吉尼亚弯身替我捡起,“这你不知道?偶知道!是派屈克·亨利。”喔!
“偶们读过《美国政府》课程,从小学到高中,读过好几遍了!”
记得1992年我在弗吉尼亚州工作时,曾住在一个叫新港纽斯的小城,城里就有个叫派屈克·亨利的购物商城,还有以他命名的公园。但我早就忘了。
派屈克·亨利,1736年生,弗吉尼亚州汉诺瓦郡人。他曾是一位律师,爱国者。他带头向英国殖民者抗争,成为美国独立,自主自治奋斗路程的象征。他一生曾三次任弗吉尼亚州长,为该州服务三十年之久,生前他作过“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演讲。派屈克·亨利的故事和弗吉尼亚州是分不开了。但我万万没想到,眼前弗吉尼亚和辛西娅只有不高的文化,对象征美国自由的人物如此了解,争着告诉我谁是派屈克·亨利。这使我这个访问过威廉斯堡——美国弗吉尼亚州也是美国所有州的第一个首都——多次的硕士生,感到汗颜。“咳,老弗,辛西娅,你们令我刮目相看!”我说。
在美国,每年成千上万合法的非法的移民千方百计越过边境和海关,希望到这儿来实现他们的美国梦,成千上万的新移民迟早会通过公民考试,成为美国大家庭的一员。但是有多少人瞩目过美国黑人为自己的独立自由付出的血泪代价呢?有多少人记得美国作为国家为自身的独立自由做出的抗争与牺牲呢?
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交谈中渐渐知道了辛西娅的一些故事。
辛西娅出身在南方密西西比州一个农民家里,祖上是奴隶。不知从何时起,父亲梦想拥有自己的农场终于成了现实。他用尽毕生积蓄,盘了一个小农场,而孩子们从此遭了殃。雇不起工人,严厉的父亲把小小年纪的儿女们赶到地里干活。辛西娅儿时个头还没有奶牛高,便要下地干活。她牵着马赶着牛,喂牲口挤牛奶,什么都干。有牛有马的家庭是富人了。我说。不,那是仅有的一匹小马和一头瘦奶牛,父亲去市场用谷子换来的。为生计一家人在他带领下没日没夜地干,孩子们在南方的日头和黑土地之间渐渐消磨了他们的童年。辛西娅记得他们的shotgun house里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什么是shotgun house?那是南方常见的铁皮屋,光线差,很小,小到从这头开一枪便能穿透那边墙壁。家里没有任何玩具,哥哥用挂衣钩弯起做个“娃娃”,破布裹巴裹巴便是辛西娅的“芭比娃娃”。有时,辛西娅会跟着哥哥到村头铁轨旁捡煤核,一不小心火车疾驶过来带来一阵炎热的急风把她刮下路基,连滚带爬中划破了面颊……那种生活太苦了。父亲为什么这么逼你?我问。为了钱。她说。父亲始终没有得到他梦想的财富。劳累和汗水换来少得可怜的钱,养不活一家子,他只不过是个贪婪的破落小农场主。孩子们渐渐长大,一个个逃离了家门,到北方自谋生路。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农场的日子。”
辛西娅的浅棕色眼睛一亮。我告诉她我在高中毕业后,大学不得其门而入,不得不上山下乡去了农场。一去就是七年,人生最美丽的时光。
“怪不得!”她雀跃起来。“怪不得我看你做事有股猛劲,不像其他老师,她们往往是只动嘴不做事。”辛西娅问了一连串问题:“你们国家有黑人么?”……“那为什么你们要去农村?你也是奴隶吗?”……“不是的话为什么被迫去农村?既然你们都是同一肤色,同一种族,也没有农场主与奴隶,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发生?……”
最后,她自问自答得出了结论:“那就是集中营。政府把持不同政见者关进了劳动集中营。”
在1990年代的美国,一个中国人要把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解释给一个美国黑人听,竟然失败了。在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的国土,天总是蔚蓝,山总是青青,人们很难理解地球另一端的日子。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我们同样在地球的两端面朝黄土背朝天,度过了一段不符自己意愿的岁月。那是我们的一段黄金年月,随汗水抛洒在大自然里,再也不复返了。知道我的农场经历后,辛西娅对我是另眼相看。她见人就提我在农场待过,她的同伙们从此对我也是敬佩不已。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体会到“天下亚非拉人民是一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自豪。
1960年代的美国不像现在。辛西娅说。那时黑人白人不能乘同一辆巴士,不能在同一个游泳池游泳。是吗?我问。遇到的一些歧视的社区,黑人的儿童不能上白人孩子的学校。辛西娅亲身经历:在餐馆,由于她和朋友们的出现,坐在邻桌的白人顾客没用完餐就愤愤离去是常有的事。而白人老板也拒绝为她们提供用餐服务。在芝加哥辛西娅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她干过装卸工、流水线装配工、家庭看护。往往在应聘工作时,她的肤色成了最大的障碍。
在芝加哥城南的一个舞会上,当辛西娅遇见强尼时,她很年轻。强尼高大魁梧,浑身散发出青春的气息,他喜欢钓鱼、喝酒、赌牌、跳舞。侃侃而谈、举止风流的强尼马上博得了年轻辛西娅的芳心。很快他们有了女儿密斯蒂,辛西娅下定决心要让女儿离开黑人区,过上像样的日子。可是离开城市南部到郊区生活会改变强尼的生活方式,小伙子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更是没有兴趣。生命是短暂的,及时行乐为先!于是发生了争执。终于有一天辛西娅抱着密斯蒂离开了城南破旧的政府楼,搬进西郊一间价廉物美的公寓。单身妈妈的日子让她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从她认认真真地填写学校工作申请表的那一刻起,她觉得要在这郊区的学校里干一辈子,她要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密斯蒂在西郊长大成人。为了争取密斯蒂应有的生活资助,辛西娅千方百计盘算每一枚盘尼,和强尼争吵多次以至上过法庭。就这么吵吵闹闹,在每周一次父亲探望密斯蒂的周末之中,十五年一晃而过。
由于梦想改变命运,辛西娅读过一期律师助理训练班,成绩不错。但她始终没有登记第二期,也没报名律师助理资格考试。你能改变自己的前途,同伴们说。她却认为,她在人前说话有恐惧症,在公众面前,她准备得再好,头脑也是一片空白,有一次在演讲课上,她眨着浅棕色的眼睛把听众晾了一刻钟:
“我,我今天要说的,是,是……”
她不能替人上法庭说话。就这么陪着女儿又是几年,转眼快到了密斯蒂高中毕业的时候。
“为什么你的工资比我高?”如果不熟悉辛西娅,我会再一次被她问得张口结舌。
“问你自己呀,为什么不读硕士学位?”
“……”她哑然。“你们中国人都这么勤奋吗?我也勤奋,为什么我没有钱?”
“你有钱的,辛西娅,你有近二十年工龄,你的钱都哪儿去了?”
她的眼睛露出少有的黯然和忧伤。所有的艰难岁月从她眼神里流过。
“怪不得密斯蒂说你,把自己收拾收拾,去找个好丈夫,”我笑道,“找个能挣钱的丈夫……”
她的脸变得认真起来。“上帝会给我预备的,”她伸出细长的手指指了指天,“圣经上说了,会的……”
我垂下了眼帘。我觉得内疚。不是因为我有丈夫和学位,也不是因为我有个老师的职位,而是我这后来之人比辛西娅她们生于此长于斯的美国黑人生活得好。如果这不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那又是什么?机会在人人面前似乎均等,但有的人总是得不到属于她的星宿。然而,谁能说她不会在将来拥有人人都拥有的呢?在美国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每逢周末,芝加哥大街上真有过节的气氛。每到星期五下午两点半,连教室的空气都弥漫着周末的喜悦。如果是星期五加上发工资的日子,那学校的走廊上会像“集市”一般热闹。教师助手们都站在教室门口,天上地下地闲聊,互相询问晚上和周六的打算。无非是那些三姑六婆的派对,或去哪儿花掉这两周的工资。她们从不存钱。她们过着从paycheck(工资单)到paycheck的日子,何必为明天发愁呢。凯伦和另几位白人老师愤愤地从她们中间穿过,意思是提醒:还没到点下班呢!这情形,我真以为密西西比的小村庄搬来了芝加哥西郊。真的。她们和改不掉的习惯一起来到了北方。
“我二姨从杰克森维尔来,今晚我得去奥海欧机场接她!”老弗嚷嚷道。
“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