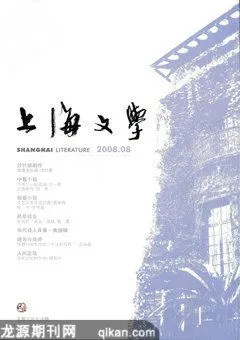永远的“孤岛”情结
生老病死事寻常,大喜深悲味最长,
最是人生龁处,是悲是喜费思量。
——柯灵(1996年)
一
柯灵先生离开我们忽忽已五年有余,每次想起这位尊敬的文坛前辈,必定会定格在《文汇月刊》二十年前一幅作为封面的照片上:背景可能就是他寓所面前的复兴西路,满地萧萧黄叶,柯灵先生披一件夹大衣,敛眉凝目,神情庄重,若有所思。这是我看到过人物肖像中最不易忘却、也是最好的一幅,好就好在它准确地表现老人晚年的心境,而又给人以深邃苍凉、余意不尽的美感。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半个月左右曾临时借住永福路上海电影厂文学部写稿,恰好柯灵先生在三楼长期借用一间写作室,他每天上午必定从附近寓所信步前来,避开一些上门的不速之客,到此处闭门写作。我偶尔上楼去看望时,他便娓娓讲述着手写《上海百年》巨著的打算,又担心可能来不及完成这部长篇,对不住上海。我劝老人不妨推辞一些不相干的访问、索序之类的应酬,以便集中精力和时间动笔,他微微苦笑,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有的推也推不掉,没有办法呀!”我知道,那些都是上海本地的作者或是有关上海的著作,他不便推辞或者推也推不掉的。老人几乎与世纪同龄,一生的大部分岁月都在黄浦滩头度过,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这座大都市的沧桑巨变,上海的百年风雨,数不清形形色色的人物,说不完光怪陆离的事件,在他都是如数家珍的。
关于上海,柯灵先生在本世纪初为《上海名人》一书作序题为《上海大梦》文中,有一段颇具华彩的文字:“一百五十年来,上海的传奇色彩,在世界名城中是独一无二的。五口通商,春申江畔一片沉睡的土地,蓦地一变,成为喧闹的十里洋场。鹊巢鸠占,喧宾夺主,从此华洋麇集,五方杂处,人口爆炸,形成一个世无其匹的生活大舞台,卜日卜夜,演绎各种大悲大喜,又悲又喜的戏剧,文戏武戏,正剧闹剧。‘三言二拍’无此惊奇,‘莎氏乐府’逊其烂漫。而角色之繁复,人品之杂,生旦净丑不足范其型,三教九流不克尽其性。司马迁之无韵离骚,难以传神摄髓;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不能完全概括。一部洋洋洒洒的二十五史,不可胜数的稗官野史,未见有如此大开大阖,诡谲多变的神话世界。抗战八年,上海和祖国大地一起经受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暴敌入侵的磨炼,抗争之激烈和勇猛,鲜明地表现出上海性格的闪光。上海沦陷,在最野蛮的敌军武力统治下,也能维持其畸形繁荣,人口密度有增无减。四五十年前,历史翻开新页,‘天翻地覆慨而慷’,上海人惊喜若狂,却依然没有改变其祸福休咎、悲欢离合不能自主的戏剧式命运,直到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出现改革开放的境。现在上海的繁华,已经远远超过旧时形容洋场风光的‘火树银花,城开不夜’,只是精神领域,在卷天席地的商潮冲击下,沉渣泛起,在许多场合,反而显得更加张扬无稽了。”
柯灵先生大手笔,只用短短四百字,就对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年来上海的历史作了准确而生动的概括,也体现他对百年上海真挚而深切的情怀和殷切的期望。他曾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最熟悉而且难以忘怀的,是30年代和抗战初期到沦陷时期的上海,特别是“孤岛”四年(1937年11月12日到1941年12月8日),他总是时刻萦怀,有永远丢不开的“孤岛”情结。
二
世纪之交,上海几位朋友积极筹划出版一套《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注] 得到上海书店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个打算,很符合许多40年代在上海的文学爱好者以及像我这样在“孤岛”时期开始接触文学的人的心愿。我有幸参加编务,分担编两本中篇小说。第一次聚会时,大家不约而同建议请柯灵先生担任这套系列的名誉主编,请他写总序。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不二人选,因为他对上海40年代尤其是“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最熟悉、最钟情,患难与共、生死以之。
柯灵先生当时已届九十高龄,而且多年卧病,但是仍然慨然应允,可惜编辑工作积极进行时,老人竟驾鹤西行,未能写总序。最后只好由编委之一沈寂兄根据柯灵先生生前几次口述意见,记录整理成卷头语:
编选《上海40年代文学作品系列》这套丛书很有意义,也很需要。人们对上海40年代的文学创作缺少应有的重视。这套系列的出版可以弥补中国文学史的一段空白。
(1999年9月8日)
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界,情况非常复杂,然作家阵容泾渭分明。文化汉奸和附逆文人鼓吹“大东亚和平共荣”,而有民族气节,坚持爱国立场的新老作家,置生死于不顾,千方百计,发表揭露罪恶,反抗强暴的作品。
(1999年12月27日)
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反映40年代现实生活,也可以有借古喻今的历史故事;作品不拘风格,一定要具有较高的文字水平。要以上海为背景,也可以扩至其他地域。尤其是上海胜利后,内地作家来沪,他们的作品背景和题材更广泛,足以反映全国人民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抗。
(2000年3月14日)
“系列”要做到“作家多,作品好”。让人们知道40年代的上海有广大的作家阵容,也发表了许多有积极意义和写作水平很高的优秀作品,是无愧于时代的文学宝地。这也是编纂这套“系列”的意义和目的。
(2000年4月3日)
这只是柯灵先生对编辑《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这套丛书的意见。从50年代到90年代,他写了许多有关上海“孤岛”时期和40年代文学的评论,介绍、回忆和序跋,对“孤岛”时代的文学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我们几个人正是本着老人的指点,认真地阅读和挑选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兢兢业业地从事这项“弥补中国文学史上一段空白”的工程。那段时期,大家好像都返回到上个世纪40年代,回到那个极不寻常而又极为难忘的岁月。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开始练笔学步,蹒跚地走进文学园地的年代。参与编务的好几位朋友当年都先先后后、程度不同地受到柯灵先生的关怀和扶持。饮水思源,他们总难忘培育之恩。使大家哀伤不已的是:2000年4月这套系列问世之时,柯灵先生未及看到,他已经驾鹤西行了。
我自己虽然中学时代就读过柯灵先生的散文集《望春草》,喜爱他主编的后期《万象》,每期必读,但是还是个高中学生,只能向报纸副刊投寄些短稿,却拿不出有分量的作品去尝试闯一闯《万象》主编的门,尽管我知道它就在福州路永祥印书馆旁边的弄堂里。有缘“识荆”已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初,那时柯灵先生与唐弢先生一起主编进步的时事综合周刊《周报》。我第一次去拜访,并非作为文学青年去拜见前辈,而是手持我们大学老师当时被誉为“民主教授”的林汉达先生的一封介绍信,送一份稿件给《周报》的。他们二位当时正同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诸位先生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高潮的到来奔走呼号,此后接触并不多。直到上海解放,尤其我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以后,才有幸经常向他请教,同一些熟朋友一样称他“高先生”。报纸副刊上需要哪方面的稿件,去信约请,一般都不会被拒绝。一时有事不能执笔,也必定来信委婉说明,诚挚谦逊的态度和严整清秀的手简,常使我们年轻的编辑引为美谈。
同柯灵先生接触更多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80年代中那些年我去上海,总要去看望巴金和柯灵两位老人,问候起居,他们住处也相近。柯灵先生每年来北京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有时也去他的住处相晤,谈谈北京和上海文坛近事,他总垂询我写作情况,多所鼓励。1987年初我离开工作岗位时,曾向许多熟识的师友和同行发信禀告,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热诚帮助。几天后即收到柯灵先生回信:
得离休讯,欣然,亦复惘然。欣然者,肩仔一轻,佳作可待,对作家来说,闲裕的时间是很可贵的,告别繁剧,是一大好事。惘然者,多年与《人民日报》文艺栏打交道,未免有些去思,亦不无岁月催人之 慨也。
近日小恙,一池春水吹皱,亦颇感徒乱人意。聊泐数行,遥祝
新岁百吉,身健笔健!
捧读手书,怅然好久,前辈的关怀和鼓舞,自然衷心铭感。“一池春水吹皱”句,对当时春寒料峭,“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时局感慨良深,也道出许多人共同感到“徒乱人意”的惶惑而忧虑的心情。90年代中,传来老人摒除杂务,着手从事《上海百年》的鸿文巨著的消息,曾为之雀跃。大半生在上海浮沉,哀乐荣辱与共,写百年上海,可以说“非公莫属”。可惜老人年事渐高,体质日衰,不再有十几年前那样的精神和体力,更无复40年代那种身处荆棘丛中仍能从容应付的韧性,终于未及全部写成,留下了千古遗憾。
三
柯灵先生去世后,我在上海报纸上拜读徐开垒、何为二位老友的悼念文章,他们都是六十年前“孤岛”年代在柯灵先生提携下起步文坛,感情自然更加深切。回溯上海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时期的文学,必定离不开柯灵的名字。在那一面是荒淫无耻、残酷迫害,一面是严肃工作、默默献身的年代中,他编辑的报纸副刊和杂志上,从《文汇报》的《世纪风》、《大美报》的《浅草》、《正言报》的《草原》到上海完全沦陷后的《万象》,在硝烟和屠刀闪光中,冒着生命危险,苦心经营,守卫一方净土,保持一点正气,给读者送去清新健康的精神食粮,同时又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文坛新人。为此遭到敌人迫害,一度身陷缧绁,但是他安之若素,在腥风血雨中保持一个爱国文人的气节和良心。“孤岛”四年岁月,在他九十年生命中仅仅是短短的一段,却是最不平凡最堪追忆回味的一段。近二十年来,他对“孤岛”时期文学的回忆著述,对“孤岛”时期文献史料的关注,费耗了许多心血。他在《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一书“小引”中说过:“思想领域没有真空,感情领域没有真空,人民的心没有真空,表达人民心声的文学也没有真空。因此盛世有文学,衰世有文学,甚至在外国的侵凌和统治下也有文学。”从《孤岛风云》、《魔鬼的天堂》、《晦明》、《浮尘》和《记郑定文》、《爱俪园的噩梦》、《遥寄张爱玲》那许多文章中,都能体会到他当时的艰难处境和苦涩心思。1985年4月曾寄来一信:
阿英同志在“孤岛”时期所编《文献》,最近在上海书店影印出版。因为该刊刊行,正当国共合作抗战初期,除了大量党内文献,还有蒋介石的文告之类,书店责成我作一前言,向读者稍作诠释,并表示希望在《人民日报》一刊,藉收荫护之效。兹随函寄呈审读,不知可行否?今年是抗战胜利四十年纪念,又正当鼓吹国共三次合作之际,或不至不合时宜吧。
当年北京东路、河南路口有一座古旧的通易信托公司大楼,楼上有一层是上海政法大学新办的新闻专修科,讲课的多是地下共产党员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阿英是主持人之一,毕业的学员,后来不少成为新四军干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就是阿英手创的风雨书屋,不但编辑期刊《文献》,还印行和保存了珍贵的革命史料。正如柯灵所写:“风雨如磐,起惊雷于无声,唱荒鸡于寒夜,这地下室里惨淡经营的,就是这艰难的千秋事业。”《文献》只出了八期,就被迫停刊。但是它刊登1938~1939年间抗日战争的概况、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群众运动及至国际风云、敌伪动静、沦陷区百态的许多材料,包罗万象,特别是用大量篇幅,刊载重要的抗战文献,既有毛泽东的重要言论,也有蒋介石的皇皇文告。这种做法,在当时租界当局禁止明目张胆宣传抗日的“孤岛”上,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80年代初,上海书店决定原样复印《文献》,请柯灵先生作些背景说明,他为此写了一篇《赘言》,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惊涛骇浪的世局,已成过眼云烟,但前因后果,互相牵连,秦时明月,汉室江山,吴宫花草,晋代衣冠,渺远的过去,都在炎黄子孙的血管里一脉相沿,因为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条永远剪不断的链环,史迹可贵,文献是珍,其故正在于此。
可惜,这篇言近旨远、语重心长的《赘言》当时因故未能在报上发表,有负柯老期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柯灵散文精编》中,收有《赘言》全文,喜爱柯灵散文的朋友可以从中领略他那一份浓郁的“孤岛”情。
柯灵先生在《望春草》前记中说:“……在这样的时代,我也还只能在‘孤岛’上平凡猥琐地活着,说来又岂止惶愧!但对于人世,我也有欢喜,也有悲愁,也有激动和愤怒;因此有时也不免漏下一声赞叹,一丝感喟,我是一下低弱的叫喊,而多数却像舟人之夜歌,信口吹来,随风逝去,目的只为破除行程的寂寞。”实际上,就从那时期开始,他已经自觉地成为“孤岛”年代文化艺术战壕中一名坚强搏击的战士。在他的前面和同时,有郑振铎、胡愈之、陈望道、韦慤、巴金、阿英、许广平、张志让、王任叔、于伶、梅益、林淡秋、姜椿芳、唐弢等一大批师长和朋友,包括近日去世、当时还是青年俊彦的王元化,都坚守在教育、报纸、杂志、话剧、电影等等不同的岗位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强暴邪恶的势力进行坚忍不拔而又灵活巧妙的战斗,在暗雾迷茫、狐鼠横行的荆棘丛中默守岗位,埋头苦干,响起号角,带来曙光。他们的战绩值得后人永远记住。
[注]《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共八集:中篇小说集《投机家》、《虹桥》,短篇小说集《喜事》、《一吻》、《迷楼》、《团圆》,纪实文学集《新生》,散文集《长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