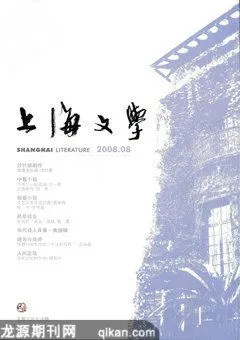活在记忆的个体
有樱桃枝摇荡的泥窗
凌晨梦见老屋。我十三岁之前的睡房。靠东墙剁顶上那一排泥窗。保留着树皮的吱呀的后门。猪草的青汁浸在泥地的痕迹。一摇晃就扑落灰尘的蚊帐。从蚊帐上落下的竹叶、苍蝇、长脚蚊、蜘蛛。透过蚊帐隐约看见去安源的毛主席,他握着把油伞。但睡在蚊帐里的不再是那个青春期刚刚到来的孩子,而是现在的我,且不只我一人,还有妻。我指着那些泥窗告诉妻,它们就是我多次在文章里写到的泥窗。那一排泥窗让我与那个孩子重逢。七个还是九个?已经不记得,但一定是单数。从识数以来我差不多每天都要睡在蚊帐里数它们。从每个泥窗里透进的光并不一样。有的白有的红,有的绿。绿的是樱桃叶映衬的。在每个泥窗里看见的东西也不一样。有的是天空的湛蓝,有的是隔壁林犬家屋上的瓦,有的是从林犬家伸过来的白樱桃,有的是火鸟栖在枯枝上。我们把火鸟叫火拐子。我不知道它是否就是父亲时常说的铁连枷。“铁连枷落到茅坑里,周身都火巴(pa,平声了就嘴壳子硬。”父亲总是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特别是形容大哥和二哥。我把泥窗指给妻的时候清楚地看见泥窗四周的木片和绷在木片上的蛛丝。它们不再是幻象或者假托,也不再是语言及其意义,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自从十三岁离家去县城读书之后,我便没有感觉过自己离泥窗是这样的近,打量泥窗的眼睛也不是三十年之后现在的我的眼睛,而是那个刚刚有过一次梦遗的少年的眼睛。
整栋房子里再没有别人,或者都在沉睡。外婆不像记忆中的外婆,大开着后门从还是黑暗的早晨抱了梢子柴进来,或者在灶房制造出咚咚的声音,或者在我床头的木柜里撮米面。在迷迷糊糊的睡梦里或者在无边的意想里,我依然能感觉到那些米粒下锅前的焦灼。外婆一定是去了菜园子。像我记忆中的每一个夜晚那样,昨天夜里她同样睡得很晚。我们床前砍碎的猪草已经撮走,留下一块青痕。我没有问妻昨夜睡前是否外婆有讲故事。可以说,外婆的故事哺育了我童年的全部想像。那些想像不只来自故事里送灯台的赵巧、长尾巴的吃人婆、要啥长啥的夜明珠、几口喝干整条灌县河的逆龙,也来自外婆砍猪草的响声、猪草的气味、外婆偶尔打盹出现的寂寞。那些被撮去倒进铁锅的猪草里包括了苦麻菜、锯锯藤、水麻叶、狗儿望、车前子、蒲公英、鹅卵草、水葵花,等等等等,有时候也包括了劐麻。我们是不敢碰劐麻的,碰到哪里哪里就起连浆大疱,外婆总是徒手抓了劐麻砍,我一直都觉得神奇。梦里想起,我是很爱这些草本植物的,有时候它们还带着朝露;有时候也带着螺丝和蝉蜕。它们的气味是各种各样的,苦味的居多。现在想来,在这些草本植物的苦味和外婆的故事里睡去,感觉一定是相当美妙的——一种复杂的美妙。也只有现在想来,且借了梦境的烘托。
父亲终究没有出现,但他确乎又有从我的床头经过。他的脚步带动的风,他的尚未扣好钮子的衣裳弄出的习习声,在我的肌肤上久久不散。父亲在厅房有过几次咳嗽,在前院又有过几次。从泥窗可以看天已蒙蒙亮,且渐渐听见了雨声。“啥子鬼天,一大早就下雨。”外婆回来了,站在屋檐下抱怨天气。雨突然下大了,屋檐水淌在檐沟的声音很清晰。我似乎已经看见屋檐水在檐沟溅起的白沫,由落点向四周扩散,一个一个破灭。我又看见那个少年,比十三岁还要小,揉着睡眼跌跌撞撞从屋子里走出去,不敢睁眼看天光;光着身子站在阶沿上,握住小鸡鸡朝着雨里撒尿,远了近了近了远了,撒出的尿形成的泡沫盖过了屋檐水制造的白沫。前面隔着院坝是竹林,竹林背后是石墙,墙里是樱桃树。雨声不嘈杂,没掩盖住不远处河水的轰鸣。
梦醒之后挥之不去的就是那排泥窗,那间睡房,那栋老屋。1986年清明,外婆在老屋病故。1988年春节,二哥家修新房拆除了老屋。记得去水田河吃老何的酒回来,老屋已经不存,二哥带了人正在往老屋基上灌水泥浆。有关老屋的最后一点记忆像是带了老朱回家,在大哥家的厨房吃搅团,现年二十一岁的侄女君不满一岁,被绑在一把木椅上。大哥家的厨房正是我往日的睡房。当时我一点没留意,还有厅房神龛上那些奖状。我只好在《老屋》借了虚构完成对它们的清理与收藏。最大的遗憾是,老屋没留下一张照片。
受惊的李子
除开记忆,没有人可以回到城湾里的那条小河。从石牌坊凹下去的碎石公路,公路两边凹得更厉害的沙地,呈现给我的总是跳着觅食的乌鸦和一笼笼的巴茅草。1975年——我相信它的某些神经(抑或根须)依然与我们今天相连——初夏,巴茅草已经茂盛得像一座座王国,乌鸦换成了喜鹊。河床不断下切,直至改道,连时间自己也无法修复那些水毁的创面。我把背篼凳在公路边的石头上,抹着满头的汗。公路靠河一边的桉树哗哗翻着白肚的叶子,我突然感觉凉意由脊背生起。“前面在枪毙人,戒严了。”前面的人传话过来,后面的人再原话传递到后面的后面。我眼巴巴朝城湾里看的时候,也不忘一只手掌着背篼。背篼里满背的李子,扑着层雪白的霜。以后——进城念书,即或进城上班,我再没有见到过那个手持铁皮喇叭、声嘶力竭叫喊的人。他是个警察,胖,戴了大盖帽更显胖,脸盘子和腰身。他从一辆敞篷车上跳下来,捡起掉在地上的大盖帽,戴上之前还吹了吹上面的灰。人山已经把公路轧断了。好多车正被大盖帽吆喝着往后倒。汽车欺负拖拉机,拖拉机欺负板板车;只有自行车欺负不到,一溜烟钻进了人缝。拖拉机倒退起来很吃力,大盖帽偌大一张脸都被它吐出的柴油烟子熏花了。
自从父亲挤到前面去看稀奇,我的另一只手便也没了空闲——为他掌背篼。我吃完了第七个李子,正拿了第八个用大拇指揩着上面的白霜。“你不能再吃了,再吃,等会上了街还卖球的钱!”父亲说话的时候甩了甩他的长头发,有几滴碎汗飞到了我的脸上。我的眼睛一直跟着父亲走上前,挤进人山,一刻也不曾离开。父亲的背影停留在了大盖帽的面前,接下来的找烟、点烟、说话也全都是背影。父亲的背影一直停留在大盖帽面前,我的眼睛慢慢开始发涩,慢慢开始流泪。父亲的背影在慢慢虚化,但余光里小河的流水却一直是畅快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欢乐的,它们在滩头飞溅的浪花洁白如雪,以至于游弋进灌木丛都还是洁白如雪。什么时候我身后的路上也是人山人海了,有汽车乱按喇叭,有拖拉机没有熄火——我这样本能地一回头,便把跟了大半天的父亲的背影跟丢了,等再去寻觅,不仅父亲的背影没了,连大盖帽也没了,但还听得见他的铁皮喇叭传出的吆喝。
没多久,我的手就发酸了,特别是帮父亲掌背篼的那只。我试着让手离开背篼。仅仅一次,就成功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又试着去摇了摇背篼,这才安心地吃起李子。也不是饿,也不是渴,只是无聊。一个,两个,三个……有父亲背篼里的,有我自己背篼里的。吃之前,还是习惯性地拿大拇指揩掉面上的白霜。那只是一层视觉的白霜,揩过什么也没有——李子上,大拇指上。我把吃过的核全扔进了公路对面的草丛。有一颗没有扔进去,它躺在桉树下的一条黄泥车辙里,让我隐隐不安;想过去捡了扔远,却脱不开手。
刚才都还是阴阴天,突然太阳就出来了,抬头望,阳光乍泻,一条湛蓝的河流深不见底,两岸的白云正在风涌扩散。“砰,砰,砰……”我不记得到底响过几枪,时至今日也不记得,甚至不记得那天的阳光乍泻是在枪响之前还是之后。枪一响,父亲的背篼倒了,李子全倒在了路上,一直淌一直淌,碰着密密麻麻的脚和车轮也不停下。
人散尽,我们的李子全部现了出来,包括被踩烂、被碾烂的,包括先前隐藏在草丛的。依旧阳光乍泻,从天上泻到地上,泻到地上的白碎石上。白光蒙蔽不了我的眼睛——把幸存的李子一个个捡起来,却再也看不见它们身上的白霜。
走在突然清静下来的马路上,刚挨过父亲耳光的脸马上又感觉到了恐惧。像一队队小虫子,脚脚爪爪都蹬着我肉里看不见的神经。还有某个看不见的地带的下陷与开裂,本来是原油一般的黏稠与焦黑,呈现出来却又是阳光乍泻般地明亮。乌鸦看见小河对面的草滩上无人,便从核桃树上飞过去,栖在刚刚被枪毙的人身上。从这具跳到那具,啄两嘴,再跳。我跟着父亲走过去,恐惧由小虫子变成了蛇和蟾蜍。草滩的草青翠,尤其是那些从石缝长出的,一棵棵,青翠里还带点鹅黄,居然还有没被枪声惊落的露珠。我不敢想像子弹穿过死刑犯颅骨的一瞬间,不敢想像那一瞬间青草和青草上的露珠的反应。“大惊失色”,我想它是一个不错的词语,至少对于那些李子是不错的。不远处,有人拿了馒头在蘸脑髓吃。乌鸦腾起来,又落下,不再怕人。父亲在解死人身上的麻绳。“让开让开,你们还要不要我们来给这些死鬼收尸?”有人推了板板车过来,朝吃脑髓馒头的人喊道。
起风了,天阴了片刻,接着又是阳光乍泻,只是乍泻的阳光已经与平常不同,像是被过滤掉了色素,照着什么都是黑白。为了躲风,我抱头蹲下;就是这一蹲,让我看见了每一棵草的呼吸——非常紧张的呼吸。不再是青翠,全是黑白。露珠下垂,但还没有突破最后的张力。
三十年,甚至不到三十年,活生生的东西都化成了虚无,城湾、小河、草滩,不要说那些被全自动步枪勾销掉名字的人。在回忆里,都如当年雪白的李霜,仅仅有一种虚柔的美,都是极为容易被时间的大拇指抹掉的。
亲爱的化学线
化学线。我们都这样叫那些洪水过后缠在灌木上的鱼线。乳白色的,不粗不细,牢实。我总觉得那种乳白是会滴淌的,特别在潮湿的阴雨天。对岸的山有一大半都溶在雾里。我们平常钓鱼用的都是麻线,大人织柴网用的那种,太粗。其实就是麻绳。把鱼钩直接绑在麻线上也能钓到鱼,但总觉得没面子,背名无实钓鱼,鱼竿上却没有一截化学线。我请婆婆帮我搓一点细麻线,且婆婆已经答应了,可是父亲晓得了,不准。我们看见洪水过后缠在灌木上的化学线,一抹一抹,一团一团。我们兴奋不已,估算着那些化学线的长度——横起拉足够拉过河,甚至拉拢道角生产队的晒坝,竖起拉足够拉拢锅坨漩。可是,谁知道呢?化学线还是一团一团的,在被洪水摧倒伏的灌木丛,沾着腐朽的树叶和泥沙,到底有多长,要等解开了才晓得。我从来没有解开过整团的化学线,也不记得有人解开过。但那些化学线真的好,乳白色的,不粗不细,绑在竹竿上钓鱼一定非常好,不只是牢实,也有面子,尤其用在车杆上,往外一甩,线盘哗啦直转,化学线哗哗直淌,没完没了。缠成一团的化学线看起来很简单,就几个结,可真要动手解,怎么也解不开。就是解开一两个结也没用。我们几个人坐在石头上,一人怀里抱着一团化学线,边解边打着腿杆上的黑么子。解不开化学线——亲爱的化学线——本来就烦,黑么子还要来烦,我们出手自然凶。一巴掌下去,除了看见无数的黑点红点,还看见五根指拇的印子。“解开了不?”旁边的人问我,我不回答他。刚刚找到一个头绪,叫他这么一问,又没了。“难球得解了,黑么子把老子腿杆咬得尽是包。”有人站起来,把化学线扔在面前跑得飞快的水里。“我要解,我就喜欢化学线。”我说,“解不开还可以带回去解。”有人为了证实化学线的牢实程度,用刀子割了一截下来,把两端分别缠在两只手的指拇上使劲拉,化学线深深地勒进了肉里,血浸了 出来。
我每年都有几个时候梦见一个孩子坐在石头上在解化学线。注意,我是进了县城读初中之后才把“解”读成“jie”的,之前一直读“gai”。那个孩子是我,又不是我。他爱那些化学线,乳白色的,不粗不细,像他后来见过的琴弦。但总是解不开,一次也不曾解开过。那些化学线于他,已经不再是鱼线了。梦境里总是洪水退却过后的景象,朝着一个方向倒伏的灌木很是抒情,还有挂在它们身上的柴草、布片、草帽、拖鞋……像五线谱里夸张的音符,除了靠形象抒情也靠站位。那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的愿望就解开一团化学线,而且是灌木丛里最大的一团化学线,然后把它们拉伸,一直拉伸,拉过河或者是拉拢锅坨漩。那些化学线摸起来其实是温润的,不像摸石头摸铁那样冰冷,当然也不像摸太阳晒过的石头或铁那样滚烫。我爱那些化学线,也许就是爱它们的乳白与温润;它们的乳白与温润背后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只是十一二岁的我还无法洞见。我先是坐在水边的石头上解化学线,慢慢地就坐在了我们家老屋的屋檐下。在下雨。屋檐水拉得很伸,也飞溅了些出来,溅在我手上、我怀里的化学线上。我依旧一个结也没有解开,但我并不失望。即使连头绪也没有找到。照说,一团化学线只该有两个头绪,但我却发现了好几个。头绪多,便意味着是断头,解开了,也是一小截一小截的。雨水把黑么子也赶到了屋檐下,它们叮上了我的脚板心。它们每吸一口血,我都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一小口也能感觉到。我感觉舒服。雨时大时小,与村庄以及村庄里的树木竹子联手演奏着交响曲,屋檐水拉伸是调子。石墙外不远处的河流是变奏。我喜欢一巴掌下去,腿肚子或大胯上尽是黑点红点,有五根指拇印子最好。可是,我的巴掌怎么能自如地打到自己的脚板心?在梦里,我清楚地感觉到做一个孩子的局限性。无人可以求助。外婆在做她的针线,已经从门槛外面退到门槛里面,她的针线篓被飘飘雨打湿了,她戴在无名指上的银顶针在午后的雨天显得格外暗淡。我们叫外婆的针线篓片篼子。片篼子,它在梦中出现时很干燥,一块块布头,灰黑的居多,也有花花绿绿的,上面压着把剪刀。很多时候,剪刀看上去都是铁青的,侧着看才有些微的反光。早先吸引我的不是剪刀,也不是花花绿绿的布头,而是一本老书——它根本就不能叫书,一片一搭的,而且字如斗大——里面夹着外婆做好的鞋样。每每外婆说它是书的时候,我都会狂笑。是书,怎么没几个字我认得?我背着外婆翻过,也摸过、闻过,纸张粗糙得很,没有特别的气味。谁会是这本书的学生,和先生?我真是愚蠢,现在才晓得提这样的问题——已经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了。
我们都晓得那些在灌木上缠成一团的化学线是从哪里来的。挂鱼子,听说过吗?我可是亲眼见过,在挑水路,在菜包石和锅坨漩。1973年,或者更早一点,我端了碗在河坝里跑,撵着看挂鱼子,把碗打碎在了乱石窖,干脆把筷子也扔了,回家问起碗到哪里去了,“我根本就没有端碗”,我回答得理直气壮。偶尔也梦见他,那个端了碗在水边奔跑的男孩,水边是乱石窖,他摔倒的时候把碗扔得老远。水里有他奔跑的影子,也有他摔倒的影子。挂鱼子总是在跑,在跑,不像钓鱼子放好线就一直等着,点一支烟,定眼看着一架架从河中间飘过的筏子。挂鱼子除了跑就是放线和收线,站在水中的大石头上,每收一手线,鱼竿就弯曲一次,弧度大得很。挂鱼子背着军挎,军挎一直在滴水。放线收线之外,就是换线。挂鱼最费线,不是鱼钩挂住了沉柴、浮柴什么的,就是鱼线卡在了石缝。特别是在滩头,而滩头恰恰是挂鱼子最钟情的水域——都说鱼爱往滩头跑啊。阳光从锅坨漩上面的障子岩照过来,从我们家菜园子看下去,站在水边的挂鱼子像是风景画里的人。空气潮湿,山河和人的轮廓都颇有浸润感。显然是水彩画。
在梦里,我看见到处都是化学线。洪水过后的景象。太阳已经转到了陶家山。远处的菜包石现了出来。河水由浑黄变成了褐黑,太阳的反光也是褐黑的。从笼嘴子到三杨盖,每一笼灌木上都缠着化学线,石缝里也是,水捞柴堆里也是,还带了鱼钩,且都在三颗以上。只可惜是挂鱼钩啊,没有倒须,不能用来钓鱼。一点不稀罕。挂鱼钩的形状矮胖,竖弯钩开离,让我想到毛主席的“毛”。三十年过去了,三十五年过去了,那些化学线又从灌木丛和石头缝里现出来,缠住那个男孩,让他憋气,也让他不失希望。男孩已经从水边回到了屋檐下,完全沉浸在解化学线这一行为中。这一行为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自我完成。雨还在下。屋檐水开始滴答。外婆收拾了片篼子,进屋了。匀净的雨水越来越像是一张外婆烫的薄面饼,因为缺油而显得过于苍白。我已经解开了第六个结,解开的化学线拖在地上,看起来已经有很长。我怕它们再打结,每完成一个步骤,都要重新理顺一遍。外婆端了筲箕从河坝里回来了。屋子里渐渐变黑。外婆点了油灯开始和面。天说黑就黑了。化学线只剩最后一个结了,可是我已经看不见。如果我动作稍微麻利一点,或者运气稍微好一点,我是完全可以在天黑之前结开整团化学线的,我兴许会大吼一声,像上山背柴扎拐那样,相当地释放。我在梦里体会到的不是想像的兴奋,而是疲惫,极度地疲惫。一个迷路的人穿过整片森林找到了路,或者是穿过沙漠找到了绿洲。自我完成之后,剩下的便是昏迷,还有托付。
想不起脸的使牛人
村里的最后一个使牛人死去之后,我开始思考是否用文字记下他们。倘若不记下,他们死掉就死掉了,像是从未有过。午后百无聊赖,钻进被窝读格拉斯的《剥洋葱》,不知什么时候将书丢在一边,爬上了老家的后山。青杠林正是四月的青翠,羊肠小路变成了石梯子,且有了千回百转。从老槽门往回走,总是睁不开眼,一路上有人招呼,没看清一张脸。跟一位使牛人的鞭声走,走丢了,又跟一位割草女的脚步走。睁不开眼,很可能是因为格拉斯的洋葱味在被窝里扩散不出去。与书评恰恰相反,格拉斯的洋葱味没有变淡,越是往后越是变得浓稠。像所有被困之梦一样,我依旧只有通过上天赐予我的醒来走出困境。那一条条变换的林中小道,多么像古宅雨天或傍晚的回廊。我不知道这个午后由格拉斯的回忆录演变的梦意味着什么,我感觉它非常像1944年的那条从但泽通往柏林的路,我甚至看见在路边刚刚萌芽的草丛里苏醒的小蛇。
现在,无论如何努力去回忆使牛人的脸都回忆不起,使牛人像是压根就没有过脸。可记忆告诉我,我见过使牛人,见过他们的脸,曾经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好比村子里那些石墙。我试过几遍,我还能哼他们使牛的歌,虽然没本事像他们站在老槽门的西风中一手扶犁一手使牛把嗓子扯圆。使牛歌脱离他们的胸腔和口腔后,还像个独立的活物,游弋在桅杆坪的上空。
使牛人的形象一直都是鲜明的,披蓑衣、戴斗笠、握长鞭、穿边耳子草鞋,不管是在旧时的雨季,还是在我而今的回忆里。雨水从斗笠上滴下来,再从蓑衣上滴下来。有时是淌。好几根脚趾从草鞋里挤出来,沾了泥水,看上去就非常滑腻。边耳子草鞋是用车轮橡胶做的,残留着石器时代的大刀阔斧。
有一位特别的使牛人,一把手,自然是有手扶犁无手握鞭;不用鞭使牛,牛却格外听话,像是晓得他的淫威。这个一把手的使牛人有淫威也有风情,淫威来自黑水战役,来自他从黑水战役揣回家的那颗手榴弹;风情则来自他那一坡悲怆、长声吆吆的使牛歌,好像真能让拉犁的牛体会到劳动的幸福。
怎么就想不起使牛人的脸?怎么想起的只有斗笠和斗笠的暗影、雨水、叶子烟的气味?斗笠好像是悬在半空中,它的暗影也好像是投在一张虚弱的白纸上,雨水和叶子烟自然没有依托。几乎就像我们当地的稻草人,只有身子,没有脸,好像很轻视鸟儿的智商。显然,记忆也在轻视我的智商。可是,记忆里那位特别的使牛人的断臂却是无比清晰的。闭上眼,它的猪肝红的截面、结扎的蚯蚓一般的血管、多少有些纷乱的青筋,都清清楚楚,连脉动都看得见。使牛人在泥泞的山路上随牛而行,斗笠的边沿挨到了绿叶。很少听见鞭声。有鞭声,也便有沉默。水牛的沉默要远胜于黄牛,感觉像是有导火绳在 燃烧。
虽然今天有了电视、电话、手提电脑和西方世界的艺术咨询,但如果要我在今天和有使牛人的过去之间做出选择,我还是愿意回到过去。在我所有的记忆展开的过去都是一片竹林,一个马厩,一副手磨,一个红苕窖。我们总是选择黄昏在马厩外的手磨边铡马草,经常是要轧到天黑。天一点一点往下黑,先是在石墙外的麦地里,慢慢就到了路口,到了我们家屋檐下的门板上。有一阵子,真像是在往门板上浇墨汁。已经看不见二哥往铡刀下喂草的手指了,我却还在一刀一刀铡。门开了,黑咕隆咚里撑出橘黄的油灯。油灯照出了我们和竹林、铡刀、手磨的影。外婆拐着小脚走近,灯掌在前面,看不见脸。现在想起,外婆的脸依然是一张橘黄的油灯。使牛人赶了牛从墙外走过,脚步声、牛蹄声各是各清清楚楚。不再有使牛歌从墙外飘进来,感觉得到使牛人的累,如拉了一天犁的牛一样沉默。而有一些夏天的午后,使牛人的山歌却是火辣辣的;火势往往在歌词和嗓音的隐秘处加强,烤得路口的青光石没人敢坐。我注意过那些伸出石墙的樱桃树的叶子,整个夏天都是卷曲的,每一个卷褶里都埋伏着一只肥溜溜的青虫。
我时常在午睡后的懵懂中被大人用绳子吊进竹林边的红苕窖。我像是很乐意。下细想来,我是迷恋被悬空的感觉。我不知宇航员除了实现生命体验的某种光荣,是否也会迷恋那种悬空感。特别是用外婆刚刚从头上取下的黑布帕从腋下交叉捆绑时,会有特别温暖的感觉。红苕窖里凉快,可以看见竹根。红苕多的时候,无处下脚,只有踩在红苕上。开始的时候,捡了红苕在撮箕里,也都是靠布帕吊出去;后来长大长高了,可以把撮箕举在头上,递出窖去。我在红苕窖里唱歌,有细土从竹根掉下来,我唱歌的声音就不敢大声了。每次都能看见一两个发霉的红苕,身上罩着雾状的白幕,表皮上浸着水。外婆吩咐我捡了发霉的红苕捡扔出去,我却不敢去碰它们;就是今天,在我眼里,腐烂的红苕和它们的恶臭都还是相当恐怖的。
每年的雨季,都能听见有人在后山吆喝,有人在石墙外奔跑。爬上门槛,能看见电影里快镜头一样闪过的蓑衣、斗笠。不知雨下到了第几天,屋檐水已经淌得很均匀,响声也已经很均匀。四处都是雨雾,竹林和树丛整天都是迷蒙的。不用去想,也知道通往后山的道路有怎样的泥泞。“牛滚岩了。”只这么一句,我便加入到了奔跑的蓑衣、斗笠中。“死娃子,你敢跑!岩背后的路滑得很。”外婆在后面喊,继而追出了路口。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见的是外婆陷进稀泥的尖尖小脚。
我希望看见使牛人的脸——它该有怎样的沮丧和绝望?事实上,我一次也不曾看见。一头水牛或黄牛的死,对于一个使牛人到底意味着什么?雨季一到,后山的青草就茂盛起来,特别是岩背后,那些悬崖边的扁谷草绿油油的,有些还间杂着雪莲花,看上去非常适宜水牛宽阔的舌胎。可是水牛不知道,它们蹄子下面的土也变得相当松软和滑溜。
在龙嘴包遇见一拨人抬了水牛往回走,总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望。水牛瘫在箩筐里,变成了一坨坨的牛肉,怎么也和走在犁沟或奔跑在山坡的畜生联系不起。原先,它的鼻孔可是可以发出“哞——哞——”的低音的,它的尾巴可是可以左右开弓扑打屁股上的蚊虫的。我为什么失望?又为什么说不出来?是因为我不曾在使牛人脸上看见沮丧、悲伤和绝望?我压根就没有看见使牛人,我只看见使牛人用的鞭子扛在他一年四季都吊着青鼻涕的孩子肩上。也许我看见了使牛人,只是依然看不见他的脸。很多年过去了,我从未看清过任何一个使牛人的脸,每每去想,它们都如那些在寺庙看见的被去掉脑袋的塑像,除开身子只是一片白茫茫的虚无;不同的是塑像的身子里塞满稻草,而使牛人的身子里塞满碳水化合物和使牛歌。
跟在抬牛肉的人后面的是一群半大孩子,他们有的扛着牛骨架,有的抬着刚刚剥下的牛皮,三三两两。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眼睛却一直盯着淌在泥路上的血水。血在雨水里扩散,像一些受惊的小鱼。雨一把捏不住。而今想来,那气氛多么像是在送葬。
后来走过报恩寺和清真寺之间的杀牛巷,看见那么多杀牛、剥牛的场面,感觉并没有获得什么感官和想像的补偿。一次次去想像笨重的水牛从百米高的悬崖滚下河的情景,闻到的除了血腥还有被压碎的青草和雪莲花的气味。我想那些使牛人一定目睹了那些滚牛的场面——不止一次地目睹,我愿意善良地相信他们的脸在那一瞬间有过变形。
我也亲眼目睹过剥牛。在岩背后的岩堰里,在金洞坡的稻田边,在龙嘴包的索桥下。我忘不了那些雨过天晴的蓝和绿,忘不了蓝天上那朵棉花云(它真的有棉花的形体和洁白,在飞快地绽放),忘不了纯净、湿润的空气里那一阵阵的血腥味。剥牛人的刀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烁白光的时候,我的神经就一股股地疼。在以后漫长的发育过程中,那些神经都一直保存着这些疼痛,并与增长的神经截面成比例地放大。血水从已经剥开的黏糊的皮张渗进了旁边水麻叶或水葵的根部。几个硕大的红嘴绿头苍蝇在剥牛人的刀口萦绕。我在围观的人群里找到了使牛人,可是他的脸上盖着一顶狗屎黄的军帽,把五官遮得严严实实,无论我怎么猜测,也猜不透军帽里那张脸。
在那些雨天和雨过天晴的日子里,我最害怕的不是看见滴在雨水中的鲜血,而是把自己想像成一位使牛人。“当一个使牛人,会看不见脸。”我当时就确信这一点。也许在山地扯起嗓子使牛有一种粗犷甚至豪迈,可是我不喜欢,因为它们怎么听都是悲怆的。
我想,你们一定看出,这样的记载对于使牛人最多是一种温度不够的结晶,他们的形象依稀,像我小时候时常在沙滩塑的那些老爷。好在白纸上没有波浪,依稀的使牛人会被保存 下去。
最后我想坦白一点,我是乐意听见滚牛的消息的。即使使牛人也乐意。我想,在当时,滚牛的消息只有对于被摔死的牛自己才是噩耗。剥好的牛肉摆在保管室铺好的晒簟里。牛脑壳、牛骨头也摆在晒簟里。牛皮绷伸钉在土墙上。“划得着,划得着,五毛钱买个牛脑壳。”每一家都分得牛肉,就我们家分得牛脑壳。从早上到下午,牛脑壳一直在大铁锅里煮着,加了自贡盐、生姜、花椒、干辣椒,在几十米开外的路口都能闻到香味。
不同的个体
午后睡醒,在床上有一段停留。一些蛛丝断去,一些石头露出水面(即或还有几个浪子,也很快就退避了),像一条条注入江河的小溪,在睡眠里失去的意识又回来了。挂起罩子,望着从泥窗照进来的阳光,清晰如铁匠铺炉火里的红铁。一只蜘蛛从一根断丝滑下来再爬上去,和从睡梦里醒来的孩子一起成为了那个遥远的夏日的午后最初的两个个体。
在看见另外两个个体之前,我先想了一会儿事——在废弃的提灌站的生铁管道里“打电话”的事。与其说是想事,不如说是陶醉。记起跟林犬、九胜、玉儿在生铁管道里说话,还真是陶醉。生铁管道一头在瓦窑前面的堰沟里,一头在挑水路的土坎上。九胜在上头的管道里说“缠(长)桂人民管报站(广播站),今天下了两个蛋”,我也听得到。我看不见九胜,九胜也看不见我。有时我也把脑壳伸进管道去唱“坐山雕杀我祖母掠走娘”,听见九胜他们在管道里嘀咕,回声很大——我自己的回声,他们的回声。明明晓得九胜他们是在管道的另一头说话,甚至想得起他们汗湿的脚趾挤在塑料凉鞋外面的情形,还是要去想像他们就盘腿坐在管道的黑暗里,屁股和腿杆贴着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生铁,宛如坐姿的青蛙或蟾蜍,不停地扇动着白肚子。
走厅房出来开大门,看见落在神龛上的阳光、落在三合泥地上的阳光、落在外婆棺材上的阳光,有圆形的,有三角形的,有长方形的,它们真像金子。有一块落在由民国留下来的桌凳上,稍微显得苍白。
大门反锁着,拉动中我看见长长的古锁,便退回去走后门。午后的后院显得特别空落,安静也成了虚茫,石墙上冬天积攒的梢柴已经被取光,在树阴里打盹的鸡也不再是个体。樱桃早已一颗不剩,徒有满树繁茂浓绿的叶子。
翻墙过去叫林犬,看见一条乌梢蛇盘在林犬家的甜菜地里,慌忙从墙上跳下来,差点磕掉门牙。走大路去晒坝叫九胜,没碰见一个人、一只猫。怎么太阳在路上、在庄稼地里、在河对岸就不像金子了?路边的茄子、辣子都有些萎蔫,只有上了架的豇豆还精神抖擞。从一个个桑田看出去便是锅坨漩,一个因为遥远变得虚茫的水域,就像是我当时偶尔念想的80年代,或者今天时常去回忆的1976。
在九胜家的房子当头听见声音,突然警觉起来。有什么香味飘进鼻孔,抬头去看九胜家院坝里梨树上的梨,还是碧青的。嗅觉告诉我,不是梨。声音越来越分明,似乎也能判断到它的来头。是呓语还是呻吟?是欢笑还是哭泣?望见一扇窗在头顶,声音不断地传出来。屏住呼吸,步子也不敢移。看见梨树下有个背篼,蹑手蹑脚过去拿来,倒放在窗下。爬上背篼,踮起脚尖……看见了两个赤裸的、交叠的个体。
九胜在胡山林家门前的稻田埂上挖曲蟮,我找到他时曲蟮正一根一根从竹筒里爬出来。我帮他把曲蟮捡进竹筒,塞上塞子。他跑过来抢过竹筒,拔了塞子,说曲蟮在里面不能塞塞子,否则曲蟮会变成泥巴。什么时候九胜也学会用“否则”了?我发现竹筒里那些曲蟮都是他在腐烂的麦秸里挖到的,粗大如蛇,蠕动起来吓人。不过,曲蟮这东西在我们眼里从来都算不上个体,仅仅是哄鱼上钩的饲料,像水麻叶、水葵花、刷把签、苦麻菜这些我们习惯了的青饲料一样。
去三杨盖钓鱼之前,我们又分组去到生铁管道的两头“打电话”。九胜、林犬、玉儿和我。当之无愧的个体。玉儿脱了裤子朝着一棵板栗树撒尿的时候,我看着长在他两腿之间的水龙头。起风了,我听见管道那头九胜的声音在变细、变弯曲,像河口桐子树上摇曳的枝条。“往里面扔个石头看看?”九胜说。玉儿找了个圆石头扔进去。我听见石头一直在管道里滚。“我们也听见。”林犬和九胜在管道里说。“任九胜!任九胜!”玉儿在管道里喊。“喂,喂,玉杯杯,你要干什么?”九胜说。“任九胜,我看见了,坐在黑咕隆咚里,像个癞蛤蟆。”玉儿说。“玉儿子疙瘩,我也看见你了,也坐在黑咕隆咚里,也像个癞蛤蟆。”九胜说。“嗨,九胜,我们不打电话了,我们去钓鱼!”我推开玉儿,把声音压得很低。“好啊,瑞哥,我也是这么想的。”九胜学着我的腔,也把声音压得很低。石头还在管道里滚吗?我们似乎都忽略了它,包括它的声音——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个体。
天暗了一成。还看得见阳光在锅坨漩和锅坨漩上面的錾子岩。我在鱼钩上穿了九胜竹筒里的曲蟮,站在三杨盖前面的礁石上,一甩一条鱼一甩一条鱼,很少有放空的。只是甩上岸的鱼不安分,又跳又扳,一不注意就回到了水里。我丢了鱼竿在石窖里按鱼,总是很紧张,动作也没有个准,尤其是按到鱼的时候。滑,再加上恐惧,鱼总能一次次从我指缝逃生。石巴子还好些,遇到红尾巴,简直没办法,身上那层黏液好像是专门为逃生分泌的。我的手不是被石头磕破就是被鱼钩划破。一条又一条肥溜溜的鱼从指缝逃走,还朝我摇尾巴,让我气愤。我把气发泄在那些就范的鱼身上——它们要么是过于贪婪把鱼钩吞进了肚子,要么是运气不佳被抛得离水太远。我比较擅长的暴虐是把鱼使劲地往石头摔,直到看见肠肠肚肚流出来。九胜喜欢拿石头去磕鱼的脑壳,磕得血淋淋的。肠肠肚肚都流出来了,脑壳都裂成两瓣了,眼珠还在转动,鳃还在翕合。玉儿习惯拿脚去踩,把鱼垫在石头上。谁叫它与我们作对?这些鱼——逃脱的和没有逃脱的——和我们,都是个体,互为对手,有灵性,但每到擦黑边上,胜利者总是我们。它们,被我们用柳条(也有用钢丝的)穿成串,以群体死亡的姿势展现在暮色里,等待它们的是油灯下雪亮的剪刀和沸腾的油锅。即使那些侥幸逃生的也算不得胜利者,我们的鱼钩已经在它们的嘴唇和喉咙等着了。
2008年4~5月于四川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