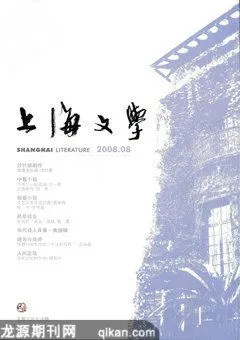人格·韵味
诗人文人,先要做人。我想先谈谈做人的问题。
鲁迅,无论品行还是文章都是让人尊重的。是站得住脚的。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有了变化。我想讲三位老前辈,但请大家原谅,我可能会有些言辞不恭。
首先是郭沫若,他确实是个才子。据传50年代末写话剧《武则天》两三个礼拜就出来了,当然缘于他的史学根底深厚。但诗在解放后却写得很滥很糟,能读得几乎没有。整天与领袖“唱和”很没有意思。郭一辈子迎合领导人,日子过得挺好。但晚年遭丧子之痛,很痛苦。直到“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一个“大”字,是宋韵里讲得“开口”口型,很是痛快,只是已到了残烛 晚年。
另一位是老舍,因《龙须沟》(按周总理的话说:是做了共产党没法做的工作,起了非常大的宣传作用)被捧得很“红”。后因“文革”前文艺界风声渐紧,又被领导人“疏远”,这时的老舍说:他们不知道我有用……话语很凄凉。直到“文革”初期溺水而亡。我认为这个悲凉,还是因为他本来是想往上面“靠”的。
还有一位就是沈从文,解放后他一直受压,在历史博物馆抄卡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了《中国服饰史》,并建议上面,由中年人(即“红人”)当头,只要有间办公室,具体工作他做,即别人出名,他写,做些文化传承方面的工作(因为他认为“当红”的人笔力不强)。直到“文革”分给他一间房,他吃、住、工作都在这间房子里,与家人的房子不在一起,只有靠夫人送饭,就难免经常吃剩饭。心疼他的人对他说,吃剩饭会得病,沈从文却笑着说:我早有准备。原来他从医务室开了许多消炎药,每次吃剩饭前先吃消炎药。就这样留给了后世一部《中国服饰史》,尽到了特定年代里一个中国文人应尽的责任。
列举三位老前辈,请各位在“学做人”上深思。
……谈谈诗歌的“韵味”。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新诗九十年了,如何才能进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诗词的“家谱”呢?也就是新诗如何传承古诗词的血脉问题。
我首先想到了“韵味”,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心理问题。一首诗,一支曲子,一幅画,一部小说或电影,读、听、看的时候,“入神”了,进入到了艺术作品的“境界”中去了,在这样的“境界”中跟作者一同经历各种感情的起伏,从中纯洁精神,陶冶情感,这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说:“词以境界为最上。”而“韵味”是在读完、听完、看完作品后,“出了”其“所造的境界”,“定下神来”,而后慢慢地回味,咂摸其中的滋味,细细分辨……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心理过程。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样对艺术作品进行品咂琢磨之后的感觉,是多少年也忘不了的,这滋味能伴随一生,这就是“韵味”。正像宋代的范温所记:“概尝闻之撞钟,大音已去,始音复来,悠扬婉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
对于新诗的“韵味”,我以后还要写文章细谈。
关于“滋味”两字,最早见于钟嵘的《诗品》。在谈到诗由四言变为五言时提到,可见讲究“诗的滋味”早已有之。
回到前面,在新诗传承中国古诗词的血脉上,我认为依据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心理,在诗的“韵味”上下功夫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别的方面的问题。
根据应张清华教授之邀,在北师大文学院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此文
2008.5.2 晨1:20 初稿
2008.5.7 下午2:00 修改定稿于上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