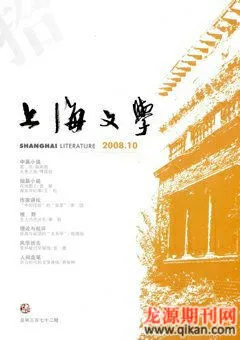“中国经验”的“原罪”
同学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到上海大学来跟大家见个面,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不太喜欢“讲座”这种说法,老是一个人坐在那儿讲,然后有听众在听。我希望讲座不是讲座,而是座谈,每一次这样的场合也都是在谈自己的创作的体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创作的一些困惑。就是我自己也特别想不通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很多年都一直缠绕的、纠缠着自己的一些问题。因为老去想这些问题,写文章的时候想,不写文章也去想,然后慢慢地时间长了,就成为一种好像必须得去想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些场合,比如写点文章,比如到这儿来和同行们讲一讲这样的想法。你看今天不光有咱们上海大学的同学们,还有著名作家阎连科先生,我说咱们俩私下已经聊了很多了,他也要来。著名评论家李庆西先生,他们都是批评作家的,也要来听。接下来我就讲讲我自己的困惑吧。
其实这个题目,当初蔡翔老师问我要的时候,因为很着急,就是今天给了我一个E-mail,我说你现在马上把题目给我。就是立等,就好像是修鞋一样,把那鞋脱到这儿了,你给我钉好我才穿上走。我说,你说的那个总的题目是什么?他说,我们就是现实主义和中国经验。我说,那好吧,那就是“中国经验”的个人体会。但是其实给了他以后我就有点后悔,我说那是太急就章的说法,就是像白开水一样的端过去一杯。其实后来我想了想,稍微修正了一下,我实际上想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验的“原罪”。“原罪”,就像基督教说的那个原罪。这样呢就可以把那个话题更突出一点,也因为它具体突出了,有时候就容易把一个尖锐一点的话题理清楚。
在开始之前,我想讲三件小事情,慢慢进入这个所谓的“原罪”,这个焦点。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水果的问题。大家都吃过水果,也都买过水果,也都进过超市。这都是最普通最普通的事情了。我在讲这个话题之前为什么要讲这个水果呢?就是我在想,有一个问题,比方说,我们进了超市,要买水果。我们只能说,我要买香蕉,我要买橘子,或者我买菠萝,或者我买芒果。你一定要说出具体的你买什么,你才可能从商场里拿到你要买的那个水果。如果说你进了一个商店,你跟那个商店的服务员说,我买水果,我相信你任何水果都买不到。他肯定会问,请问你要买什么样的水果?是苹果?是橘子?这是我讲的第一件事情。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和这个水果也有一点关系。有一次我在太原的时候,是我女儿去法国留学的第二年,暑假的时候,她从法国回来。她的法语老师认识澳大利亚来的一对夫妇,他们在这儿任外教。就是认识这样的一种关系,知道说认识一个作家,就是希望能和我们见见面。我和蒋韵说,我们就见见面吧,既然有这么一个关系。我也想人家是外教嘛,能够到我们山西省太原市这么偏远的黄土高原上来,做这个外教工作也有一点儿献身精神。人家提出这个要求我也不好意思拒绝,我说那好,无非就是吃顿饭嘛!但是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位外国的先生,很有意思。他是个有心人,他不是为了简单的想吃一顿饭,在饭桌上谈了很多问题。然后他就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李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自己首先是一个作家呢还是一个中国人(听众笑)?这个问题有点像水果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首先认为你是一个苹果呢你还是一个水果?我明白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有过一些出国的机会。经常会在一些会议里,或者说在一些场合里,碰到这样的提问。我也知道,这个提问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个现成的正确答案,所谓“政治正确”的答案。你一定要说,我首先是一个作家,其次才是一个中国人。因为这种说法就会凸显出一个艺术家的个性,我的主体精神,我的不愿意被归类,我的不可被同化。然后才可以谈我是某一类的。意思就是说,你首先得说,我是水果,至于说是苹果是香蕉是西瓜,这个咱们先不要谈。于是,我知道他希望我说,我当然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我才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我想了一想,我觉得那样说有点像说谎,我决定告诉他实话(听众笑)。我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才是一个作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个答案也是很现成的。因为任何一个人被自己的爸爸妈妈生下来,生在一个环境里,任何一个孩子的第一声啼哭都不是诗歌,也都不是作家。他首先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懵懵懂懂的生命,被他妈妈生到这个世界上。那么他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决定了他。如果你生在中国,你长在中国,你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上长大成人,你在上海长大成人,那么你就会受上海的很多的文化气氛生活习惯包括上海方言的影响,然后你慢慢地成为了一个上海人。又由于你受这样一个每时每刻身边都存在的中国文化气氛的影响,你上学你听广播你看电视,你结交的朋友老师广而扩之所有的这些人,你出去旅行见到的事情等等。在这个经历当中,经历了中国当代的那么多事情,“文化大革命”、唐山大地震、改革开放,最近是汶川大地震等等。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的总和渐渐地积累而使你成为了一个人、一个中国人。那么在那么多中国人里,因为你有一种关于语言表述的渴望,而又碰巧你又有这样的一点儿才能,那经过努力之后你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就是说“我首先是一个作家,我其次才是一个中国人”这个说法它是一个谎言。肯定是,它是一个后天选择的。就是说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我的“政治正确”,为了使这个问题比较圆满,为了显示我的个性,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它会从这样一个定义出发,而且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定义出发。这是第二件事情。渐渐地我们在接近那个“原罪”了。
我再讲第三件事情。那是1999年,去马来西亚。那一次是《星洲日报》组织一个“文学周”之类的活动,要评奖,我和王安忆都是评委。然后在我们评完奖以后主办方就安排我们到槟城、怡保,这样一个一个城市去游访,然后他们就预定了许多城市的这样的讲座。到一个地方去,两个作家就给讲座一下,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也没有那么多的听众,一般都是小猫两三只,但是我和安忆就像夸父逐日一样(听众笑)锲而不舍,不管人多少,反正是去了就一定要认真地讲。包括那次我去槟城的时候,因为不慎吃了一口虾酱蘸苹果,结果上吐下泻发高烧,还是得坚持去讲座。于是我就遇到下面的事情,就是在一个讲座的时候我讲了一个问题,第二天就变成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后来又演变成了另一个事件,这个有意思。讲什么问题呢,我就来对比莎士比亚和曹雪芹。我就讲我不能讲我偏好的最喜欢的作家,就讲最经典的作家。他们几乎可以作为符号,莎士比亚可以作为英国文学、英国文化的符号,曹雪芹可以作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符号,我就举这两个人的例子。我就讲这个莎士比亚他实际上是文艺复兴运动结出的硕果,因为莎士比亚咱们大家都知道,他产生的时候文艺复兴运动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他是那个集大成者。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当中,最后结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果实就是莎士比亚。那么莎士比亚无疑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的悲剧,莎士比亚的传之久远的悲剧,是非常感动人的。但是我同时就要讲到曹雪芹,我说,当然,曹雪芹稍微晚一点。但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中国的大地上并没有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一个积累了上百年几十年的一场人文主义精神的这样一个觉醒的运动,一个自觉的运动。但那时曹雪芹只是凭着一个作家的深刻的良知,和他空前绝后的才华,以一人之力,在那个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最黑暗的清朝,就是“文字狱”最惨烈的那段历史背景下。那个时候也没有政府的扶持,也没有作家协会,也没有文学奖。“不务正业”的曹雪芹不去考八股,却写出了这样一个思接千载的悲剧——《红楼梦》。那么我就说,要这样来对比这两个作家,我就觉得曹雪芹的探索更可贵。在这个寓意上,我就觉得曹雪芹更伟大更可贵。不是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而是说就作为个人的探求个人的追求,作为艺术家的这样一种以一人之勇,一人之精神所担负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么把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相比,那个是一个集大成者,这个是一个从羊肠小道上只身攀登的孤独的探索者。好,第二天当地的新闻就登出来了,说,中国大陆著名作家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听众笑),就觉得特别解气。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一个非常受压迫的一个群体,在马来西亚,在很长的时间里,华人是不可以自己办学校,不可以用华文的。后来经过很长很长时间才被允许,还只可以办小学,中学不可以办,又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可以办中学,但不能办大学。比方说我去的槟榔屿,那个槟城,我们去,那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寺院,寺院里塑了一个金身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像,这个像是在大陆塑成的,而且漆了金身,在这个寺院里安放好了。等我去参观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南海观世音菩萨从底座向上大概有这么三五米的地方全都给刮下来了,全都裸露出水泥,非常难看。我就问当地陪我的那个记者,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他就告诉我说因为这尊菩萨像放在这个地方,它的高度超过了槟城清真寺的金顶。所以槟城的议会就通过了一项决议,说要不然在那个菩萨头上盖一个亭子把菩萨挡住,要不然去掉几米,要低于这个金顶。于是就出现了我所看到的这个剩下多半截的南海观世音。大家可以想想,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气氛之下,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压迫之下,就是华人在那儿的那个地位,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去槟城之前经过怡保,怡保是马来西亚最著名的锡城,就是金银铜铁锡的那个“锡”。当年全世界最大的锡产量就是在这个城市。我们路过怡保的时候,就是我吃虾酱的那个地方(听众笑),吃完虾酱吃完饭我们出来路过街边的一个小茶馆,一看就是那种非常破败的一个小茶馆。里头摆几张非常破旧的塑料桌椅板凳,坐着几个老头,一看就是那种穷困潦倒的人,穿着拖鞋,穿着裤衩,晒得黑乎乎的,无事可做。因为怡保的锡矿已经被全部开采光了。英国殖民者先开采,荷兰殖民者再开采,所有的锡矿被开采光了以后,这个当年世界上最著名的锡都就剩下一片荒凉,所有的外资撤光,然后留下了深深的矿坑。矿坑都被雨水填满,原来都要用抽水机抽水,抽水机一不抽水就全都变成了万丈的深井。那个城市现在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些不知道路的孩子们不小心就掉到矿井里去了。路过这个小茶馆的时候其中一个老人,一看我们走过来了一群人,前头人都已经走过去了,我在队伍的后头,就突然上来,握住我的手说,台北来的?他马上认为是台北来的,因为台湾的旅客比较多,而且马来西亚的小学和中学的课本都是用台湾的课本,繁体字。我说不是,我说是北京来的。他就说都一样嘛,都是中国人嘛。然后就握着我的手开始唱开了,就是《我的中国心》,是那几年特别流行的一首歌,唱得荒腔走板,还把其中的歌词“我的中国心”唱成“都是中国人”。老人一头白发,唱着唱着热泪横流啊。我当时就呆住惊住了,我一个路人,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突然被另一个人握住手说都是中国人嘛,然后就给你唱起一个歌来,而且唱得是热泪横流,我当时都有点忍不住。你一看他就知道这是一个饱受沧桑的劳动者,一个一生辛苦的老人,然后这件事情就在我心里久久不能忘记。大家知道华人在这儿的命运,他们当年就是去当“猪仔”,“南洋猪仔”,做苦力,然后慢慢就留在那里了,有些人经商成功了,大多数人一直就是最底层的劳动者。那么现在我再回到莎士比亚,回到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那这件事情还没完。然后当年呢,高行健就获奖了,获奖以后就开始每年炒作这个诺贝尔奖,这是一个逃不脱的时髦话题……有点像是生病,每年的流行性感冒(听众笑)。每年流行一次。然后有一位就问马悦然先生,就是那种引诱式的问题,先是问别的,问着问着,突然问一句说,我在马来西亚的报纸上看见,李锐认为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马悦然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听众笑)?这个问题已经简化成李锐认为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马悦然先生回答的还是很得体的,他说这是两个不可比的作家,不可以这样比的。而且艺术只有欣赏和不欣赏,喜欢和不喜欢,没有谁比谁更伟大。我觉得马悦然先生大概见多了这样的突然袭击,他的回答还是很得体的,没给对方留下什么,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说某个人或某份报纸怎么篡改了我的原意,或者某个人怎么用心叵测或者用心不良提出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背后也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有一个所谓“政治正确”的答案。就是说你如果认为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你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你无疑就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你就是一个文化原教旨主义。大家别忘了,现在世界上最流行身份认同。昨天王安忆还在讲,身份认同啊,是现在最流行的话题。但是这个身份认同是已经分好等级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一律都有一种文化印记或者说政治印记,就是叫民族主义。就是任何对于发达国家发达世界的不满、批评、抗议都会被很简单地贴上一个标签,就叫“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这是中国人的“原罪”,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原罪”。只要你生在一个穷国,你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你的身份就是一个区域性的狭隘的地方性的身份,你的发言就是一个方言的发言,你就永远不可能参与所谓人类的,所谓关于“水果”的讨论。你就永远是一个橘子,永远是一个不起眼儿的退化的苹果。你不可以被放到关于水果的这个归类里来进行讨论,我就是在讲这件事。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本来是在讲两个作家各自的优长,讲他们各自产生的那个不同的背景。实际上我认为《红楼梦》里面所表达的深刻的人性,一点儿不比莎士比亚的悲剧表达得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部杰作,一个代表作,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曹雪芹确实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因为莎士比亚不能说他作为整个英语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是真的没有这个意义。所以说,为什么本来是讲审美,讲文学欣赏,讲对作家的选择,讲一种审美上的喜欢与不喜欢,怎么就忽然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就变成了这样一场标签游戏。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这个问题让我挥之不去,就一直在我身边,而且我在许多场合许多次都碰见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作为“人类”的普遍可能性,或者说民族主义、地方性等等这些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的“原罪”。
我在这儿再给大家念一段话,傅斯年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大历史学者,应该是大师级的人物,大家都知道,我不多说。我念傅斯年先生抗日战争期间说过的一段话,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评价和认识,这段话登载在第六期《读书》上。傅斯年先生一边说要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不容怀疑要建立民族的自信心,这是必须树立的。同时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运动的近代的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这是一个疑问句,一个彻底的疑问句。就是说,在傅斯年先生的评价里,中华文明的四千年文化,叫做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傅斯年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的这个说法,其实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个世纪,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也包括在中国普通人身上纠缠不清的一个问题。一直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种“原罪”,就是我们万事不如人,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来跟人家谈的东西。昨天的圆桌会议上我们讲到普世的价值,就是为什么现在讲西方文化欧美文化推广到全世界,有一个最基本的论点就是认为,他们有一种普世的价值。讲自由平等博爱,讲人权,讲民主政治,等等,这都是一些普世的价值。但是,就像刚才傅斯年先生这样一个论断,他可以说学贯中西了,而且他又是搞历史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评价就是“四千年的垃圾箱”。所以对于我来说,尤其对于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所谓的新中国50年代的黄金期,那个浪漫的黄金期,又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国门终于打开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走到世界去看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不必总是在书本上电影里和电视里去看别人,而是真的走到美国走到欧洲去看一看的时候。那么,我们自己的身上的这样一个文化身份认同,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我们希望着自己融入世界,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认为我们融入世界的时候百无一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值得你提。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幻灭之痛》,谈我的两部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就是来讲我们这一代所谓祖国的花朵们,充满了信仰的一代人,怎么从一个狂热的红卫兵又变成了知识青年,然后怎么从这个狂热的信仰变成那个“我不相信”,北岛的代表性的那一句话,“我不相信”,就是我不能相信任何事情。当所有的真理、正义、神圣,这些这么堂皇的、这么庄严的口号,这种旗帜在你面前全都变成肮脏、残忍、冷酷和失败的时候,真的你不能相信。我曾经说过,我为了不再绝望,我宁愿不再相信希望,这就是我的一个精神状态,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断地希望要去写作的一个精神状态。为什么?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来疗救自己这样的精神创伤。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原罪”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处在一个从里到外的双重的否定。就是别人的否定,再加上一个我们自我对自己的这样一种否定。我们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全盘西化、全面反传统,“四千年的垃圾箱”让我们不停地革命、不停地摧毁、不停地铲除。我们在一个永远不停铲除的、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怎么能再建历史的高度,怎么能再去找到那个所谓的“整体性的建立”?这几乎就等于自己希望在一个深渊上建立大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荒谬,我自己就觉得我总有一种荒谬感,而且是种很难以克服的荒谬感,但是人不能老是这样。那么我就在想,有没有超越了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这样一种东西。如果说普世的价值,那么我们讲,比方说唐诗宋词,唐朝的政治已经过去了,宋朝的意识形态也已经变成了彻底的历史,但是留下来的苏东坡和辛弃疾,留下来的李白和杜甫的诗句为什么今天仍然感染和打动我们?那里头所保有的价值,有没有普世的价值,有没有超越国界文化种族宗教的价值?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没有这个价值?如果有,那么作为一个方块字的书写者,你有没有可能在前人这样的一个高度上去完成你的创作,你有没有可能把前人的这样一种价值,把千百年的传统变成一个此时此刻的叙述?其实是渐渐的,我也是在这样的一种矛盾里挣扎,自我的不停的纠缠、否定、找不着出路,希望找到出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彻底地自我否定的。因为彻底地自我否定的人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人。
永远自我否定的最终出路,解决的途径就是自杀,我在我的小说里写了很多位自杀者。在那条自我否定的道路上走到底的时候,就只有用死亡来结束这个否定,用死亡来肯定自我,最后一次肯定自我。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可以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去探索这个深渊的深度,并且可以在探索深渊的深度的过程之中去找到那个可能的立足点。所以说我二十多年来渐渐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寻找精神的支点。1987年的时候,我曾经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过一片文章《现代派:一种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因为当时中国文坛上正在开始所谓“现代派”和“伪现代派”的争论。“现代派”,冒号,一个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在反省我们中国作家,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处境。首先我们要能够清楚地去看别人,正确理解别人,而不是简单地把别人的现代派创作,拿来就当成今天的真理,立刻去做一个复制的现代派,立刻去做一个简单的摹本,立刻去做一个对他人的重复,那叫“副本效应”。就是别人的副本,别人已经写过了,我再拿到复印机里复印一下。我在那篇文章里讲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在讲西方人自己对自己的反省“原罪”,就是他们对自己“原罪”的一个深刻的反省。
我提到了一本书,就是美国作家库尔特·冯纳格特的《囚鸟》,一本长篇小说。在这个小说里,他写了一个美军中尉,一个军官二战期间在欧洲大陆认识了一个犹太姑娘,他爱上了这个犹太姑娘。然后他就决定要和姑娘结婚。当他向姑娘求婚的时候,姑娘说了几句话,让他非常震惊,也让我非常震惊。这姑娘说的话很简单,大意就是说,人类这个物种,是一个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物种,人类现在污染的还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她不希望看到人类污染更多的地方,所以不希望人类再繁殖下去污染别的地方。因此,她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这个姑娘的彻底绝望我们可以理解,她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因为她亲眼看见了人类怎么用现代科学技术,用严厉的现代社会的组织手段,大规模地像宰杀牲畜一样的宰杀人,进行种族灭绝。这是人性的一部分,这是发生在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最科学、最优雅的欧洲心脏里的事实。欧洲人为什么要在全世界搞几百年的殖民地,为什么?他们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推向全世界,全球化是从殖民地开始的。他们先在欧洲自己互相殖民。后来打来打去他们想明白一件事儿,与其我们在自己院子里“殖”,还不如跑到外面去“殖”。于是他们就从欧洲的院子里集体出逃,四处殖民。在外面建立殖民地,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殖民地的原住民都是“低等人”,都是应该被他们去教化的人。但是最后就是在这个文化的中心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人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还不够,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还不够,还要把原子弹造出来,然后扔到广岛和长崎。实际上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就是从《尤利西斯》,从《恶之花》这样开始的现代主义,从美术、文学、诗歌等各个领域开始的现代主义思潮。实际上它背后的历史大背景,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西方文明的灾难面前的反省。我在那篇文章里说,西方的艺术家们是坐在真理的尸体上发出的哀歌。我们看到的现代派艺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多的现代艺术中,包括蒙克的《呐喊》,那样的画,包括卡夫卡的小说,那样的荒诞等等。就是你能看到这样一些西方的艺术家们,他们敏感地发现了自己的文化当中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那个是他们的“原罪”,就是没法去掉的人类的罪恶。他们就在反省这个问题。
实际上西方文化在他们的几百年来对世界产生最大的影响,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们对于全球的殖民化,还有一个就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从西方文化里影响波及全世界的一场深刻的运动。当然这个运动带着一种强烈的对原来所谓“资本体系”的反拨和批判的东西,但是大家不要忘了,那也是从西方的文化中心里传播出来的一个东西,而成为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其实中国的近代史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完成的。我再来讲,任何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不可能把自己自绝于历史之外,而变成一个独立的、独特的、我行我素的单个人。就是说,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苹果,如果你进了市场,说,他们是水果,只有我是苹果,只有我是橘子,我跟他们都不一样。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别人不知你是什么,会导致别人不知道你的最终属性是什么,是把你放在家庭用品那一栏里呢,还是放在服装那一栏里呢,还是放在日杂用品里呢?就是说我们讲人性、讲人类、讲人的困境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在里面,而正是这个东西超越了朝代、时间、意识形态、政治的。这也是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写的《离骚》到现在还感动我们。其实屈原是一个楚国人。在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大潮当中,在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所谓的“历史大潮”之中,楚国是属于一个区域性的、地域性的国家,而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其实他是要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普世价值的大一统。就好像现在的全球化,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无非是当时的那段历史是发生在大致中国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之内。所以说钱穆先生有一个观85bX1i/iQLzw87w13/1VvPPWKJtzTcv0g3IhR/yvaCM=点是非常好的,他讲到春秋战国的历史,老讲孔子、庄子和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的思想家们。老讲他们的眼光,世界眼光,就是国际眼光。他,孔子不是站在鲁国一地来讲人类的困境和人类的道德,他在讲一种普遍的道德。所以说同理,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在自己的文化传统里找到那个支点,不仅在传统里找到支点,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那个精神和文学的支点,来完成自己的文学攀登。
看起来好像这个问题讲得很大,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小也很具体,只要你写小说,只要你把你的小说发表出来,变成一种公共的东西,你写小说为什么,要往外发表,如果说你写小说不发表,只是写给自己看,那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包括现在大家都说的网络写作,网络写作是什么,是为了更简单更方便更容易地发表出来给大家看,说白了就是那么一回事。就好像没有印刷术之前,所有的文字性的东西都得手抄,所以读书破万卷,其实比较容易,因为它都是写在竹子上,一卷一卷,一万卷也没多少字(听众笑),是吧,就容易破万卷。因为当时是那样,但是有了印刷术造纸术,文明有了一个极大的扩展以后,它就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其实是一样的,现在有了网络了,也无非就是这个文明的扩展技术有了一次大的变化。但是我在想,这并不意味着人性有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不能判定坐飞机的人比坐牛车的人更有人性。我们不能判定使用原子弹和激光武器杀人的军队比楚霸王的军队更有人性,比一次坑了几十万俘虏兵的楚霸王更有人性。一个原子弹投下去,一个城市毁灭了,和楚霸王把别人的军队俘虏了,一下推到河里去,淹死它几十万,这两者之间,我们看不出来谁比谁更进步、更有人性。所以说,这个问题也一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昨天,我为什么讲到汶川,汶川地震里的那个小男孩儿,林浩,映秀镇渔子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讲自己地震以后的经历。就是地震了,他从倒塌的教室里已经逃出来,可是还有许多同学压在废墟里面,他就跑回去背出一个被砸昏的同学,又跑回去背出一个同学,第三次又跑回去的时候,他自己被埋在废墟里了,然后老师把他救出来了。那个小孩儿对记者讲这个话的时候非常沉着,非常简练,一点儿也不煽情,讲得非常朴素。而且因为我是四川人,他说的四川话我都能听懂,我觉得极其亲切,我觉得那孩子简直是太神奇了。我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一个九岁的蒙童,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成果,你也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受了西方启蒙主义思潮影响,或者说是受西方现代化思潮的深刻的影响而长大的。他一个蒙童,基本上应该维持了一个人的原始状态,他刚上小学二年级,他识的那点儿字还不足以让他做出对那么大问题的判断。可是这个孩子义无反顾地当下的选择,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真的是一种叫做“普世的价值”。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普世的价值,我们不必把它简单地归并为只有西方的理论诠释了的解释了的那个才有价值,才可以拿来普世。也不必说一定得是读了《三字经》读了《论语》读了《庄子》以后的孩子,这个才叫人性。那么我们在小林浩身上所发现的光辉是一个可以普照全球惠及全人类的一种大爱,一种类似于圣徒的行为。小林浩的行为,就像当年菩萨所发的那个大愿,只要此岸还有一人不被超度,我就留在这儿,留在苦难中间。所以说,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么就在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也希望能够把中国的元素,中国的文化资源融入自己的创作。
比如说我的《银城故事》整个四章就是用唐诗来做篇目的。“黄河远上白云间”是一章,“一片孤城万仞山”是一章,还有“羌笛何须怨杨柳”和“春风不度玉门关”。当然,进一步地讲,在小说里我写了一场失败的暴动——辛亥革命。暴动的暗号,起义的暗号就是用这首诗来通知起义开始或者起义取消。这是他们暴动的暗号,最后,这个暴动失败了,那个总指挥就把这个暗号写在长江一艘盐船的白帆上,当然最后我写的是一个悲剧。就是我为什么用一首唐诗来做整个小说的题目?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简单的把一个标题挂在小说上,而是希望,在我的小说里能够透露出这首唐诗所给我的那样一种苍凉,那样一种阔大的时间感,那样一种中国人所特有、中国诗人千百年来所咏叹的生命悲情。这种天崩地裂的暴动,和这个恒久不变的永恒的日常生活,就成为这个小说的两个声部,交替出现。当我把这样的意愿带进自己的小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仅是一个水果,我也可以说我是一个橘子。包括后来,我和蒋韵,我们俩合作的《人间——重述〈白蛇传〉》。把一个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故事重新讲述一遍,用一个当代人的眼光把它完全重新讲述一遍。又因为,《白蛇传》这个故事本身具有强烈的佛教因素,所以说当我们在叙述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浓烈的佛教因素使我们在表达人性的深度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当我们在讲人性、人性的深度,在讲善恶这样的一些普世的价值的时候,佛教那种深邃的认识就给我们两个人很大的滋养,也就成为我们叙述的动力。当然,我要申明一点,这个小说是蒋韵写的多,我写的少(听众笑),当然是我们两个人合作产生的,经过充分的讨论,讨论了很多,但是蒋韵写的很多。虽然最后署名的时候出了一点技术性的问题,那个出版社一定要坚持说我们当初和你签合同的时候是你一个人签的,你现在是两个人合作了,我们也不能添上蒋韵的名字(听众笑),但是发表在《收获》上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现在台湾出了一个版本,昨天我们拿到学校现场义卖的书里有两本,麦田出版社出的,是署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重述,本来它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写作,它邀请世界上各国的作家来讲各自文化传统当中的神话故事,神话传说,你爱怎么重述都可以。一开始,我也一直害怕出版社是商业的操作,我一直拒绝,我没答应。出版社说我们给的稿费非常高,你答应吧李老师,这个别人都已经答应的。我就说,那不行,我没有写过神话,你不能说你让我写神话我就写。然后他们就把翻译好的外国作家写的重述神话的中文译本拿来,给我寄来说你看看,我们真的不是胡闹,你看这些得了布克奖的女作家也参加了,人家都不是胡闹,都是很认真的。我一看这个,我说那好,我来参加。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和蒋韵一直在讨论。后来蒋韵一直鼓励我说你参加吧,为什么不参加啊。后来我说那行,那你也参加写。于是最后就产生了我们俩的第一次合作。
其实,我们重述的“人间”是写身份认同的一个命运悲剧。一个妖来到人间,她的身份不被这个人间所接受,四处流浪,被法海为代表的所谓的正义和法律镇压,他要追杀她这个妖。作为追杀者,法海最后也发现自己所谓的替天行道变成了一场残忍的没有人性的屠杀,他也在怀疑自己作为一个镇妖人的身份,到底我这个镇妖人的身份是慈悲的还是残忍的。白蛇和许仙两个人生的儿子,从生下来起就是一个异类,他不同于他人,一直不能知道自己是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虽然高高地考中了状元,但是因为自己无法被人间接受的人蛇共体的身份,他最后终于也离开了、抛弃了状元的锦绣前程,跟着他父亲一块儿流落江湖。而且我们又写了这样一个白蛇的前世和今生。一个现代的、当代的白蛇是一个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授(听众笑)。她自己就是在雷锋塔倒塌的那一天出生的。其实那都很巧,去西湖是写这部小说的一个契机。李庆西先生在那儿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就是那次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出去玩,真的到了西湖。到了西湖晚上就要去荡舟,去游湖,看见在漆黑黑的湖面上“哗”一声就蹿起一条鲤鱼来,看见暗影憧憧的那些荷花啊,就真觉得可能会遇见白娘子。(听众笑)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真有了那个实地的感觉。我后来说叫“偶遇因缘”。要没有这个因缘,没有这样的直感也不会有后来的小说创作。我觉得这么多偶然凑起来完成了这部小说。那么这也是把中国千百年的传说变成一个此时此刻的叙述,变成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对于人性,对于身份认同的理解。
当然,我知道,这恐怕会被国际的主流,所谓的“主流文化”不大认同的。因为他们想看到一个中国人怎么嫁给一个美国人,然后生了一个非中国非美国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事情,才比较夺人眼球,一定要有他们偏爱的才会被他们接受。当然,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人么,总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去接触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熟悉的世界之外的那个世界就没有丰富性。就好像你不知道李白和杜甫,并不意味着李白和杜甫不伟大不存在,那是你无知。就好像当初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不知道雨果、巴尔扎克一样,那并不意味着雨果、巴尔扎克不伟大、不存在,那是我们无知。
2008年8月19日 审阅改定
(整理人:谷雨倩)
注:此文为作者今年6月在“第三届上海大学 文学周”中的演讲稿,本刊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