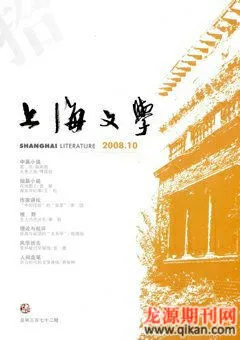女人仍然迷失
我在美国大学修两门课,其中一门听起来时髦,“美国女作家的现代主义”,我很容易口误,将之称为“女性主义作家”,因此有朋友来信问道,“女性主义究竟是应当怎么讲?我有兴趣。日本有一个姓田岛的女教授,未婚,自称女性主义者,在名片上都印着‘女性主义者’。前几年日本女子高中生卖春(援助交际)成为社会现象时,我看她在一家杂志的对谈栏目上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要是碰到自己的下体,大人就会说,不好碰哦,现在碰了,将来男人就不要你了。好像我们的身体都不是自己的,而是为男人预备的一样。现在的女孩子和过去不一样了,她们要为自己把身体拿出来用一用了,有什么不可以!”我的这位移居东京多年的朋友对此评价道,“怎么看都要怀疑这样的女性主义是不是正宗,不过确实是痛快。”
我也觉得痛快,为了这一位举止优雅性别状态传统的朋友发出如是慨叹。关于女性处置自己身体有多少主动权在今天的时代似乎已不容质疑,不仅卖春,女人也买春,巴厘、塞班、尼泊尔、越南、老挝,大城市生活优质的亚洲单身女性在落后原始的东南亚旅游地消费比她们低等的男性,也不再是尖端话题。
不过在美国大学课堂讨论女性作家的现代主义,远不是我想像的那般极端和概念。
开课的第一本书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航海记(VOYAGE OUT)》,当然故事的主要场景是在一艘航船上,毫无疑问这发生在上世纪初的航海——从英格兰驶向南美——承载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正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时代。有意味的是,迥异于掠夺成性的男性殖民者,女性们在落后的殖民地感受的是异国情调,崭新的生命场景,现在请暂且忘记这位著名女性主义作家的似乎已覆盖她的文学成就的论点,“女人需要一间房”,贯穿全书的船主女儿瑞秋成了女作家的女性意识的载体,航船上邂逅的男人和女人成就了她的觉醒和成长。只是,坐在21世纪初的课堂,父母们都已经历了性开放时代的美国女生又如何理解已婚男人给予瑞秋的初吻对她的身体和观念带来的双重冲击。被吻的羞耻,被已婚男人吻的更羞耻,以及发现自己即刻陷入情网的痛苦。
“男人女人接吻是正常的,瑞秋的反应是不正常的。也许因为这段爱不能把她带向婚姻。”一位脸颊胖胖还未脱婴儿肥的美国女生做着简单化的解释。
当然诸多学生受时髦理论影响,从中看到作者给人物注入的双性特质,瑞秋爱上的男子个性上都有女性特质,以及她与年长女性海伦同性恋倾向的友情。
我对雌雄同体、性交错以及双性恋等理论议题并不以为然,即便作者早被论定是同性恋,试问,哪位女性不为男性身上温柔一面心动,哪位女性不倾慕比自己优秀的同性,抑或,所有的女性都有同性恋的倾向?然而,这样的议题终究有些简单化。
讲课的女教授爱米丽以优雅著称,她穿着配套的羊绒套衫和开衫,用她的发音清晰柔软的漂亮英语朗读着小说里值得关注的情景,尽力将她的年轻学子们带回百多年前的场景,试图去感受女作家的敏锐锋利的女性意识在当年的先锋意义。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贡献在于,在男权的大英帝国时代,她通过笔下的女性人物颠覆了传统和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期待。
的的确确,任何人物或故事的平庸和非同寻常都和其发生的背景有关,很遗憾,在性自由社会成长的女生已经无法从身体上感受“觉醒”这一刻的震撼和革命意义。
似乎这些故事与我这个中国女性更加切近,它们好像就发生在不远的地方,因为我们保持着的最清晰的记忆仍然是那些禁欲年代的故事,在美国课堂上我的思绪闪回的都是些看似无关的细节。
比如,在70年代的中学课堂,一位漂亮女生因为穿了一件鲜红格子的短袖衬衣,而引起一场风波,该女生的额上从此刻上“红字”,她就坐在我的前两排,这一记与道德沦丧有关的警钟如此响亮令人惊骇,我的整个少女时代因此在“无色”中度过,原来,禁欲的前提便是抹杀性别,尤其不能有女性意识,也因此,谁领口上饰一条尼龙花边,辫梢上扎一朵蝴蝶结,穿一条展现臀部线条的裤子,对于其他女性都是如惊雷轰鸣般的刺激和震撼,她们听到的是激情又痛苦的性感召唤,感受着比革命时代的专制力量更加强悍的本能的渴望。
女教授希望我这个戴着女作家光环的旁听生能参加班级讨论,我常常欲言又止,对于我,所谓发言不是几句话就能结束,那将是一个个冗长的故事。
怎样让她们明白,我们走过的迥异的女性成长路程,当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女性在争取选举权、堕胎权,从各个领域对性别歧视进行消毒,不仅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要求和男性平等,也力图超越自身心理和生理上的性别限制,我们这个国度的少女却在渴望穿一件能展示自己身体线条的衣裳,渴望回到家里的厨房跟妈妈学煮饭而不是坐在学校的大礼堂参加大批判会议并学着男人放粗喉咙喊革命口号,渴望温柔和爱,一句话,渴望做回女人。
有趣的是,弗吉尼亚之后的曼斯费尔德小说的讨论更加文本化,其现代主义更是通过艺术表现手法的前卫性凸现。女教授甚至带来艺术界诸如莫奈、毕加索、雷诺阿、莫里索等印象派后印象派的幻灯作品以对比曼小说的印象派描写,此时我的另一门课,“美国战后戏剧(1945年后)”已读到70年代,正就读的女剧作家“费芙和她的女朋友们”(Fefu and Her Friends)一剧,刺激强烈,惊世骇俗,简直是女性主义里的女性主义,十二分正点。
这是一出非写实却又非寓言的戏剧,无论观念还是戏剧形式都属Avant-Guard前卫,剧中故事发生在30年代,剧中女性属有闲阶层,某一天在女主人公费芙客厅相聚原本是为慈善事,却引出女性们内心的悲剧生活,用我们今天的陈词便是,在表面光鲜的生活背后看到的是黑暗的核心。
此剧开场便不同凡响,第一句台词来自于费芙,可谓一鸣惊人,她说,“我丈夫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持续地证明女人有多么令人讨厌。”此语一出即引起她的女性朋友惊诧和不满。更刺激她们的是,费芙进一步道,“我并不在意,当他告诉我时我笑了。”对于女朋友们的强烈反应,她的解释愈加具有攻击性,“我觉得有趣,因为这是事实,所以我笑了。”接着更困惑惊人的场面是,费芙在朋友面前拿出一管枪朝着门外的丈夫瞄准并射击,对于她们的惊恐尖叫,费芙镇静告知,“他已经走开了。他上楼了。这是我们之间的游戏。我射击他倒下。无论何时他只要听到枪击声他都会倒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倒下地。有一次他倒在有泥浆的水坑里衣服弄得一塌糊涂……”费芙很有优越感地告诉她的女性朋友,互相用枪射击是她和丈夫之间一项持久的游戏,他们是通过这项游戏,这样一种标新立异的方式保持彼此的新鲜感和保持爱的张力。
无疑地,费芙在这个女性沙龙,构建了一个梦幻,一种新的关系,令人好奇也让她的女伴们感受到威胁。
是什么在威胁剧中人和剧外的我们?此中有真相暴露,我们很容易将之变成概念,你也可以把这一对男女间的游戏看成是一种象征,男女之间“战争”的象征,早在50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中,特吕弗在他著名的不朽电影《朱尔和吉姆》中便阐述了这一观点,即使在战争中,男人女人越过炮火线还在互相征服,世界大战结束后,个人的战争还在继续。爱情便是一场战争,由爱生恨,爱恨交错,征服、占有,直至毁灭。
不过,玛丽亚·爱伦的戏剧走向却似是而非,反讽,自嘲,对于情爱关系的根本怀疑,揭示情感的暴力本质,不断带领观众体验崩溃的边界,剧中人物精彩议论一段连一段,比如,“其实人类就是指男人,从男孩长大的男人,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为男人、也就是为人类存在……女人是邪恶,女人不属于人类,她是:1——某种神秘的事物。2——另外一个种类。3——还不能界定。4——不可预知。……上帝给男人的伴侣是女人而不是其他,羊很不错但不能做男人的伴侣。女人是男人的伴侣,所以这是男人必须忍受的苦难——男人的性感受是非精神的,他因此能享受性。他的性欲只在身体产生,也就是说他的精神是纯洁的。女人的精神充满性欲,这就是为什么性交后她们仍然停留在那种狂野的感觉里,因为这正是她们的与生俱有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让她们返回到人类世界是多么困难。性爱的感觉跟随她们直到死。她们带着这种感觉到死后的地方因此而腐化了天堂。于是她们被送进地狱。她们历经痛苦而摆脱了这种感觉,便又成为男人而回到地球。”
显然这个剧本在课堂引起的讨论更加热烈,学生们感到兴奋有趣但毫无愤怒生气之类的负面情绪,他们或她们到底太年轻了,爱于他们是上帝馈赠的礼物,对于女剧作家的自嘲自贬自虐,对于两性关系中的掠夺、占有和挣扎这一面,觉得好奇也有些为难。
我在这样的课堂,感受的是类似于happy的感觉,因为听不到任何批判或界定,戏剧课教授是个希腊裔美国人,来自东岸,也带来了纽约的开放气氛,他的微笑富于魅力,他不断提出问题而不是讲解,几乎是愉快地吸纳所有的奇谈怪论。
知识是无限的,想像力是无限的,探索也是无限的,我正是在阅读和讨论“费芙”这一剧时触摸到女性主义精神的真谛——女性对作为女性本性的怀疑、自省、探索,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后女性主义运动后,西方女性们对于获取所有合法权力已经理直气壮,但更加独立自主的女人仍然无法超越某种困境,不是所有的困境都可以通过社会运动获得解脱,女人有了所有可以争取的外部权利和自由,然而一种基本的关系——男女关系却仍然千疮百孔,女人强大了,却仍然无法让这种关系变得完美,或者说,男女之间无法穿越的黑洞让女人们绝望。知识权力文明,所有时代进步带来的好处都无法帮助女人去超越这一个几乎可以决定她们的人生幸福或痛苦的指标的困境。
女人只能自嘲了。
值得玩味的是,恰恰是知识和文明让女人更有迷失感,然而,我喜欢这种迷失感,“迷失”这一词具有审美性,正是这种感觉让女人在自省和自我怀疑中不停止地探索,让她们的心灵更加丰满。
然而,这认知乃是为文章而用,无济于真实人生的困境。
夜晚,我卧室的电话铃响,显示屏上是A女友上海来电,从上海打国际长途昂贵得离谱,我让她把电话挂了,重新拨通我的网络电话给她,这是我在美国的家里安装的第二根电话线,专门用来打越洋通话,或者说用来援助女友。
然而,回A电话时B的电话进来,B的电话未完C又来了,ABC分别陷入不同却又类似的情感困境,就好像现实在用它的情节起伏颇具悬念的“连续剧”向我提供已经明白无误却不会因此而感受任何知性快感的论点。
先说A。去年离开上海时正遇上她第二次“离异”,不同的是这一次是离开情人,虽然没有法律麻烦,但所受伤害远远深刻于前一次的离婚,因了她的倾情投入。我在她最黑暗的时刻离去而难受,只能用这根电话线弥补。
A年轻时是公认的美女,却在离婚后才遇 “Mr.Right(有译成“白马王子”,其实是与你最般配的另一半)”,对方是他人丈夫,A坚守两年终于不敌对方强大攻势,追求完美的她渐次妥协成了“第三者”,所谓“不伦之恋”嘛,她当然有心理压力,然而对方心态很好,妻和情人在不同城市,他便如同米歇尔·布托尔的男主人公,在“巴黎”和“罗马”之间穿梭,乐此不疲,相当享受,她也不想麻烦自己,迫男人离婚好像做不出,离开他是忍痛割爱也难,如此这般得过且过,抱残守缺,这段情竟也延续了六七年,却在这时发现了“第四者”进入,向来理性甚至比较冷感的她明白此事无公道可讲,无论如何也是到退场的时候了。
却未料到,这个“退”于她却也艰辛得出乎想像,我才发现沉醉于谈情说爱的/TDzD/GhO1ertNSkL9j49A==女人如同吸上毒,这“退场”就像经历一场“戒毒”,几乎需在炼狱走一遭。那时正值我离沪去美之际最忙碌的日子,一边还在主持一个戏剧节,只能是在每一个空隙争分夺秒接听她的电话,或者说,倾听她的倾诉。最后一晚,说服她来剧场看戏顺便与她告别,离去时她在纷乱喧闹的人堆回转头给我的最后一瞥绝望空洞得令我震撼,我是在那一刻感同身受她那种五脏俱焚的痛苦,对自己釜底抽薪地抛下落难朋友而不安,于是夜深回家整理行李,次日出发去机场途中,仍忙中偷闲挂在她的电话线上,直到登机一刻,以致来不及向送机的丈夫交待家务事并遗忘重要东西在家。那个关键时刻我们都没有选择,她在“戒毒”,而我必须支撑她,无意间,我已经在扮演女性主义戏剧的角色。
之后,这支撑只能通过越洋电话继续,看她如此痛苦,我开始劝说她“放弃戒毒”,反正那个男人还要把着这段关系,他哭泣,跪着求她不要离去,奇怪的是,这种时刻,他仍坚持他的“No”,婚不离,新欢,也就是“第四者”也不肯舍,她一百次地问我,为何他可以同时把感情分送几个女人。我冷酷答她,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这么一个品种,你要么接受要么说“不”。
她既然不是男人,只能说“不”。
放下A女友的电话,回答B,她的是婚外恋,对方是单身,这是一段精神恋,在B看来纯真得令自己感动,却不料,昨天深夜还在电话里卿卿我我,今天早晨却从报纸的婚姻公告栏上获知其婚喜消息,一时间觉得之前的一切宛若梦幻,都不敢相信是否发生过。B是烈女,一个人跑到咖啡馆哭了一场,一边删去留在手机上的所有爱的絮语,与他的联系方式。正是这一个毫无防备的挫折让热衷恋爱的B明白,恋爱是“吸毒”,很过瘾是吗?接下来是“戒毒”的可怕折磨,体弱多病的她简直不堪回首这个过程,发誓从此不再去沾这个“毒”。
C是美国女子,为人爽朗富于同情心且母性十足,无疑地,她是女性聚会的灵魂人物,离婚单身的她,最近在网上结识一男士,两人笔谈投机,之后便有电话热线,电话里的男人健谈幽默,作为成功人士,其个人奋斗史十分传奇,这热线电话递送的能量也十足充沛,眼看C陡然风采照人。终于到必须见面的时刻,C很忐忑找我商量,我也不太有主意,直觉是个冒险,说来可笑,我和她一样,所谓的“险”是怕见到的真人“面目可憎”,我俩达成共识,坚决不接受“大肚腩”。
我离城一段时间,回来时被邀去她家聚餐,她那天苹果绿衬衣配淡绿框架眼镜,衬得她的双眸更绿,一双漂亮得极富诗意的眼睛。她在餐桌上快乐宣布,与网恋男友相见甚欢,他们将正式开始约会。女友们举酒杯说着祝贺话,我心里却有些忐忑,中国人的我多一些忌讳,总觉得某些好事刚开始不宜声张,仿佛一说出口便有掉落的风险。但那晚当她抽隙轻声告我,肚腩不算大,未过底线,我也有买彩票中到奖的充满侥幸的欢喜。
几个星期后我们再见面,她那里故事已结束,相见甚欢的约会并未继续,那个曾经浮出海面的男人,突然又消失在茫茫无边的海水中,从此再未露面,就像被海里的鲨鱼吞去了一样。这样的结局从抽象的含义上于我并不意外,因为,奇迹终究不可能发生。让我不好受的是,C变得很委顿,她特有的自信乐观荡然无存,这正是我最怕见到的后果:这段情虽然短暂,C终究被摧残了一下!
当然,无论如何ABC们是现代女子,爱的创伤终会让时间治愈,连受伤最深的A都已经挣扎出来,镇静如常,她的前男友不时有电话进来,他仍然试图挽救这段关系,男人的甜言蜜语已经说不流畅,但共同拥有的回忆却是现成的,说到伤心处还会哽咽,显然有泪掉出,她始终沉默以对,骇然发现自己已心冷如铁,男人怨恨女人比男人狠,却不知女人心的坚硬是因为之前碎裂的记忆,他的“亲密感”的声音带给她的是近似于恐惧的回忆,“戒毒”过程历历在目呢!因此,他愈示爱留给她的阴影愈浓重,他不再明白她了。或者说,男人不明白女人,就像地球上的人不明白月球上发生的事。就像玛丽亚·爱伦在她的剧本中自嘲的,对于男人,女人是另一个种类。
“一场恋爱可维持七年零三个月。三个月的爱。接着用一整年的时间对自己嘀咕,还不错,总算越过了所有的烦恼忧虑。跟着一年里在试着搞清楚什么地方不对了。在两年的时间里明白了这段爱已到结束的时候。再用一年的时间寻找结束的方式。分手后的两年里则一直在试着探究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七年零三个月。然后是新一轮的关系,一样的次序。”
这夸张的断言仍然来自女性主义戏剧“费芙和她的女友”,与我的ABC女友们分享,她们个个忍俊不禁,为了它的寓言式的覆盖力。
现实生活的女人们至少有了这样的共识,每一段情感关系,好像,的确,最值得珍惜怀恋的时光真的不会超过三个月。
这段议论早在70年代便发出,三十多年过去,今天的人不过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出,人的生理机制决定,“激情只能维持三个月!”
于是女人们互相警告,不要再为这“三个月”的快乐付出漫长得多的苦恼乃至痛苦。不要沾染“毒品”,假如谈请说爱像吸毒。
在本剧结尾,这对夫妻的游戏玩不下去了,费芙正在失去爱,“他离开了我,他的身体在这里其余的都离去了,我把他耗尽了,我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我需要他,朱丽,我需要他的抚摸,需要他的吻,需要他这个人,我不能放弃他,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你所看到,那是死亡。是战斗。”
人们又听到枪声,子弹终于射出去了,“我杀死它了……我正开枪……把它杀了……”费芙提着枪和死兔子出现在女友们中间,
是的,费芙射死的是一只雪白的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