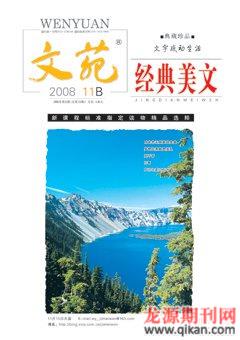狼
陈企霞
……1……
澳门的雾是紫色的。细看时,那紫又很亮。哪样东西一触着了这样的雾,立刻就变成了雾的一部分。云里雾里的感觉,只因为岁月太深。
我正在走向一片大陆的尽头。我知道我脚下踩着的其实是一个岛,很小的一个半岛,然而人更小。以人的渺乎其小,是无法把一片大陆和一个半岛分开的。何况有雾。雾罩得我连一些基本的地理概念都开始变得混淆模糊了。
一些先来过澳门的人给了我一个忠告:要想看见澳门,先得去看那条老街,不看那条老街,等于没来澳门。它不仅是一条街,它曾经是澳门的全部。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澳门街就是那时的整个澳门。
然而它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连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头上盘着辫子、脸孔被太阳和海风轮番制造得黝黑的大清帝国的子民。这些人都是些洗脚上岸的渔人,走下网船开起了渔档,但他们走路的姿势还是在船上的样子,一摇一摆的似乎很长时间都没能克服大海给他们带来的失重感。是他们开创了这条街——澳门的第一条街。街上铺满了漂亮的海螺石,但他们费了很大的劲也没能把这条街修直,一条街蜿蜒曲折得就像海岸线,不过这倒很适合他们一摇一摆地走,一双双大脚丫子甩来甩去的甩得很响亮,整个澳门都有点醉了的感觉。
几个世纪过去了,澳门人还喜欢说这些旧事,只是早已抽去了昔日的情绪,变成了纯粹的故事。这不是因为澳门的健忘,而是因为她的宽容,当所有的恩怨超尘出世之后,华人特首替换葡人总督才有可能更接近于一种仪式,一面旗帜落下卻不见人头落地,一面旗帜升起却不闻枪炮声响起。即使有炮声,那也是在雄壮优美的乐曲声中鸣响的礼炮。连炮也仪式化了。
今天的澳门早已是一个葡华杂处的和睦大家庭,许多葡萄牙人都在这里落地生根成为大家中的一员。随处都可以看见,一个葡萄牙人丈夫挽着自己的华人妻子,宛如神仙眷侣般穿行于中西合璧的大街小巷,而他们手中牵着的那个漂亮小囡,心照不宣的,就使你对“血浓于水”这个汉语词组有了另一种理解方式。
走出那条早已不复存在的老街,雾已渐渐消散。浓重的雾是因为太阳的照射,才呈现出迷人的紫色。雾小了,太阳大了,山岭明亮起来,这样你就可以看见澳门了。
……2……
最早关于这扇门的记载,是明朝的一位官员给皇帝朱载垕的一份奏疏,他很仔细地描绘了这扇门:“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门也。”朱载垕不是昏君,甚至是明朝中晚期少有的一个明白皇帝,一度让明王朝颇有中兴气象。然而他看见了这份奏疏,却看不见他屁股后面还有这么一扇门,或是根本就视而不见。
中国失去了太多的机会,又岂止是后来失去了这个澳门。早于朱载垕登基之前的一百五十多年,郑和就率领大明帝国的远洋船队浩浩荡荡出发了。船队途经澳门,停泊在澳门南湾,郑和豪华的旗舰就像一座建筑在水上的流动皇宫,那时澳门和香港一样,还是个荒凉的小渔村。郑和对澳门同样也视而不见,在他的航海日志里没有出现“澳门”这个字眼。或许他也曾在落日的余晖里回望故国的无限江山,然而在他眼里出现的是江山之间的帝京。
在他身后,一些比他走得更远的人很快就从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纷纷出发了,达·伽马、麦哲伦、豪特曼,这些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一个比一个走得远。荷兰和葡萄牙人在澳门发生的纷争,其实更早就在海上开始酝酿了。荷兰人豪特曼为了窃取东印度群岛航路秘密海图,被葡萄牙人投入了牢狱,而此时,郑和的航海图早已像废纸一样被中国人抛在了一边。
当荷兰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像蹒跚学步一样,从郑和当年泊船的地方上岸时,中国人还沉浸在郑和给他们制造出来的长久的幻觉里,就像有人描绘的那样:古老的中国掉进了最后一个梦里永不苏醒。大清帝国用他刚愎的眼光,轻蔑地打量着这一个个形状古怪可笑的夷人。而夷人们一开始也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他们驾舰进袭澳门,却可怜巴巴地向中国皇帝哀求恩赐给他们一块席子大小的地方,可以睡觉就行了。
于是修史者就有这样得意洋洋的记载:
雍正五年(1724年),葡国使臣麦德乐朝觐雍正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奉呈大量礼物……
乾隆十年(1746年)诏告天下,如今天下太平……
在这样的所谓国史档案之中,你根本找不到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是何时进占中国海疆的,你看见的都是些“葡国入贡”、“荷兰入贡”之类自欺欺人的文字。
中国人看见澳门的时间实在太晚了,晚了好几百年。这座中国南海的国门,如果在郑和的时代就能被人发现而不是视而不见,澳门又是怎样的情景呢?中国又是怎样的中国呢?
历史无法假设,我只能直面眼前残酷的现实,那些我正在走过的或即将走过的街道马路,几乎全都是外国人命名:慕拉士大马路、美副将大马路、荷兰园正街、俾利喇街,葡、荷、英、美、法……就像整个世界突然集中在这个小岛上。小岛因不堪重负,与连接她的故国母土断裂了,一个长达五百年的伤口,以流血的方式唱响了闻一多作词的《Macau之歌》,而当它作为童谣到处传唱时,听起来更像是弃婴在睡梦中的哭声,仿佛是要惊醒她的母亲……
……3……
心情开始变得复杂。我看见了我投在地上的一小片阴影,它趴在地上,微微地颤抖。人在备感压抑时,格外渴望有一个高度。仿佛是神赐,这个念头刚在脑子里一闪,就有一座山奔来眼底——莲花山。
莲花山是澳门的象征。我的第一个感觉不是看见了山,视野里刹那间绽放出一朵莲花,停在半空中央。那是真正的仙境,绽开的花瓣中观音在光天化日之下显形了。在中国众多的神祇中,观音是离大海最近的,她与穷苦渔姑化身的女神妈祖,是中国人的海上守护神。每一个出海的渔人、船工,都把生还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爬上山顶,走进观音殿,我的目光循着观音的视线延伸,延伸至大海。我想看看,一个神仙端坐在这里日复一日地看着什么,除了海,她一定还看见了许多别的东西吧。然而,我能看见的只有海,蓝得深湛的海。我开始确信,海是观音唯一凝望的东西,大海因她的凝望而平静,这也就是她凝望的全部意义。渔人和船工只追求平静,平静是海上生存者的信条。
出了观音殿,绕过一段围墙走进一个缺口,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仿佛某种史前的巨大爬行动物,撅着屁股,昂着头,瞄准了一个方向,大海的方向。那是一门老火炮。我惊悸了一下,没想到莲花之中除了观音还藏着一个炮台。开始我还以为是中国的炮台,看见炮台基脚一侧的洋文,我才知道是葡萄牙人架设的。他们架起这门大炮,自然也是为了守护海上的平静。同样是为了平静,中国人寄希望于一尊泥塑的观音,葡萄牙人架起的则是火炮。我脑中一直很模糊的阴影突然清晰起来,中国之所以陷入那种支离破碎的悲惨境地,除了埋怨那些不中用的帝王将相,肯定还有一些最秘密最诡谲的原因,它就藏在我们每个中国人血液中。
这个炮台已经很老了,作为武器它早已丧失了英勇的含义,炮台上的那些葡萄牙大兵,连同那一场场血战,也早就越出了人们的记忆。但我仍感到被一种空气逼迫,我感到这座老炮台已成为某种信念。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长了嘴的人都会说,可我们是否深刻地理解了,落后的除了武器,除了科技,背后还有更可怕的一种落后?
……4……
葡萄牙人在澳门站稳了脚跟之后,一度把自己弄得越来越亢奋越来越激动,他们也像中国人一样想把通向大海的门关上,还效法中国皇帝在西望洋山一带构筑了一系列城墙,这也是欧洲人在亚洲构筑的唯一长城,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澳门人也称它“万里长城”。
他们在澳门生活得实在太舒服了,生怕别人打扰了自己的酣梦。一座俾利喇行宫,无处不营造出殖民者想要的那种养尊处优的舒适之感。
俾利喇是葡国皇室贵族,澳门保险之家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行宫是一幢南欧建筑风格的宫殿,外墙洁白,圆拱式窗花檐口,大理石砌成的露台和石阶,富丽堂皇的厅堂装饰。我参观得目瞪口呆,想象着这屋里的主人,一定是个穷奢极欲无所用心、终日吸着雪茄烟、喝着咖啡悠闲地打发时光的家伙,一种慵懒的气味呼之欲出。
侵略者和殖民者其实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侵略者充满了进攻性,给人一种尖锐赤裸的力量感。殖民者因生活优渥而惜身爱命,基本上是采取守势,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澳门像俾利喇行宫这样的安乐窝比比皆是,修一道长城也就并非一种无知可笑的现象了,谁又不想将所有的烦恼和隐患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呢。然而固守其实是更大的隐患,在那道长城伫立百余年之后,葡萄牙人猛然发现澳门内港淤塞得水深仅余一米左右,不要说军舰,连他们爱玩的赛艇也开不进来了。如果这时有人从他们屁股后面撵过来,除了跳进大海他们已无路可逃。葡萄牙人因此而惊出了一身冷汗,封闭的不是敌人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拆除了自己筑起来的长城,随后女王玛丽亚二世又宣布澳门为自由港,而那时满清的道光皇帝,却在强征百万民工加紧修复北方的长城,以抵御沙俄的入侵,可是终没能抵挡住汹涌而至的俄罗斯大兵。
……5……
现在我已经走得离大海越来越近了,实际上就是在海上走了。友谊大马路,一条在新填海地上修建的海滨大道,原本就是郑和当年泊船的南湾,葡萄牙人登陆的南湾。穿过这条澳门最年轻的大马路,你就看见了,那是海啊。
澳门三面环海,但澳门人对海的敏感是在葡萄牙人来了之后,澳门人现在每天早晨打开窗户,一闻到那种清幽湿润的气味,马上就觉得,那是海啊。海在空气中,在嗅觉中,在风中,海无处不在,澳门人浑身都是海的感觉。这是澳门被葡萄牙人征服之后渐渐化入了骨髓的体验,他们在葡萄牙人的背后,终于通过大海看见了澳门。
只有远道而来的人,像我,才非要亲眼去看看大海不可,仿佛是为了验证什么。澳门的海就像澳门的雾,是紫色的。
她被晚霞照亮了,但除了霞光似乎还有另外一层东西在她身上燃烧着。
我俯下身来,向大海深处凝视。为了找到一种深度,降低姿态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我看见了澳门,沉浸在大海深处的另一座澳门,一个没有门限制的城市,她四处透明着,鲜艷的鱼群和海藻荡漾穿行于其间,如入无人之境。或许一座城市只有完全融化在海水之中后才会打通无限之路,此时大海即便汹涌也是宁静的。
我在此留影一张,以这片大海和澳门的倒影为背景。照片洗出来后,却少了一片辉煌的幻彩,留下来的只有海,宁静而纯粹的海。这让我多少有些沮丧,毕竟丧失了许多风景,然而我对澳门的理解似乎又深刻了些,她的存在或许从来就不是作为背景而虚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