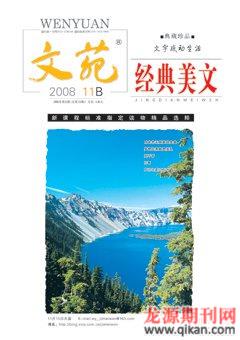谁是该哭泣的那个人
(美)艾琳·凯尔
本文節选自《动物之神》,一个美丽而又残酷的成长故事,一个关于妥协与梦想永不会实现的故事。
因为同学突然溺毙在水渠中,唯一的姐姐突然辍学离家与牛仔私奔,妈妈常年关在楼上的卧房里,而疲惫寡言的爸爸只顾着要挽救岌岌可危的马场,没法照顾她,反倒要依赖她挑起清理马房的重担。
这个夏天,12岁的艾莉丝被迫提早进入复杂的成人世界。
波莉·甘恩在水渠溺死的六个月前,我姐姐诺娜离家出走,嫁给了一个牛仔。爸爸说他当时是有机会可以阻止她。我说不准他指的是什么,是指她还会听话的时候,或者历史上曾经有某个时期,沙漠谷这里维持治安的义警有权力拿着火把追捕她,扯着她的黄头发把她拖回家。在我出生以前,爸爸就担任治安义警,他们好久好久才聚会一次,运行非常重要的任务,例如:清除狩猎小径上坍倒的树木,或从水渠里拖出淹死的小女孩。
波莉·甘恩是在某个星期三的午后失踪。一开端大家说是绑架。但是他们在水渠旁的泥巴路上发现她的背包,马上打电话找我爸爸。义警花了两天时间打捞河渠。他们把白色小礼服衬衫与黑毛毡牛仔帽换掉,穿上可穿到腋下的橡胶涉水装,肩并肩走在褐色污水中。我放学途中还曾经过他们。才四月,蜉蝣却已在水中孵化,我看到爸爸用力从脸上赶走它们。我在水渠旁挥手喊他,而他一脸紧绷没看我。
“我们今天找到那个女孩了。”隔天下午他回家后说。我正在水壶里冲泡果汁饮料,他用手指蘸了一口来舔。“卡在铁栏杆上。”
“她死了吗?”我问。他瞪了我一眼。
“艾莉丝,你走路回家时,不要靠近那条水渠。”他说。
“会办丧礼吗?”我想象自己如电影中的女人,穿着黑色洋装,戴上厚片墨镜,站在坟墓旁,难过得哭不出来。
“你那么关心干吗?”
“我们工艺课是同一组,我们在做灯笼。”事实是,波莉做灯笼,我在旁边观望。她从头到尾都没有计较,麦克拉斯基老师走过时,她让我提着灯笼,这样他会以为我也在一起做。
“我没有空带你参加丧礼,艾莉丝。”爸爸说,手放到我头上。“家里的任务实在太多了,我已经用掉了两天时间。”
我一边点头,一边用木勺搅拌饮料。任务永远做不完。爸爸经营马场,除了义警召集之外,他还教人骑马,育种养马,然后把马卖给用手喂它们苹果切片、喊它们“宝贝”的人。早晨天还没亮,爸爸跟我就得喂马,接着我走路去学校,在半路上先甩掉头发与衣服上的干草,拍去粘在衬衫前的碎片。到了下午,我们清空马厩,照料并锻练马儿。现在正值小马出生的时节,母马随时都可能会生产,爸爸连一分钟也不能退出马场。也好,反正我没有黑色洋装。
“孩子,你向来任劳任怨,”他说,“等姐姐回来之后,生活就会安稳下来。”
他总是这样,相信姐姐会回来,日子会回到从前的样子。有一阵子我怀疑他说的会不会是对的。那件事情发生得太快了,诺娜在星期天认识杰瑞,下个星期四她就打包好四个箱子与一只背包,坐上他的小卡车走了。杰瑞在巡回各地的牛仔竞技会上表演骑野马,跑到堪萨斯州的法院跟姐姐结婚。爸爸说,杰瑞总有一天会因为骑野马而摔断脊椎,诺娜到老都得用轮椅推着他、捧杯子接他的口水。爸爸认为婚姻不适合她,她才不会满足于自己的人生只是站在竞赛场外为他人喝彩。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诺娜的来信中依然画满了笑脸与惊叹号。她说,跟巡回参加马术表演赛相比,牛仔竞技会太美好了。她和杰瑞晚餐都吃牛排,在汽车旅馆过夜,日子舒服多了。我们参加马术表演赛则是啃燕麦棒、喝汽水,陪着马匹睡在马厩,这样马儿才不会在晚上被人偷走。
她来信的收件人总是我,头一句是“艾莉丝宝贝”,末尾写着“向爸妈转达我的关心”。我会把信放在厨房料理台上让爸爸看,而他几乎从来不看。几天过后,我会到妈妈房间,把信朗读给她听。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几乎都待在卧室里。诺娜说我们还没出生前,妈妈曾是马术表演赛的大明星,四处获奖,连照片都上了报纸。她说我还是个小婴孩的时候,有天妈妈把我交给她,说自己累了,接着上楼休息,从此再也没有下来过。
我常坐在床上,借着电视屏幕发出的蓝光,为她朗读诺娜的来信。她会拍拍我的腿说:“很好,听起来过得很好啊,对不对,艾莉丝?”
我习惯用嘴巴呼吸,免得闻到她苍黄皮肤发出的酸湿体味与油腻发味。妈妈要我讲出每封信的寄件城镇,叫我说说看我认为那是个怎样的地方。在我的想象中,牛仔竞技会在干燥、满是灰尘的城镇举办。但是我努力发挥创意:内布拉斯加州麦格古镇的每条街上都有一排栗子树;伊利诺州马里安镇的落日是紫色的;密苏里州西肯斯顿镇有座公园,正中央的池塘能喂鸭。再变不出花样时,我就说我要回房了,或者得去马厩帮爸爸。然后我溜出房间,随手把门带上。
爸爸说诺娜退出后,算我们走运,因为出现了熙拉·奥特曼。她住在沙漠谷的另一头,就读的崭新学校里头有计算机和空调。熙拉·奥特曼有双蓝眼睛与一副轻柔的嗓音,经常把“可不可以……”还有“你介不介意……”挂在嘴边,从不忘记说“请”与“谢谢你”。我很想一把扯下她婴儿般细柔的头发。每当她妈妈开车到我们家之后,熙拉就冲到马厩亲吻马儿,拿家里带来的红萝卜喂它们。奥特曼太太会拿着相机与支票簿下车,望着女儿匆匆忙忙钻进马厩。“噢,温斯顿先生。”她说,“你今天的任务安排好了吗?”
奥特曼太太告诉爸爸,她过去几年中花了几千美金,送熙拉到骑马营,让她在那里把某匹马当做自己的马一个星期,喂养它、照料它,还清扫马厩。我爸爸打趣地说,他可以只收一半的费用让熙拉清空他的马厩。当奥特曼太太惊讶地倒吸一口气,说:“真的吗?”他回答得干干脆脆。
“这个小女孩嘛?”他说,“当然是真的。”从此,每日放学后,奥特曼太太从山谷另一端开车载熙拉过来,付钱给爸爸,让她照料我们的马匹并打扫马厩。熙拉在的时候,爸爸精神奕奕,神情轻松愉快。他告诉她,她做事勤奋,没有她,我们不知道怎么才好。她走了之后,他就摸摸我的背说:“艾莉丝,那女孩要怎样,你就让她怎样。对她讲话要客气。熙拉·奥特曼是我们的饭票,而且她不像你姐姐性情不好。”爸爸总说诺娜的嘴巴很坏、忘恩负义,说的时候,脸上却常是流露出笑意。她生气的时候,脸绷得又紧又硬,像会从眉心迸裂成两片。
爸爸说我不爱表现,其实他是客气了。他真正的意思是──我没有天份。
而诺娜一个人就抵得过我跟爸爸两个人。她对裁判时而微笑,或者笑容可掬,要不然就是眨眼睛。在跑马场外,她让小女孩从看台上下来,坐在马背上面,一面示范缰绳的拿法与脚的位置,一面朝着孩子的父母说:“你有天赋耶!”接下来,她堆满笑容对那孩子的妈妈说:“我爸爸有开课,你们应该改天过来看看。”
小黄帽是爸爸买给她的最后一匹马,是巴洛米诺品种,站在跑马场中,它是跑得最快、最高大、最亮眼的马儿。我头一次见到它时,心想它肯定会让诺娜没命,但姐姐却轻而易举地骑上去,轻轻晃动缰绳,说:“好乖。”小黄帽的脖子一弯,身躯一收,便和姐姐一同绕着练马场跑起来,有如在聚光灯下。爸爸跟我们潜在的客户在场外观看,他说:“只要她开口的话,那匹马,甚至连水面上也能行走。”
波莉被爸爸从水渠拉上来的隔天,我们没上工艺课。全体六年级同学被带到体育馆,校方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然后叫我们回家后跟父母讨论我们的感受。
我回到家时,爸爸站起来,脸色红通通,嘴巴紧抿。“你妈哭了一整天了。”他看见我,劈头就问:“你跑到哪去了?” “上学啊,不就跟平常一样。” “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盯着双脚。“你现在上楼去,跟她好好讲几句话,告诉她你非常爱她,让她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回来帮我,这里事情多到忙不完。想到这里有这么多事要做,我就烦死了。”
我看着他。诺娜不会回来了,永远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