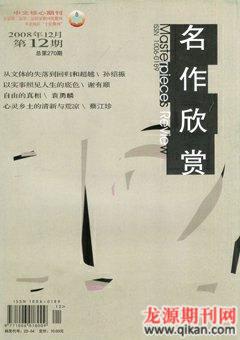国人之吃
孙绍振
1.孟夫子引告子言:“食、色,性也。”在那生活条件很简陋的年代,能把吃饭和性事坦然地当作人生两大支柱肯定下来,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的洞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在孔夫子死后几千年,就一直弄不清楚。直到五四运动期间还要劳鲁迅的大驾庄严地宣告一番: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生存,就是吃,发展,就是性。但是,孔夫子是有些矛盾的,他偏偏要把对于女性的爱好和道德对立起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圣人说了,凡人当然不敢违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女性,尤其是美人是有高度警惕的,对于性爱最爱做出一种厌恶的样子。所谓“万恶淫为首”者是也。但是,对于人性的另一种需求,吃,中国人却十分宽容。民以食为天,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吃饱肚子。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中国。毛泽东比起他的战友和敌人来,高明之处,就是深刻理解这一条道理。早在五四时期主编《湘江评论》的时候,就坦言说:“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君不闻,谚云:开开门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与口腹之欲有关的,才与人生之真谛与革命之大业有关。不能领悟这条最普通的真理,就不能洞察中国的人情世故。
吃这个字,从口,本来是表意的,本义是口腔,有发声和进食两种功能。但是中国人好像更重视吃的功能,一百天不说话无所谓,十天不吃饭,就活不成。早在甲骨文就有“口井”,计口分田,井田制,到了第一部字典《说文》中就干脆把发声功能排除了:“口,人所以言食也”。实际上在许多圣贤典籍中,口就等于是人了,《孟子•梁惠王上》:“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于是就有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词语创造:人口。人就是口,口就是人。好像人只剩下了一张嘴,除了嘴巴什么都没有了,连脐下三寸都成了空白。
从“人口”这样意味深长的构词法引申开来,顺理成章,就产生了“户口”这样的词语。这就是说,吃饱肚子,不仅仅是单个人的头等大事,而且对于维系家庭,巩固社会秩序也是根本大计。中国人向来是讲究含蓄的,在这里却并不羞羞答答,对于胃肠功能的急迫感丝毫不加遮掩。连夫妻两个都叫做“两口子”,在英语中,husband和wife和mouth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中国人把什么事情都和吃联系在一起。一般草民,问他什么职业,回答说:吃xx饭的。好像除了吃饭什么也不干似的。旧时上海一些流氓,坦然宣言自己是“吃白相饭的”。“白相”,是上海话,就是无所事事,整日游逛,当然是没正经的意思,但是一和“吃饭”联系起来,就有正经职业的意味了。西方留学生在中国学中文,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用大碗吃饭,叫做“吃大碗”,到食堂吃饭,叫做“吃食堂”。他们的想象力不行,无法解释食堂被数千乃至上万大学生咬噬多年,仍旧傲然挺立。他们更不能理解的是:家住农村,青山绿水之妙不在养眼,空气新鲜之优越,不在养肺,而是有利于口腹之欲: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水的样子还马马虎虎可以想象,无非是嘴巴张得大一点,比之抿嘴一饮那样,不够文雅一点。吃山的姿态,就真有点可怕了,恐怕连恐龙都不可企及。
这不能说明中国人特别馋,相反,吃在汉人心目中,绝对不仅仅是口腹之欲,而是与人的生命质量息息相关的。精神品味档次最高的人物,叫做不食人间烟火。屈原的品质是高贵的,所以他吃的东西就不一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西游记》上,妖怪要成精,要食“日月之精华”。品质特别恶劣的人叫做“狗彘不食”,而特别凶残的人,叫做“吃人不吐骨头”。
我小时候,在上海的青浦读小学,对于极其厌恶的家伙,喜欢在墙壁上写标语加以愤怒声讨:最常用的一条是:“某某某吃卵三百只!”这个卵,不是鸡蛋的意思,而是男性生殖系统中最突出的一部分,水浒传上和闽南话中都写作“鸟”,粗话叫什么,大家都知道,不便写入文章。现代汉语中,近来,有了一种昵称,叫做“小鸡鸡”,或“小鸟鸟”,正如,小哥哥,小妹妹一样。汉语的单音词语,一旦重叠起来,就有幼小、可爱的意味,排排坐,吃果果,改成排着坐,吃水果,就煞风景了。当然,任何规律都有例外,花花公子,花花太岁,花花世界,就是。当然,昵称,在俄国人中也通行,只有在很亲近的人之间才通用。例如,列宁同志自己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而家里人的昵称就叫他“伏洛加”。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多少文化,想象不出文明的爱称的各种花样,以至于这种以数量上要达到“三百只”才满足发泄私愤的口号,居然从男生普及到女生中去。不过女生并不确切了解其中关键词的外延和内涵,却也常常偷偷地写在厕所里,男生则冠冕堂皇地写到对方的大门上。但是,这也并不完全是孩子的淘气、野性,而是有中医中药的根据:胃有病,胃壁溃疡吃鸡的胃内壁,学名叫做“鸡内金”,阳痿要吃动物的外生殖器,中药学上的正式名称曰:牛鞭、鹿鞭;据说,更有效的是老虎的那一鞭,但是,不如狗鞭,但是,据说,虎鞭是带钩子的。
吃不但意味着人的生理功能,而且可以阐释人的心理素质,胆子大叫做:吃了豹子胆的。所以到了拚老命的生死关头,往往就和吃有联系。例如,义和团攻打使馆区东交民巷,勇士们的豪情就这样表现:
吃面不搁酱,
炮打交民巷。
吃面不搁醋,
炮打西什库。
献身革命,意志坚定,也与吃有关,三十年代在红色根据地,有民歌曰:
要吃辣子不怕辣,
要当红军不怕杀。
革命者的视死如归的英风豪气和吃的联系一目了然。这种革命胆略,永远是不会褪色的。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思想要解放,要冲破“两个凡是”。有些当年吃过辣子不怕杀的革命干部,却失去胆略。据当时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同志对于缺乏思想解放勇气,前怕狼,后怕虎的战友,十分藐视,他追问说:“你怕什么?怕他咬了你的鸡巴!”话说得虽然粗了一点,但是,却符合汉语的集体无意识中把人的精神状态与食物联系在一起的规律。当然,“咬”还不等于吃,但是,肯定是吃的一种前奏,而且在用力的程度上,也就是在情感的强度上要比吃动作性更大一点。
吃有时则用来表述“个人”问题上的奥妙。我在昆山念中学时,班上有个男同学,同时和两女同学谈恋爱。一个密友私下问他,你究竟要哪一个。他的回答很平静:
“两个全要吃吃。”
最富于情感的成份的要算“吃醋”,男女都吃,但是女人吃得更认真,有时把小命都吃掉也不后悔。林黛玉的大部分审美情操,都由吃醋而来,自我折磨,自我摧残,才这叫做美。不吃醋的薛宝钗,虽然身体健康有利于生儿育女,从美学意义上说,是空洞的。
吃不仅仅有关虚无飘渺的情感,而且是全部生命的体验,在艰难的条件下工作,叫做能吃苦;空想改变现状,不切实际,叫做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癞虾蟆没有翅膀,不能飞,当然吃不到,但不排除意外的好运,有歇后语形容曰:“癞虾蟆吃糖鸡屎——笑眯眯的”。这种“糖鸡屎”并非真的有糖,而是鸡拉的稀,不过颜色像是调了红糖的。
在汉语里,阐释人的命运也由吃来承担了。苏南地区1949年前,有谚语云:“牛吃稻草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牛的劳作是艰辛的,但只能吃草,而什么劳动也不会的鸭子,明明是二流子,却一心想当歌唱家,不择场合练嗓子,以折磨人的耳神经为职业,却得吃比较高级。这种命运的不公,是以吃为衡量标准的。而鸭子虽然成天歌唱,但,总有一天,要抹脖子,其精心包装在椭圆的壳里的后代要被拿到油里去煎,水里煮,就不在比较之列了,因为这与他们所吃的食品无关。
因为吃与命运有关,所以吃的语义就和人的一切成败得失联系在一起,外部形势严峻,或者手头的钞票不够用,叫做吃紧。吃一堑,长一智,用吃来形容倒霉与智慧之间的正比关系。对于外来的横逆,威武不屈,叫做不吃这一套。吃香,吃得开,说的是广泛受到欢迎和尊重,通吃,则已经超越了赌场上的含义,成为全盘胜利的概括,而吃亏和吃瘪,不但是遭遇挫折,而且是丢脸了。
2.这可能是中国汉人,属于农业民族,又有强调子孙繁衍的传统,人口增长迅速,土地不堪重负,满足饮食生理需求的压力相当大,吃饱肚子的问题解决起来很不容易。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饮食文化,特别奇怪,什么都吃。饥荒年月,树皮、草根、观音土,都是果腹的佳肴,平时连蛇和蝎子都不放过。婴儿的胎胞和癞虾蟆的卵巢都是补品。
就连小便,也是可以吃的。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记忆。
那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家逃难到乡下。有一天,吃完晚饭,我被叫到房间的当中,一向严厉的爸爸,破天荒让我站到桌上去,并且拿了一个相当精致的瓷碗放我面前,要我在把小便拉在里面。当时我四五岁,已经模模糊糊感到代表男性的尊严的那一器官,是要严格保密的,不能示众的。不能像小狗那样在大庭广众之间,随便抬起腿来方便,只能偷偷地在墙角。突然间,要我当众把它掏出来,众目睽睽之下,岂不羞死我也。然而,父命不可违。而且那么多人的眼睛,都放射出期待的光。我勉为其难迟迟疑疑掏了出来,但是,就是拉不出。父亲鼓励再三,仍然无效。最后还是妈妈理解我。说:孩子害羞,大家把眼睛闭上。这一下真是有如神助,碗里顿时就满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给一个很可敬的叔叔吃的,他得了一种病,中医开了一贴药,要有一种药引子,叫做“童便”。我不能想象,那位可敬的叔叔在喝我的小便时,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得到了解释,因为儿童,具有绝对的童贞,故有救命之功效。我当时并不担心,我的童贞被他吸收了,对自己会造成什么影响。而是想到有朝一日,自己长大了,也得了这样的病,不知又要去喝什么样的小孩子的尿。这种恐惧已经够呛。更可怕的事还在后面。有一次上公共厕所,那时没有冲水设备,小便池里臭气熏得眼睛都睁不开,池里积了一层厚厚的垢。突然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挑了一担水来,三下两下把小便池冲洗得干干净净。我不禁对此人投以崇敬的目光。他却目不斜视,只顾用一只蛤蛎壳去小便池里刮,每刮一下,那壳里的尿垢就满了。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这是药引子,叫做“人中白”。我不免像水浒英雄们那样“倒抽一口冷气”。没有想到过了几年,听一位中医说:还有一种药引子,叫做“人中黄”,是大便的积垢。那时,我已经从母亲那里获得一鳞半爪的人生是作孽的佛学,起初总是有点怀疑,得知这一切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佛学的精深。
然而,这还不够我灵魂深深震撼的,等到阅读能力提高可以读点古文的时候,才知道,在最为严重的饥荒年岁,吃人肉的事情也是有的,春秋战国时代,易子而食,折骨而炊,在历史上有记载的。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母亲,要把他们煮成羹汤,逼迫刘邦就范。从这里可能看到一点吃人肉的习俗。直到唐代,在白居易的《秦中吟》中还提到“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灾荒年头如此,平时是不是就绝对不沾人肉呢?至少《水浒传》上就有一位女英雄,丈夫叫做菜园子张青,看来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可就是这位农民的老婆,绰号母夜叉,开饭馆,专门卖人肉包子,还差一点把打虎英雄武松给放翻了。幸亏武松机灵,才避免了一身结实的肌肉变成她的瘦肉馅。
我在一本英文的读本上看到一个英国人的感想,她说,英国自从光荣革命以来,三百年来就没有国内战争,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封建王朝都是在农民战争的烽火中倒塌下去的。我想此话有理,差不多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为争夺土地而流血。为了满足胃的需求,不惜把脑袋丢掉。插起招军旗,不怕没人来吃粮。故李闯王造反时,民谣曰:“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不过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竟能建立王朝,开基立业,横行在江南北十余年。而上个世纪50年代拍摄的《宋景诗》,属于其支流黑旗军。在进攻地主土围子柳林团之前,黑旗健儿们唱道:
打垮了柳林团哪,
有吃又有穿哪,
黑旗小子穷光棍儿,
娶个媳妇不作难哪。
先杀王二香哪,
再杀韩鸣谦哪,
东家财主,
齐呀么齐杀完哪,
过个太平年哪。
充分表现了杀气腾腾的英雄气概和吃饱肚子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这位英国女士的意见,我想也不太全面,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中国又是一个文明礼仪之邦,特别讲究饮食文明。钟鸣鼎食,悠扬的庄严音乐,把血淋淋的凶残推向幕后,像《左传》中描述的那样,跪、拜、登、受,一套套规矩,把本能的争夺变成转化为精神的殿堂。推杯换盏,多少杀机因此而遮蔽,勾心斗角的胜负,全在举杯的分寸之中。就是严峻的军事斗争,人头落地在须臾之间,饮宴的仪式也不越规矩,鸿门宴上,项庄舞剑,表面上是娱乐助兴,但意在沛公的脑袋,樊哙本是对项羽杀气腾腾,刀光剑影,都因饮宴的仪式而超越了杀机。项羽反而赏赐给一大块生猪肉。这位壮士,就拿自己剑割着大啖。饮宴仪式以中规中矩为特点,多少勾心斗角的伎俩变得文雅而神圣,血淋淋的历史,反而成为千古佳话。唐太宗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你死我活地争夺皇位,李建成阴谋杀死李世民。想出来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在出兵时阅兵的饯行仪式上,于饮宴之中,“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结果,未及等到仪式开始,李世民先发制人,兄弟相残,李世民亲手射死了亲兄弟,血溅玄武门,令司马光为之扼腕不已。至于赵匡胤登了大宝,为了防止功高盖世的大将兵权太重,重演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悲剧。如果鲁莽地把大将们的兵权一把撸了,可能引起一场混战,他却来个“杯酒释兵权”,和哥们儿来一场盛大的宴会,文文雅雅地把隐患给消除了。到了元朝,,在关汉卿的笔下,关云长飞舟过长江去东吴单刀赴宴,面对那滔滔的长江,他不禁感慨:
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饮食的仪式性,使得饮食的口腹之欲具备了一种高雅的装潢。这可能是汉族人的特点,而满族就不同,他们入关为主,建筑承德山庄,和关外的少数民族会盟,主要就不是吃喝,而是狩猎,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达到情感的沟通。而汉族人不但用酒肉和政敌周旋,就是对仙逝的祖先,最隆重的就是以热气蒸腾的猪头三牲奉献。西方基督教世界扫墓,多用鲜花,而中国人则祭以食物。清明节墓台上红烧鱼与香蕉并呈,白米饭共巧克力相叠。说是祭祖,实际上是自祭。《孟子》中的齐人,就钻了这个空子,到人家坟间去吃人家祭祀的食品,满嘴油光光的,居然能混到了两个老婆。在明清之际,清明扫墓间直就成了美食节。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扬州清明,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辞往复。监门小户,亦携肴核纸钱,走至墓所。祭毕,席地饮胙。”这里的肴核,是菜肴的总称。而饮胙,则是一种古礼,饮是饮祭神的酒,而胙则是祭神的肉。不管是神还是祖先,绝对是不吃任何一点东西的,不管多么丰盛的菜肴,最后都进入了自己的肚子。饮祭神的酒,叫做“饮福”,吃祭神的肉,叫做“受胙”。也是承受福荫的意思。
以饮食的仪式来沟通冥冥之间的妙招,不但在后代与祖先之间,而且在人与神佛之间。祥林嫂视为性命交关的“福礼”,其实就是一条大鱼而已。家神吃得痛快,才有好心情保佑你发财发福。中国人很重视过年,从腊月二十四就过“小年”,首先要祭的是灶神。这个神,不但日日监视你家的伙食,而且每年要回到天上去汇报,对你一家的品德行为作出评价。为了贿赂一下这位玉皇大帝派在身边的特务,在他即将上天汇报的时刻,给他狠狠地吃一顿。临了还给他吃一块灶糖,其实就是一块麦芽糖,很粘的,让他到了玉皇大帝那里,就是有坏话,也讲不出来。可是,我父亲,偏偏又写了一副对联:
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
我想既然嘴巴被灶糖粘住了,坏话讲不成了,好话,不是也不能讲了吗?后来,又想可能是到讲好话的时候,就把糖吐出来,或者赶紧把它啖了。好话就滔滔不绝地讲个没有完了。但是,吃人家的东西嘴软,形同受贿,岂非有负于玉皇大帝的信任?
我怀疑,这和西方基督徒有点异趣,基督教每周的“主日”(即周日)有这样的聚会,叫“擘饼聚会”,意思是纪念基督的死与复活。基督徒吃的面团,象征神的身体,饮的酒代表神的血液:《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如果在教堂的神坛上,将中国祭祖宗的猪头供上,不知基督是否宽恕亚当后代的罪行。
这个问题,我不敢问。因为父亲早就警告过,小孩子,过年时期,胡言乱语,是要破坏神佛的情绪,影响一年的运气的。父亲对我的嘴巴,不大信任,写了一御防性的条幅贴在墙上:童言无忌。但是,到了年三十,我还被强制性用上厕所用的草纸,擦了一下嘴巴。也就是请神佛把我的嘴巴当作肛门,我讲的话,当作肛门里放出来的臭气。但我并不服气。我所讲的话无不出自我的童心,不论按李贽还是卢骚,都是最纯洁的。而灶王爷,却是吃了人家的东西,就报喜不报忧。品德上多多少少有些污点的吧。发自纯洁的童心的话语,如巴金所追求的讲真话,反而是放屁,而贪吃的下放神仙,却享有神圣的尊荣。这世道真是有点让我满腹狐疑。
3.中国人对于吃的豪情和对于女色的警惕成正比。
《三国》《水浒》《西游》中的英雄对女性不是没有兴趣,就是有些仇恨的。不管什么盖世英豪,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但是但凡犯了一个色字,就一世英名丧尽。故关公、武松、孙悟空乃至诸葛亮、吴用对异性一概没有什么感觉,不管是什么档次的英雄,一旦沾上了女色,就显得十分可笑可卑。猪八戒一见女性就流口水,吴承恩,利用一切机会,让他出洋相,这还不算,还给了他一副猪脸,让他应了一句俗语,叫做丑人多作怪。但是,中国古典传奇中的英雄主义在色方面受到压抑,往往就向吃喝方面发泄。武松景阳冈打虎,英名盖世。为了表现他超人的神勇,先让他一口气喝了十八碗酒,外加几斤牛肉。武松醉打蒋门神,不吃不喝不见英雄本色,吃喝而不醉,更不能现出武艺高强。关公斩华雄,如果没有那杯砍了人头还没有凉的酒,肯定是大煞风景。
有多大的食量和酒量,就有多大的英雄气概。二者的正比关系,是经文学经典一再不嫌重复地加以证明的。
这在西方人看来,还真有点隔膜。他们中世纪的英雄,主要是骑士,其英雄气概和把生命献给美女的自觉程度成正比的。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味吃,而忽略了美女,是野蛮的。他们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做饭上。正是因为这样,快餐、汉堡包,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地吃,才充分表现他们的民族性。而在中国人,尤其是圣人之徒看来,这么简单草率,简直是荒唐。孔夫子云:“肉不正,不食。”所以中国的厨师,讲究“刀工”,显示其富有圣教的文化底蕴。
把吃看得很庄严,这是中国文化的光辉传统。
虽然中国文化发源于北方黄河流域,但是,对于饮食的考究,南方人却是青出于蓝。广州人在爱情上,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别表现出骑士精神,但是,全中国都知道,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州人什么都敢吃。这实在令北方人肃然起敬。可惜的是,吃到果子狸,吃出非典,弄得北京、上海、福州、杭州、南京,道路以目,公共汽车上人烟稀少,而广州大马路上依然是熙熙攘攘,一个个面不改色,心率正常;其慷慨的程度,不亚于水泊梁山上聚义厅去赴宴。比起广州人来,福州人,胆子小一点,但是,一生花在做吃上的时间,消耗掉的生命,可能是北方人的好几倍。福州人和广州人一样讲究美食,美在吃出花样来,以至于食本身倒无所谓,要义在超越口腹之欲,升华为一种美学。光是口腹之欲,就是好吃鬼、贪吃婆,超越了,就有一个挺文雅的说法,叫做美食家。福州人一讲起锅边糊,一讲起蛎(方音读de)饼,就流口水,这不是馋,而是对于乡土文化的热爱。乡土感情,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就是到了美国,在纽约定居了两三代,还是不改。在唐人街,早上可以用福州话买到蛎饼。虽然讲广州话在纽约比英语还难懂,但是广州人的自豪在旧金山,在餐馆里,用广州话可以买到蛇羹。当然东北人,一听到蛇,就想起那粘滑的皮,还有那毒牙,不免有点汗毛孔竖起来的感觉,不要说吃了。但是,他们那里的猪肉炖粉条,也是一绝。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老乡坚信,一吃了这玩意儿,就能成为活雷锋。这是有一首流行歌曲为证的。
这就是所谓乡土风味,一说到乡土,感情成分就浓烈了。有道是:月是故乡明,猪肉炖粉条是家乡的美。
虽然英国人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词语叫做:nostalgia,翻译过来叫做怀乡病,但是,他们没有明确说,他怀念家乡的什么,可是我们中国人,就很坦诚,怀乡就怀念家乡风味的食物。当然,生活在天堂里的苏州人,正如孔夫子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再加上食品的名堂用吴侬软语那么一叫,正如霓裳羽衣曲一样令人飘飘欲仙。东北老乡的猪肉炖粉条就太土了。但是,苏州人也洋不到哪儿去,早在晋朝,阊门出了个张翰,在洛阳做官做得好好的,突然秋风起来了,想起了家乡的鲈鱼莼菜,口水就流了下来,连官也不要做了,回家吃鲈鱼莼菜羹去了。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特别重,别以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感情,这里边包含着口腹之欲。吃的最大特点是怀旧,鲁迅从东洋归来以后,又到北京,吃了多少山珍海味,居然,在《故乡》中坦然宣言他儿童时代吃的罗汉豆最好吃,郭沫若从日本岗山医学院毕业,来到上海,成了大诗人,居然最令他念念不忘的是四川凉薯。
可见所谓怀乡实际上是一种怀旧癖。
和口腹之欲相比,性欲的动作就有点粗鲁,谈不上多少怀旧的诗意,肢体语言则更简洁明快,但是性欲的特点不是怀旧,而是求新,没有见任何一个人的乡土观念是固定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就是我们的革命干部,也未能免俗,战争胜利了,乘着新婚姻法颁布,大都把往日的糟糠之妻离了,带着大城市的女学生荣归故里。这一点似乎不是中国民族特色而是人类的共同性。拜伦在欧洲旅游,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陷入一种如痴如醉的爱情,不断地更换新的恋爱对象,歌德到了八十岁还不断在恋爱方面求新。喜新厌旧成了中外男性的通病。如果要评比的话,克林顿会成为当之无愧的代表。这可能是因为,食物之美,可以历年不变,而异性之青春却与年龄的递增成反比,美色很难以永葆。
不过人性总是进化的,这几年,据中国大城市某些敏感的女性观察,又有了发展,她们的先生,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喜新厌旧的恶习,以喜新不厌旧的姿态,在新与旧之间取得平衡。有诗为证:
外面红旗飘飘,
家中红旗不倒。
2004年7月18,8月6日修改
(选自《山花》, 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