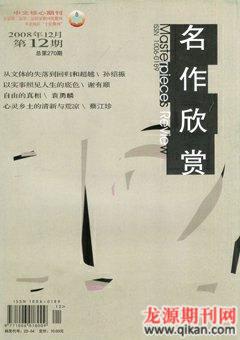“小地主”
它歪着脑袋,嘴巴向上翘成45度角——我看不出恐惧和紧张,它的表情就像在示威。可以肯定,这是一只雏鸟,因为它的神态太天真了,有种孩子式的任性。我初见到它时,它正扑腾着翅膀,累得气喘吁吁却收效甚微地停在大树底下。我不知道它是急于成长趁父母不在就翻窗跳出家门,还是太过淘气,总在试飞练习中逃课才造成今天的危险局面。我弯腰捡起它,它用小翅膀用力拍打着我的手,并发出带着感叹号的抗议,非常反对。如同外婆威胁童年的我“大灰狼来了”以使我听话,我教育它说:“别动,有猫!”
它的体形比麻雀大,羽色黑灰,我们宿舍为它的身份争论起来,有的说是喜鹊,有的说是乌鸦。我总结,说它是乌鸦的人肯定出于嫉妒。我相信每个人都愿意拥有救助小鸟的机会,只不过这次的幸运落在了我头上。我从感情上不希望它是乌鸦,也许这鸟类看来是种族歧视的表现。面前摆着小米、菜叶和清水,可它不吃不喝,就在那儿歪着脖子生气,也不知道是生自己的气,还是生我的。我质问它;“凑合吃吧!难道想让我给你满处捉虫子不成?”它一翻白眼,还是不领情,干脆转过头不理我了。根据它的脾气和对食物的挑剔,我给它起名“小地主”。
为了让小地主进食,我在洗干净的眼药瓶里装上牛奶,然后我拿着它,像一枚导弹一样向它挤射过来。小地主不知何物,大叫一声——它一张嘴,牛奶就灌进去了。我怕热量不够才放的牛奶,我想大象都能靠喝奶长大,何况你这么个小东西。书上说幼鸟在发育期食量惊人,母鸟辛苦奔波,才能勉强满足它们的胃口。如今,让我像个保姆似的代劳了。由于小地主不配合,吃饭的时候,我不得不找一个人专门掰开它的嘴,我往里填,它吃得满脸都是。它昂着半只眼睛已被糊住的小脸,气愤地盯着我。
我们宿舍被包围了。高高低低的树杈上,站满数十只灰喜鹊,不仅父母,连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也来了。小地主一看家里来了人,马上趾高气扬,一声又一声地叫起来,也许是告我的状,反正听了它的一番陈述,灰喜鹊们纷纷声色俱厉地指责起来。为了破除扣押人质的嫌疑,我打开纱窗,让小地主自由地站在窗台。显然窗台与树枝之间的距离超过小地主的飞行能力,它张开翅膀,呆了一会儿,又理智地收拢了。灰喜鹊家长们似乎不再怀疑我的清白,当我把小地主重新拿进房间,它们没有表示出什么激烈的举动。
灰喜鹊这种鸟相貌优雅,胸部是柔和的灰蓝色,还拖着长长的动人尾羽,只是叫声高亢、粗实,甚至带点儿沙哑。它们轮流看望小地主,问寒问暖,虽然亲情可以理解,但是制造出一片喧哗——读书看报的事儿在我们宿舍是进行不下去了,午休的美梦就更别想。为了不影响其他人休息,我只好每天中午把小地主带出来。烈日下,我在空无一人的校园操场上无奈地散步,头顶时常有几只灰喜鹊飞来飞去。小地主四处张望,满腹阴谋。一次,小地主格外乖巧,后来我才发现事出有因,它竟然在我兜里随地大小便——它使我成为一个有味道的女人。我一边走一边跟小地主聊天,一个星期下来,使我认同这种说法:牙都被晒黑了。
回宿舍之前,我每天都先到顶楼阳台上站一会儿,看看小地主什么时候敢于飞到那些高大的法国梧桐上去。树冠就像一只巨大而柔软的绿色摇篮在下面接应着,我期望小地主能从中得到信心的鼓励。小地主好像忘了怎么飞似的,再也没张开翅膀一试。把它带回家,我却总怀有一种侥幸的甜蜜:它还需要我的照顾。
小地主的离开非常意外。它在窗台上晒太阳,我在旁边读书,不知是小地主的爹还是娘在对面的树枝上跳跃。就在我低下眼再抬起的一瞬,窗台上空了!我一怔,放眼前方,看见小地主处于抛物线末端的身影落进茂密的叶丛之中。我有点儿难过,它竟然不辞而别。小地主大约在落脚点寄宿了几天,因为几只灰喜鹊常常飞到这棵树上,我估计是给它喂食的。小地主一直没露面,它把自己很好地隐藏起来,我想经过这次教训,它开始学习谨慎的生存策略了。
此后,小地主并没有像我希望的和别人文章中描写的那样,有天突然折返,一眼认出我是它的大恩人。校园里成群的灰喜鹊一如既往地自由起落,我觉得自己和它们之间有种秘密的联系。室友们说:“这里面说不定就有小地主,你该盼着故人重逢吧?”我鼻子里喷着冷气:“那个小没良心的,哼!”说实话,我有虚荣心,也希望小地主是只虚荣心强盛的鸟。就像去过异国他乡的人就有了让听众羡慕的吹嘘资本,鸟群中,有谁的童年曾经像哺乳动物的婴儿似的喝过奶,有谁曾在人类社会中生活过?这样我的小地主就可以在鸟类里散布点舆论影响,讲讲它的年少经历,讲讲它遇到的人,虽说有时不太温柔,可是心眼还不坏。
(选自周晓枫《斑纹——兽皮上地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