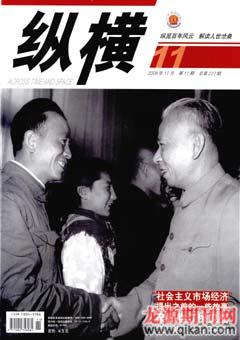全国科学大会纪事
吴明瑜 林自新
对于中国来说,1978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大事,都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三十年中国的历史进程。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次会议被称为“科学的春天”,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吴明瑜和林自新当时都在中科院工作,是政策研究室的正、副主任,他们参与起草了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稿,见证了大会从筹备到开幕的全过程。对于吴明瑜和林自新来说,那一年春天,给他们留下的记忆最为深刻。

一
1977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一份通知,宣布将在第二年的3月18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很快,吴明瑜和林自新就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吴明瑜(以下简称吴):当时我们是起草两个稿子,会议上一共四篇讲话,都是重要讲话:邓小平一个讲话,华国锋一个讲话,方毅同志一个报告,最后郭沫若同志一个讲话。最关键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我和林自新两个人负责起草他们两人的报告。
林自新(以下简称林):我们写出提纲,然后送上面审查,听听有什么指示。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此时,邓小平已经再次复出。他身兼数职,不但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还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林:小平同志复出了以后,他是眼光很敏锐的,要抓科技和教育。
吴:整个改革开放是从科学院揭开序幕的,邓小平也是把科学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首先从这里开始。
这个时候,距离“四人帮”倒台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然而积重难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召开这样的一个大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吴:我们当时考虑这个问题:马上开会,匆匆忙忙地开,不如充分准备好了开,这个准备好包括动员组织工作。动员做的规模很大,上海等省市都开十几万人的大会动员。所以科学大会还没开之前,人民就已经翘首以待了,就希望科学大会给我们来一个惊喜的成果。
其实,就在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发布之前,也就是1977年8月,邓小平就在北京的科学教育工作会议上,做了一次系统的发言,史称“八八讲话”。
吴:8月8日的讲话没有公开,但是影响很大,影响大在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高考制度这件事情今天看起来,好像大家争论高考应该怎么恢复,但是当时的影响是大,可以说牵扯到亿万个家庭,因为那时大家都不知道子女将来上什么学校,读书有没有用。
高考在1966年被取消,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不过招生的方式却和“文革”之前大相径庭。
吴:“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政治审查”16个字。结果呢,变成走后门,有些人利用权利欺负青年人的一个手段。但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使当年考生几十万人和几百万知识青年都有了希望,大家对中国的前途开始也有了信心。
在这次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当年就恢复高考制度。不过,这只是科学大会准备工作的第一步。
吴:要恢复研究生的招考制度,恢复所长的责任制,把专家们重新请出来,要平反很多冤假错案。当时几十个科学家被“文化大革命”逼死,一个个开追悼会都是在这时候搞起来的。另外要评奖,在科学大会上要评优秀论文、优秀成果奖励,要评优秀的科技人员。
此外,参加科学大会的代表,要经过各个地方省市推荐,层层选拔。而这个时候,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刚刚展开。
吴:比如说我们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原来在生物物理所搞X光远射,被下放到广东一个造船厂做油漆工人去了。这个时候就把他找回来,后来这个人就当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副主任,很有成就的科学家。所以很多人还在牛棚里刚出来,还不知天下如何呢,就先把人家先热热身。所以当时搞的很隆重,准备很充分。
科学大会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与此同时,吴明瑜和林自新也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为邓小平和华国锋准备讲话稿。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这看似普通的讲稿,却遇到了难以想象的波折。

二
从1977年9月一接到通知,中科院就成立了文件小组,负责起草中央领导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其中,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稿是重中之重。在吴明瑜和林自新的记忆中,他们最先起草的是邓小平的讲话稿。尽管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和邓小平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们起草这篇讲稿并没有费太多的周折。因为吴明瑜和林自新在科学院工作多年,这份讲稿,不但融入了邓小平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心声。从1977年9月开始,吴明瑜和林自新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邓小平的讲稿终于完成了。
林:不包括空格,9402字。稿子大约是集中在一个晚上写出来的,我们两个到办公室去加夜班,办公室就在现在的发改委,过去属于计委大楼——过去科委是在计委大楼办公。明瑜同志文笔流畅,记忆力好,字也写得好,所有的稿件,近一万字的稿件没有我写的一个字,都是他写的。并且他很细,哪怕写了八行十行,要改一个字他就把这一页重新写,所以最后的稿面是很干净的。
吴:邓小平、华国锋两个讲话是我和林自新起草的,小平同志讲话起草完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看,很快通过了,后来小平同志跟胡乔木他们讲:“很多是我讲过的内容,文字也很流畅。”他赞成这个稿子,做了一点小小改动就通过了。
由于邓小平是主管科学教育的领导,因此他的讲稿侧重于讲科学工作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林:一个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个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当时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很不容易的。
知识分子的问题由来已久,因此在撰写这部分讲稿的时候,吴明瑜和林自新不但字斟句酌,而且还翻阅不少经典著作。
吴:童大林同志说:你们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的剩余价值论,里面马克思有好几段专门论述知识分子地位,马克思作为阶级分析是这样分析的:是看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你是创造剩余价值还是剥削剩余价值,这和毛主席的从世界观分析不一样。旧社会的确有一些知识分子他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他的地位就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但是广大的知识分子不能这样分析。到了新社会,知识分子更加不是。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一部分,工人阶级一部分。所以小平同志非常欣赏这一段话,我们写在这个报告里头了。
对于知识分子到底是不是工人阶级,一直难有定论。在吴明瑜和林自新的记忆中,1962年召开的广州会议让他们印象深刻。
吴:当时周总理、陈老总讲过两个重要讲话,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这个冕。那时候没有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很谨慎,那个讲话稿是我帮他整理出来的。周恩来讲: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说我是江浙人,因为他祖籍绍兴,长大在淮安,所以是江浙人,不要忘本,虽然我们知识界,今天虽然大家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不要忘记我们过去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还要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讲得非常诚恳、亲切。陈毅同志当然更加快人快语了: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冕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称号。但还没有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林:当时影响很大,但是后来这个说法毛主席没有点头,所以还是不行,还是扣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吴:讲到知识界的关系上,周恩来他们的确是关心知识分子的人,但是不行。“文化大革命”所有保护知识分子的人都被打倒了,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吴明瑜和林自新起草的讲话稿,尽管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许和肯定,但是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声音。
吴:这个讲话到政治局讨论的时候,当时主持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为什么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技工作、关于知识分子的话你不引用?比如说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为什么不用这个话呢?这就叫我们很为难了。方毅同志回来传达了,他就请示小平同志说,你的意见怎么样?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不要改!那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了,就按照小平的意见——不改。
三
尽管在讲稿的起草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波折,但是全国科学大会依然在1978年的3月18日如期召开。
吴:会议的组织工作也做得很好,搞得很生动活泼:有大批少先队员献花,进入会场音乐演奏。这对科学界的人来说从来没有过:一直都受打击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也是受压,现在变成人们所尊敬的人了。全国著名的科学家都来了,现在翻翻什么院士,年纪大一点的,大概60岁以上,大都参加过当年那个会。5500人,加上列席的一共7300多人,再加上工作人员,整个人民大会堂一万人都坐满了。真是历史上空前的一个盛会,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会。
在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的讲话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林: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吴:小平同志觉得这个“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非常好,所以在科学大会上又重申这个话,到了1988年小平同志跟外国人谈话,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说过,这是对的,现在看来恐怕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讲这句话后面还有句话,“如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知识分子就不是臭老九,而是第一”。
在邓小平的讲话中,第二个重点就是专门论述知识分子的问题,也让在座的科学家们激动不已。
吴:当时参加会议的很多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比如天文台的张老,当时都70岁了,听了讲话热泪盈眶。科学大会影响很大,很多老科学家多少年互不往来,大家兴奋得不行,仿佛重见天日。上海审计所的所长冯德培说:有了邓小平的讲话,过去那些悖谬,以后成立不了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戴不上去了,小平同志都把问题解决了。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公开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确需要勇气和魄力。
吴:今天提起来“工人阶级一部分”,有人觉得这句话有多大意思呢,管他是哪个部分?其实当时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你不是工人阶级一分子,就是异己分子,四人帮讲:异己分子就要骂,就是臭老九,是全面专政的对象。今天,不仅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且是否定了几十年来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错误。这下子解决了,不仅是自己人,而且说精英分子是我们的精华。邓小平讲了,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吴明瑜还记得,3月18日,科学大会开幕的当天,除了邓小平,当时主管科技的副总理方毅也做了一个报告。

吴:大家已经寄希望于邓小平了。我们想,就用郭沫若最后一个讲话——闭幕词的讲话再鼓动一次吧。本来郭沫若讲话是请徐迟起草的,因为徐迟写了《哥德巴哈猜想》,他和科技界有接触,想请他写,他写了几百字,诗意很强,最后临时改变请胡平来起草。
胡平也是科学大会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吴明瑜说,由于大会临时决定,郭沫若在闭幕式上发表一篇讲话,再加上临阵换将,因此写稿的时间非常紧迫。
吴:胡平同志写的稿子就是最后一两天的时间,郭沫若的讲话前两篇均是急就篇,写得如政治家的口吻。胡平写的稿子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当时在病床上,加了一两个字,其余的他都同意,这个稿子基本上没有动,很快就用了。会上是由广播员宣读的,广播员的口才非常好,读得非常激动人心,抑扬顿挫,所以全场气氛非常热烈,谁都记得科学的春天、人民的春天、中国的春天,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
这篇讲话稿的题目是《科学的春天》,在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上宣读之后,很快就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这篇讲演稿被作为经典散文收入了中学教材,“科学的春天”也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语。科学大会之后,很快就在全国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回顾30年前的那次科学盛会,吴明瑜和林自新都说,邓小平之所以选择科学领域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和1975年发生的一段历史密不可分的。邓小平也曾经说过,中国在1974年到1975年就有一段改革的试验期。
(文稿来源: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编导刘革非)
责任编辑: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