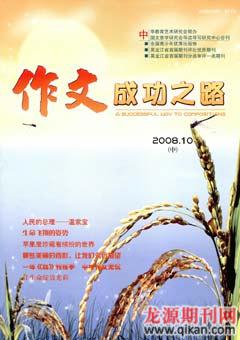做个不听话的好孩子
刘亚男
“听话!”
“乖,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你到底听不听话!”
……
从小到大,“听话”——作为长辈们最常用的训导词,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长久的熏陶和灌输,难免给人留下一种“听话就好,不听话就坏,就是大逆不道”的印象。年幼的我们,早早地就在人生的第一计算题上用等号把“好孩子”与“听话”拴在了一起。
似乎只要安分地“听话”,自然就会成为一个让大人们省心的“好孩子”。我们长大后却发现,在已经渐渐衰老的大人面前,我们无法再躲在“听话”的光环下,心安理得地做“好孩子”。
随着岁月的逝去,我这个成长起来的“好孩子”,开始质疑起这个训诫我多年的“等式”。
因为“听话”,我与第一失之交臂。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唱歌,经常被妈妈领着在公司里的各类文艺演出中做表演(所谓“表演”,只不过就是妈妈在节目编排的过程中为我争取到的唯一一个儿童级别的节目罢了)。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展示,我站在台上,站在许多双眼睛面前,不再羞涩与紧张。现在面对种种比赛,我依然会显得那么从容自如。而当时年幼的我,对于那次幼儿园举办的唱歌比赛,真的很在乎很在乎。直到现在还依稀记得,我是那么用心地去练习,大大咧咧的我第一次那样专心。结果出来了——第一名是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孩子。远远地,听到了指导老师与妈妈的谈话:
“我努力争取想破例,但园长说第一只能有一个。”
“那能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毕竟孩子她……”
“她是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
“嗯,我理解,那……就给她吧。”
“谢谢你。”
恍然间,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跑过去想说些什么,却被妈妈制止了:“听话,只不过是次比赛。”那天,听着园长宣布比赛结果,我没有喜悦,只有说不出的难过。那个不服输的我,那个争强好胜的我,第一次认识到第一与第二的差距……
因为“听话”,我放弃了最爱的电子琴。
每当手指触摸到键盘,总会产生一种最新鲜的感受。那黑与白的鲜明对比,仿佛昼夜交替般轻盈、和谐。喜欢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的感觉,就像喜欢白天替代黑夜一样。那天,我收拾好乐谱,去了妈妈的房间。
“妈妈,我们走吧!”
“不去了。”
“为什么?再不走就要迟到了。”
“我跟老师说了,以后不练了。上了初中,时间紧。”
“可是,我……”
“听话!回屋去吧,以后有机会再练。”
现在,每当看到被冷落在墙角里的电子琴,总忍不住想去触摸。才发现,弹奏出来的只是几个断断续续的音符,僵硬的手指,再也奏不出美妙的旋律……
因为“听话”,我一直学不会怎样去拒绝。
终于结束了一天的课程,初四的生活真是累啊!回到家,迷迷糊糊地做完了作业,看时间还早,悄悄地跑去书房,打开电脑,这几天的“与世隔绝”,一定发生了不少事情吧?刚想轻松一下,却听到隔壁房间里当教师的舅妈传来的“呼唤”──
“亚男,写完作业了吗?”
“嗯,写完了!”
“帮我看几份卷子好吗?”
“啊?卷子?可是我在……”
“听话!我看不完了,明天还要用。”
“哦,好吧……”
走出书房,努力掩饰内心的不悦,拿起红笔,在那些凌乱的卷子上开始了圈圈点点。心里依然很不高兴: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一下,却又要面对这些牛皮糖似的甩也甩不掉的试卷……
我不想再“听话”了!
因为“听话”,我迷失了自己,丢弃了自己的爱好;因为“听话”,我选择凡事都退一步,以至于成了别人眼中的胆小鬼;因为“听话”,我不会拒绝别人的要求,逼着自己去做不想做的事情……
现在,我不再生活在“听话”的阴影下,而是努力地昂头向前走。试着让自己去拼去争,试着让自己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见解,试着让自己学着去拒绝一些人、一些事……因为,我想做一个“不听话”的“好孩子”!
(指导教师袁承印)
(选自望岳文学社社刊《望岳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