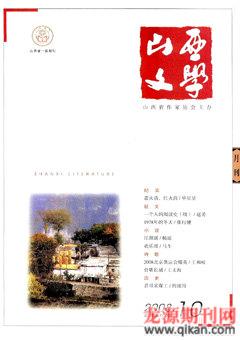1978年的冬天
1978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多风的冬天。
特别是处于吕梁山腹地大山峡里的蒲县,那种寒冷彻骨穿髓。记忆中山峡里的寒风如刀子一样切割着人们的脸,蒲县中学旁边的那条小河里冰块像山石一样的厚硬了,其实脚下的整个土地都冻得坚硬如石。
1978年的冬天又是一个温润祥和的冬天,特别是对从那个欲说还休的十年里刚刚走出来的十亿国人来说,这个冬天和这个冬天里的那次伟大的会议,像一道阳光照射在依然冰封的土地上,照射在渴盼早春的人们的心域里。
这年冬天我刚刚二十岁。
二十虚岁的我已在山区中小学里有了三年多的代理教员的生活。
先是在南山上的李家坡小学,后又在城关红旗小学,后来又在南山上的郑家园小学,之后又在城关的荆坡学校,接着又在蒲县第二中学,到了1978年的冬季,我又到了蒲县第一中学当了代理教员。
不到四年时间却频繁地换了六所学校,山上山下,城里村里,从深山里仅有十三个娃娃的单人校复式班,到县城最具规模的拥有几千名师生的第一中学,可以想象到那时的我像一只丧家之犬,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比公安机关到处抓捕的流窜人员也强不了多少。
那些年,教师队伍里明显地分几个阶层,公办教师、民办教师、长期代教、临时代教,也可叫做铁饭碗、木饭碗、泥饭碗、纸饭碗,长期代教是固定的代教,代替一个固定的位置。临时代教就不同了,像一块砖头,搬来搬去填一个空缺,哪一个女教师肚子大了,请了产假,就替她代一个或半个学期;哪一个老教员头晕眼花,请了病假,就替人家代个仨月五月。临时代教最怕放假,一放假,下学期的饭碗没个着落,便在放假前给校长或联合校长买一包点心,偷儿一样趁无人的夜色里给人家送去。校长或联合校长爽快地收下了,临时代教心下窃喜,不慌了,校长在假期里要给他考虑一个位位的;如校长或联合校长死活不肯收他的那包点心,推来推去,甚或有些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临时代教就得识眼色地退出来,怅怅地站在夜色里,感到自己的命运像这夜色一样,一派灰暗……
我在当临时代教的几年时间里,夜晚的月光下或没有月光的灰暗里,给头儿们送过十余次包装得四方四整的点心,那些年这是我唯一能送得起的奢侈品,得到过头儿们接收下的窃喜,也承受过头儿们不予接收和委婉拒绝的痛苦……那种痛苦一次次刺激了我的早熟,使我十八九岁二十岁的一张少年或者说一个小青年的脸上,过早就爬满了人生的沧桑。故而我的一张脸子就十分的老相了,以至于在我十九岁的那年,一个新的同事曾小心翼翼地问我,跟前有几个孩子了,是三个还是两个?我尴尬而惶恐,要知道我是他问话之后的整整十年后也就是我二十九岁那年才结的婚,三十岁才有我的儿子的。
话似乎有些拉扯远了,我的意思是想说,一个临时代教的纸饭碗,要端在手里也难上加难,还有比我更困难更恓惶的人在盯着这个纸饭碗,在同我竞争着……
恢复高考是1977年的冬季,那年十九岁的我在荆坡学校代初中语文课,我想请假两个月复习一下功课,校长没有同意,我只能在代课之余挤时间温习了。那时候我一派混沌,老虎吃天没法子下手,既没有复习提纲又没有参考资料,这时候在蒲县中学当高中语文教师的父亲不赞成我参加大专考试,说像我这种情况,参加个中专考试考个中专学校两三年分配个正式工作就满不错了,抄花头(叫花子)还嫌汤儿稀哩,就考中专吧!父亲对我的低估和他的选择使我走错了人生的一步,考中专是要考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而我偏偏理科特差,我的长处是文科,是强于同龄人许多的写作,是惊人的记忆力,是在几年的代教生涯里杂七杂八阅读过的周围同龄人从未读过的那些文学作品……如果我在那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把在陌生和费解的数学、物理、化学上花费的巨大功夫用在记忆历史、地理和政治习题上,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父亲却没有认真地分析这一切,而是人云亦云地甚至很轻率地让我报考中专,我只有顺从地看那些枯燥无比的数字、方程式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整整两个多月,我一直勉为其难地学习那些我压根就不感兴趣也无法开窍的功课,直到考试结束,我的视力一下子下降了许多,身体也瘦得剩下皮和骨头。
我居然被预选上了,红纸黑字的预选名单就大大地张贴在县城十字街头的南墙上面。
不过,我的名字是靠后的,现在想来,名字的先后顺序可能是根据成绩的先后排列的吧:
能被预选上也是侥幸的,这种侥幸在于我的数理化成绩太差,而考好的仅仅是语文和政治两科。
体检,填报志愿,做完这一系列工作后便是忐忑不安的等待。
第二年三月,即1978年三月,当最后一批录取通知书像早春里雪白的鸽子一样落到其他同学名下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落选了。
平心而论,考上中等专业学校的这些同学仅是各门功课匀称而已,才学平庸,志向也平庸,只是为了上两三年学校将来有一个工作而已。我在体检和填报志愿时同他们不少人接触过,发现他们几乎没有自己人生的理想和抱负,除了要考试的那几门功课,他们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更不要说什么中国名著和世界名著了,这是一批没什么文化的中专生,不要说现在,就是等他们学业结束毕业出来,也多半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我知道社会需要这大量的平凡的工作者,对这种“平凡”的指责是有失公允的,他们脚踏实地,认真生活,平平静静老老实实度过每一个日子,在平凡得接近于平庸中创造了生活,无须超前的思想,无须辽阔的视野,无须批判的锋芒,更无须也不会有深沉的忧患,他们满足和不满足地生活着,过着平稳而平淡的日子……
但我自以为不是这样的,我即使考上当时的任何一所中专学校,我也不会使自己追求的脚步停下来。我当时想,我必须接受国家的高等教育,具体一点说,我一定要坐在大学中文系的教室里,系统地学习我骨子里深爱的中文专业,更广博地阅读一些文学经典,然后认真地哪怕痛苦地思考一些问题,社会的、哲学的、思想的、历史的,弄清许多我当时模糊不清的困惑,在学习之余拿起笔来,倾吐心中淤积的愤懑,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叙写不算漫长但却有波折的青春阅历,还有二十年岁月里所经受过的一些所谓磨难、委屈、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
作为一个不错的中学生,却偏偏不让上高中,那是贫下中农推荐的时代,原因就是我家有一个黑色的成分,我爷爷、大爷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四类分子。
在生产队里劳动时,为了每天挣到9个工分,和强壮劳力一样,在山上炸石头,在河里挖淤泥,在平田整地的劳动场地跑飞车,曾累得脱肛。
十六岁细细高高的我学会了犁地耙地锄地割麦,农活之外还作为一个小工跟着清一色的四类分子大工们给学校盖高中部的教室,那是拒绝我的学校,拒绝我的教室。原来的同学坐在宽敞亮堂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而我却在不远处的工地上顶着大太阳搬砖和泥扛木料,那时候,我的
心理就严重失衡了。
几经周折在吕梁山深处当了一个临时代教,却命运多舛,代教的第一年里领上五年级学生搬石头烧石灰,学工劳动中班里一个女学生就意外地被青石砸死了,作为班主任的我自然难脱干系,受到了牵连。
这段不算漫长但还比较丰富的阅历,使我不像其他同龄人那样生活平静经历单一,我的高远志向和生活积累使我有创作的冲动和自信,如果在大学那样一种文化环境里,我相信我能有所作为!
这就是我当时幼稚却真实的想法。
上大学中文系是我那个时期里最美好的愿望和魂牵梦萦的心结。
可是心强命不强的我,居然连个……
我伤心,自闭、自卑,内心里却不甘服输,因为,全县大学文科预选上的几位我都清楚,我的文科水平绝对在他们之上!只是各种原因让我失去了1977年高考的那么一个绝好的机会。这是作为蒲县语文权威的我父亲的严重失误,他对我的低估和漫不经心让我永远耿耿于怀!
1978年春末夏初,我病倒了,且大病一场,人瘦得皮包骨头,面色苍黄,一直不停地吐酸水,医院说我白血球增多,县城里传说我得了白血症,一时间纷纷扬扬的。认识的人见了面轻言轻语安慰几句,意思是让我想开些,有病了就按有病的来,想吃些什么好东西就想办法吃点吧……语调里充满了同情和关切。我正在教着的荆坡中学班里的学生们也一拨一拨地来看我,男学生直爽,愣愣地问我,张老师,人都说你得了不好的病,是真的吗?女学生含蓄,一个个眼睛红红的,看过我后躲在一边去悄悄擦泪。我得摆出一个老师的姿态来,劝他们回去,不必担心我,我病一好就会回学校教他们的。
我现在记不起那时候吃了些什么药,记忆中只买了两小瓶黄黄的如豆的药粒,没打针没输液更没住医院,家里实在太困难,我硬挺着,我整天一人钻在屋子里,到了傍黑人少时才走出屋子到了中学后面的山坡上,吐一会酸水,散一会步,在山石上久久地坐着。
那时候我力所能及地看一些书,准备着下一年的高考,担心着下一步的代教工作,同时心里也埋怨着父亲,为什么就没有让我参加上一年的文科高考,误了那么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虽然在病中,我还是在温课之余写了三大本作文,我父亲当时代着蒲县一中高中班,一来二往,我的作文就传到高中年级了。先是文科复习班,后是理科复习班,复习班的语文老师让班里平时能考前五名的学生传阅我的三本作文,有的复习生甚至在大清早的河滩里一段一段背诵我的作文。
是的,他们没有不传阅、没有不背诵的道理,我的作文让他们,甚至让所有的高中语文老师们耳目一新,想象、构思,还有早已摆脱了学生腔的颇有几分老练的语言,使所有读过的人惊奇惊讶!
要知道刚刚恢复高考的1977年,语文试题光作文就占七十分!那可是命题作文。
难熬的病痛过后,已是几个月之后了,我在蒲县二中代教了几个月,正好蒲县一中初中部缺语文教师,我又到了蒲县一中代教。
一边代一个初中班的语文课,一边在文科高考复习班听听历史、地理、政治几门课,尽管生活安排得非常紧张,我还是挤出时间看杂志上的小说散文作品,还订了《人民文学》等杂志。早在前一年的秋季里,我在荆坡中学看了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给班里学生读了一遍,又推荐给了其他老师,还展开了文学讨论,引起了一些反响;之后我又推荐给了蒲县中学的语文老师们,推荐给了文化馆的文学辅导员以及蒲县当时的文学爱好者,立刻引起了全县范围内的文学热浪。尽管当时还是个小青年,但经历使我早熟并学会了思考,初读《班主任》,我激动难耐,刘心武用小说声音第一次大胆地否定了“文革”,勇气可嘉!我从《班主任》看到了一个文学新时期即将到来!心里又惊又喜,惊喜什么?又说不明白,同时学习更加用功和勤奋了,总觉得往后没有真本事果真是不行了,同时在混沌和朦胧中,隐约看到了一条可尝试的创作之路。
天气很冷,风也很大,自然的风总是把早春的气息一点点吹来;还有一股风把时局和政治的春意一股一股地吹向民间,从报纸上,从广播里,从人们私下的言谈和猜测里,从一段时间的来自官方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从文学作品中作家对社会政治的敏感和尖锐里,人们嗅到了早春温暖祥和的气息,祈盼着怡人的早春快些到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个时候召开了,记得那是十二月十八日以后的那几天,整个蒲县中学的老师们集中精力地听着广播,看着报纸,打探着会议的精神。
那一段时间的我,也处在一种新的紧张和学习中。县教育局按照上面的精神,要在全县近千名民办教员和代理教员中招考十三名公办教师,条件是,凡有二年教龄以上的现任民办代教,其中包括在蒲县中学文理科复习班复习的以前有二年以上教龄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这对我无疑又是一个机会,只要能考上,要比上三年中师还要经济合算,试想,如果1977年我被中师录取的话,到1981年才可以毕业的,那现在只要考进前十三名,就是正式教师,就成了国家正式干部了。
诸多的理想目标都在后面,先顾眼前吧,先端个铁饭碗再说,端上铁饭碗就没后顾之忧了。
有关考试转正的细则一一出来了,我能记住的,是与我息息相关的条例:参考人员,如果仅考语文、政治、数学三科者,考上担任小学教师,如果加试历史、地理(文科)或物理、化学(理科)者,考上之后在中学任教。那时候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人才不够时便拔高使用,教育局出这一招,也是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同时也鼓励考试者有一种向上的决心。
我当然要加试史、地两科的,我现在就是中学代教嘛,何况我跟着文科复习班已经复习了一段时间了。文理两科的高考复习班共有四个人符合招考条件,大家都报了名,都加试两科,都跃跃欲试,都把这次考试作为高考前的一次预演。尽管大家知道,一旦考上教师,就得马上教学,绝对不可以参加下年的高考了!这也是教育局铁的规定。
教师招考的需要,凡参考者都要有一寸照片,在蒲县唯一一家照相馆里,我留下了1978年12月的一张免冠照,一张精瘦清癯的脸,有些突兀的颧骨,双眼里有些困惑更有许多的希望。这是一个年轻人对自己前途的写照,它恰恰迎合了当时的许多国人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命运的些许担忧并充满期待和渴望一样。在之后的多年里,我从自己的那张小照里,居然读出了许多的蕴含内容。
在我夜以继日的温课复习中,三中全会此时也开得如火如荼,我忙中偷闲问一句父亲,会议的内容和精神是什么?父亲显然有些兴奋,但他知道我正在复习,便深入浅出地说,国家以后停止搞阶级斗争了,国家以后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还有,要纠正以前的错误,实事求是,平反昭雪,解放思想朝前看,工作中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我点点头。几年前,阶级斗争斗死了我亲爱的爷爷;阶级斗争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力,阶级
斗争像一团沉重的乌云,一直笼罩着我的家庭,笼罩在我少年的心头。多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次一出校门,见村巷里围了一群人看热闹,我们小娃娃跑前去一看,原来是民兵们押着几个四类分子在游街,四类分子们一个个头戴着纸帽子,满脸被抹上锅黑,一人手里敲一面破铜锣,口里念念叨叨:我该死!我是四类分子……在四类分子行列里,有我的爷爷,我的大爷爷。此后,我害怕人群,害怕聚会,害怕锣鼓声。
因为我是四类分子的孙子,在村里劳动的那年里,派我和“可教子女”上山炸石山,那可是最危险最艰苦的活计;派我在河里拉河泥;派我和一群四类分子挖房基、打夯、盖房子。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广播喇叭里一听到那句张扬暴力的话就让我不寒而栗。
如今好了,自上而下再不倡导人为的阶级斗争了。何况,国家要大力抓建设,抓建设能离开人才么?
我运了运气,争取把眼前这次招考机会紧紧抓住,并且考出个不错的成绩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亲,对得起身边的同事和一块学习的文科班同学!
再说,代教每月仅有24块钱工资,还得在附近的村里买粮食,日子窘迫得很。只要这次一考上,马上就吃国供粮,工资也挣到34.5块了。方方面面考虑,我必须在这次招考中发挥好!
在全县上千名民办代教中,那次报名参加转正考试的有468名,这数字我至今不会忘记。怎么会忘呢?那是考前468人集中在一起听教育局的干部训话时,大家都记住的一个数字啊!环顾一下,礼堂里黑压压一片,468对眼睛里,眨动着的是自卑的、惶恐的但还不乏希望的光线!
紧紧张张的两天考试时间过去了,蒲县中学除了星期天还破例放了一天假,因为所有教室都被参考者占据了,一个教室里只有25人,株距行距拉得很远,完全是一派高考的架势。
考试结束的时候,已是12月23日,正是三中全会结束后的日子,远远地就听见大街上传来欢庆的锣鼓,在蒲县中学通往城中心的北关街两边,红红绿绿贴上了庆祝三中全会的标语和口号,我至今仍记得几条口号内容: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工作重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红红的标语像一团团红红的火,燃烧着我的一颗心。我火热的然而忐忑不安的心在期待着12月25日晚饭后,文科班王建平同学找到我,有些神秘地对我说,这次你考得很好,明天一大早就要公布成绩了,十三名考中者的名单被写在大红纸上,张贴在县城最热闹的十字大街南端墙壁的木板上,那里,招人眼目,常常张贴电影广告的。
是吗,我考中了,进了前十三名啦?
我的心,一下被兴奋的情绪揪起来了。
那当然,我刚刚知道的内部消息,不敢给任何人说的。王建平压低声音更神秘地说道。我知道,王建平说的是有根据的,他爸是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参与这次招考,还是主要责任人,建平从他爸那里了解到最新消息,估计不会有错。再看建平一副庄重神秘的样子,不像开玩笑。那个年代,谁开这样的玩笑呢?喜悦像大冬天里一口气喝下二两烧酒,我的周身被兴奋溢满了。
因为王建平告了我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就诚恳邀请建平去看电影,建平很爱看电影。你想,文科班的同学有谁不爱看电影看小说呢?建平尤其喜欢。我俩欢快地朝电影院里走去。那晚的电影是王丹凤主演的《女理发师》,冈0刚开禁重演的老片子,故事我一点都看不进去,我依然被兴奋燃烧着,同时也被一个悬念困扰着,我到底考了第几名?十三名之内第一名和第十三名还是不一样啊,要张榜公布,不知要被收进多少人的眼睛里去的。我敛了声悄悄问:建平,能告诉我,考的是第几名吗?
王建平笑一笑说,这可不行,告诉你考上了,进了前十三名,这还是我自作主张的,教育局有纪律,不到发榜是不能公开的。
我不好再问什么,默默地陪了他看电影。
电影院的最后一排有一处灯火,是摆摊卖葵花子的,用纸页卷起的圆锥型,一毛钱一桶,我借了解手的机会返回来买了两桶,俩人边嗑瓜子边看电影,我无心去嗑,等到建平拿到第五粒瓜子时,我忍不住又问:
建平,告我算了,不就是一夜的时间嘛!你知道我这人的性子,不知道底细就着急得不行,你看,电影也看不进去,瓜子也吃不出香来,告我第几名算了,就提前对我一人公开一下吧!我也笑着,但有些央求了。
王建平依然不急不躁地笑一笑,顿了一下,他下了决心的样子,终于开口道:
我只能告诉你,你考的成绩不错,靠前排着呢,其他的就不能说了。你急什么?明天吃过早饭,不就啥都清楚了?
我连连点头,不好意思再问了,直到电影散场。
出了影院不大远,有一家卖羊汤的,我硬拉着建平过去,一人喝了一碗羊汤,建平要付钱,被我硬摁住了。我说,我马上就成了国家干部,马上就挣固定工资,马上就吃了国供粮,而你目前还是个学生,哪有学生请干部的道理?见我说得有理,建平再不去急了,埋头喝羊汤。
羊汤下肚浑身热腾腾的,记得一人还加了汤泡了一个饼子,吃得美滋滋。见建平热热的,平时蜡黄的瘦长脸上出现了两团少见的红晕,我又不失时机地发问道:
建平,告诉我算了,到底我考了第几名哪?
王建平还是笑着说,原来你这碗羊汤和电影院里的瓜子都是在贿赂我哩,都是在一点点套我的话哩,你可真有心计,不知道你着急甚?步步为营,逼得我没出路了。好,我犯一回错误,我索性冒一回天下之大不韪,你听好了,这回你考到前五名了,行了吧,你这人,明早不就啥都知道了嘛!
我想,前五名是啥意思,是第五名,还是还在前面?我心里责怪建平的小气,索性告我不就结了嘛,真是的!心里责怪着,还是很高兴的,毕竟我的努力是有收获的,我起码知道我在前五名里面,这还不让人亢奋,这还不够光荣?要知道,参加考试的468人哪,我的天!
走到十字街头的时候,我特意将南墙木板张贴电影广告的地方深看了一眼。我想,再过十几个小时,这里将张贴着一张红榜,红榜上会大大地写着我的名字,明天,来来往往的人们,只要留意,便会看见“张行健”三个字的。
几乎一夜无眠。
我把这消息告给了父亲,他也几乎一夜失眠。
是啊,我等于上了一个中师,而中师的三年,也得花一些钱吧!
第二天早饭没吃完,就有十几个文科复习班和父亲代的高三年级文班的学生前来报信,他们都是平时和我熟悉的,一个个喜滋滋地说,十字大街上张贴了大红榜,十三个人的名字大大地写在一张大红纸上,张行健三个字显赫地写在第一行,行健居然拿了第一名,属于状元呢。
我大喜过望,真没料到会考第一名。
同学们说,名单后面附着各科成绩,除了数学一门是28分,其他四门都在95分以上。
因了语文等四门功课的优秀,这一平均,分数就上去了,就排在了第一名。
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次考出了我的水平,从此后再不为工作、生活而担忧了。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四年代教生活没有白白度过,用四年岁月作为铺垫换取一个正式工作,且是中学教师的职位,也能说得过去。要知道,还有近千名民办代教们依然生活在艰辛中,而他们的教龄大多都十几年了,他们依然得在山村学校里,在单人复式校里,或者在城里的中小学里,艰难地、卑微地工作着、祈盼着。
我感到欣慰的是,从此可以安下心来,看一些复习资料之外的书籍了,在教学之余,可以尝试着写些东西了,小说散文之类。我才二十岁,严格地说还是一个大学生的年纪,思想轻松了,干什么都可以用心而上劲,我认为自己还拥有一个有意义的未来。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工作和生活的转折正好迎合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大命运的转折,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我是幸运的,作为小青年的我,当刚刚迈入生活走向社会,刚刚尝到了一些生活的辛酸,受到了一点点生活委屈的时候,就可喜地遇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大复兴。和多灾多难的民族比起来,个人的那点磨难微不足道。把个人的命运融入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之中,这种意义就非同一般,就有了更为开阔和壮美的背景。在这壮阔的背景之下,我的前途和命运一定还会发生更加喜人的变化。
我期待着,也渴望着。故而我牢牢记着1978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