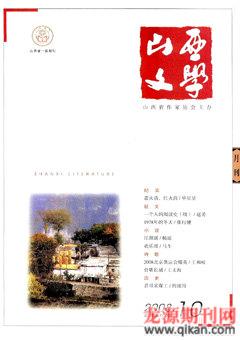往事六记
赵少琳
捡燎炭
天还未亮,我和哥哥便悄悄地钻出被窝,准备起床。刚掀开被子,冷气袭来,让人真不愿意离开这个暖暖的地方。正值数九寒天,很少有这个时候往门外跑的。可是我和哥哥都惦记着锅炉房里倒出的炉渣。
锅炉房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每天早晨五六点钟是往出倒炉渣的时间,大概七点钟左右是夜班向白班交接班的时间。交接班之前,夜班的师傅要把工作现场和烧出的炉渣清理干净,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从锅炉房里推出一两车的炉渣来。
倒出的炉渣是浇过水的,还冒着热气,有时没有浇透的炉渣还很烫手,我和哥哥便要从这发湿和发烫的炉渣里面捡出没有烧透的燎炭来。
每次我们都带着筛子和耙子,还带着一只箩筐。来得早了的时候,我们就在锅炉房的太门外等着,并从大门的细缝中向锅炉房里望着,盼着锅炉房的师傅早些将炉渣倒出来。天气寒冷,我和哥哥穿得都很松垮,站在大门内侧的角落里,彼此也没有什么话语,只是一遍又一遍听着锅炉房里的动静,看着锅炉房里的师傅在锅炉房里外睡眼惺忪地走来走去,有时还碰出了工具的声响,就恨不得能从门缝里钻进去,把清理炉渣的活儿替他干了。
炉渣或早或晚倒出来了,我和哥哥在清冷的月光下又筛又捡,凡是留在筛子上的块儿,我们都急急地倒在一边,因为天黑,我们也分不清哪些是燎炭,哪些是炉渣。
前面说了,倒出的炉渣冒着热气,有些炉渣还很烫手。我们的手上热一下,冷一下,手背上常常裂着口子,乌黑乌黑的两只小手更是难看。就这样,赶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便将锅炉房里倒出的炉渣筛捡得差不多了。哥哥有力,常常抱着箩筐在前,走走歇歇,我则拿着筛子和耙子在后跟着往家走。
回到家中,母亲已经把早饭给我们做好了,嘱我们把黑脸和脏手洗净,然后再把我们捡回来的燎炭加进火中,让我们暖手。
盖房子
过去人们的住房都很窄小,便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盖起了房子,我们家也不例外,盼望着也能早日把自家的房子盖好。
盖房子需要砖、房梁和椽子等建筑材料,特别是砖会用得更多。那时,我们的父母挣得工资仅够维持家庭的生活,根本没有钱去购买别的东西。
但房子还是要盖的,我就经常留意玩耍的地方丢弃的砖头,留意有砖头的地方,不管是半砖还是整砖,不管这些砖头离家有多远,我都会把这些砖头拾回家的。
有一天放学,经过一家工厂的宿舍区。这家工厂的宿舍区要盖楼房,旧有的宿舍区的平房便被拆得七零八落,我看到废墟里尽是杂乱的砖头,心中甭提有多高兴了。因为自从我开始留意捡拾砖头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砖头在一起堆积着。我回到家中,放下书包,借来邻居家用手拉的平时买粮买菜的小车,匆匆地向那被拆迁的宿舍区走去。
由于捡拾的砖头是一些旧砖,上面挂着一些凝固了的泥浆,因此砖头很笨重,如果不将这些凝固了的泥浆磕掉就不能整齐地把这些砖块放在那不大的车上。即使放上去也会东倒西歪,走不了几步就会从车上掉下来。这样就需要我把一块又一块的砖头敲打干净。我找来了瓦刀,凝固的泥浆在瓦刀下也并不示弱,常常,我的手上磨出了水泡,有时几块砖头粘连在一起,更是不容易敲打干净和分开,但是我知道只要耐心地弯下腰来多捡一块砖头,不怕吃苦,就会早日将房子盖起来,就会早日和邻居家的人们一样住进新房子里去。
砖一车车被我吃力地拉回了家里,虽然我每次只能拉二三十块,院子里的砖还是明显地一天天多了起来。默默中,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假日里,父亲请来了好几个工匠,用我捡回来的足够的砖头,把墙一层一层地砌好,然后上门、上窗,然后再上梁、上椽子……我看到自己捡回来的砖头一块又一块地站立起来,一直到屋顶,虽然这房子只有十来八平方,但是我想到我们的家从此又多了一处温暖的地方。
上学的时候,我的数学不好,每当期中和期末考试后,常常气馁和自卑。有一回我做数学作业,父亲站在我的身后和蔼地说,学习就和盖房子一样,要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地积累,要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地往起盖,不下功夫不行,就像眼前的这所房子,不是在你的努力下盖起来了?
从那之后,我领悟着父亲的这些话,知道父亲说的话是不会错的。
换豆腐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学过农,村子里的人们会做豆腐。
星期天,我们几个同学约好,要去五六十里以外的这个村子换豆腐。
换豆腐就是用家中省吃俭用下来的高粱面或者玉茭面,去换人家做出来的豆腐,一般情况下一斤面换一斤半至两斤豆腐。
那天,母亲给我准备了十来八斤玉茭面,把口子扎紧,还给我带了一个小黑铁桶。母亲把玉茭面放进小黑铁桶里面,把小黑铁桶牢牢地给我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位上,我便和班里的几个同学出发了。
去的时候坡路很多。在坡上我们不能一口气骑得太远,就从自行车上下来,推一阵,骑一阵。这时,大家的脸也憋得彤红彤红的。
我们小时候吃豆腐可不像现在,豆腐多得遍地都是。那时东西都是按号供应的,一个月公布一次票号,什么号买什么东西,买多少东西都是有限制的,就连豆腐一个月一个人最多也只能供应半斤一斤的。有了票号不等于就能够吃上豆腐,吃豆腐是要早早地在卖菜的地方排队等候的。菜店里,一早晨就来几屉子豆腐,卖完为止,因此豆腐总是供不应求。如果几次排队买不到豆腐,过了这个月,买豆腐的号也就作废了,只能等下个月出的新号了。
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骑上自行车,带上粮食去很远的地方换豆腐吃了。
路上,我们往学过农的那个村子里去,却并不知道这个村子确切的位置。因为我们是学生,并没有单独出过远门,所以我们在大方向不会错的情况下,边走边向一些上了岁数的人打听那个村子在什么地方,沿途被打听的人都能够详细地告诉我们那个村子还有多远,它的周围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大约是在午后两点多钟,我们终于到达了那个村子。
一进村子,我们就看见了一座简陋的房子里热气腾腾,走近一看正有两三个人在房子里点着豆腐。我们和那做豆腐的老乡说明了来历、说明了来意。那做豆腐的老乡也还记得我们这些个学生。
面和豆腐在善意中进行了交换,我们把豆腐小心地放在带来的家什里,匆匆地告别了老乡就原路返回。
午后了,大家也没有感到饥饿,可能是因为换上了豆腐的缘故吧,心里暖暖的。加之,回来的路上又一路下坡,大家显得都很轻松自在。
回到家中,父母问了我一些路上的情况,用扫帚把我身上浅浅的灰尘扫去,把换回的豆腐提回了家中,我自然也觉得像是长了一些本事。
晚饭的时候,父亲用猪板油给我们炒酸菜吃,酸菜里擦进了一些土豆。然后他又把我换回来的豆腐多拿了一块切好,放在土豆的上面,再撒上一层花椒面,用锅盖把锅盖严。炖了一会儿,热气和香味从锅沿漫出来,闻着就让人嘴馋。
那一晚的那顿饭我们吃得都很满足。
事情过去好多年了,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儿,女儿说:“真的呀!现在我们连肉都不想吃了。”
拾粮食
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年我们当地的高粱收成不错,把我家附近的一家面粉厂的好些个粮仓占了个满满当当,除此而外苫了席子的粮垛也把厂里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没有办法,厂里的粮食只能临时往单位外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存放,粮食一垛一垛地在麻袋里装着,走上前看,庞大的一片让人咋舌。
那个年代粮食是珍贵的,即便我们能够看到这粮食堆得遍地都是,却也并不能说我们就拥有了粮食,就能够顿顿吃饱。哪怕是眼前粗糙的高粱,能够尽着吃,也是令大家羡慕的事情。
我每天上学要路过这家面粉厂,上学放学时发现粮食在搬运的过程中总会撒落一些在地上。撒落的粮食工人们是不会去收的,也是没有办法去收的,因为那地本身是土路,不像现在便道上铺的都是五颜六色的砖块。粮食掉在便道的土路上稀稀落落的,就有人拿着笤帚和簸箕去扫。
放学后,我也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拿着笤帚和簸箕去扫粮食。粮食掉落在地上要想全扫起来,往往就要把更多的尘土扫进簸箕,这样才不会将粮食漏掉。
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扫好了粮食,我趔趔趄趄地把扫好的粮食提回家中,然后把它倒在一张低矮的小方桌上,再搬来凳子坐在跟前,便一粒一粒地往出捡。捡出的高粱用手刮进桌子底下的脸盆里,再把桌子上的泥土和石子推到一边。这样的活儿非要干到眼睛酸酸的,手指也有些肿胀,非要干到困得要到入睡的时候,才肯罢休。这件耐心的事儿我和家人大约干了有一个星期。
高粱捡好后并不是就此完事了,捡好的高粱是要淘洗的,一遍又一遍地,直到淘洗后的水变清了,高粱才算是淘洗干净了。淘洗干净后的高粱还要晾晒几天,不然潮湿的高粱用不了多久就会发霉。
那一年的秋天,我给家里捡回了二三十斤的粮食,我和父亲把那二三十斤粮食装进面袋,用自行车推着去换面粉。在路上,我看到父亲高兴的样子,觉得我们离好日子近了一些。
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偶尔有谁吃上一回高粱面那是当细粮吃的。但是我发现,现在的人们不像过去仔细了,吃不了的东西就往桌子上一扔。让他打包吧,他还嫌掉价。每到这时,我便真的想狠揍他一顿。
看电影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孩子,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有着一些特殊的经历。
譬如看电影吧,常常在一些新片到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早早地来到电影院前,等候着购票或者是等候着别人退票。那时的娱乐活动太少了,也许只有电影才是人们最好的消遣方式。
电影院的门前已经等候了很多人,黑压压的一片,来回地涌动着,似乎外边等票的人比电影院里面的人还要多。通常电影院的电影票提前两三天就售完了,到了放电影的那天就没有了,即使有,也是前两三天没人要的,座位号肯定是最偏最远的。最偏最远的票也是不好买的,那些偶尔买到票的人从人群中挤出来,迫切而警惕地看看手中刚买的电影票,一蹿一蹿地就进了电影院,兴奋地找他最偏最远的座位去了。
这是幸运的,但大部分人是没有这样的运气的,他们在炎热的夏天或是寒冷的冬季里,巴望着能够等来一两个退票的观众。正巧有退票的人,或是当人们发现了有退票人的时候,大家一拥而上,像撕扯一块肉一样,迅速将钱和票进行了交换。这时无票的人们才失望地松弛下来,探头探脑地看着那个买到票的人渐渐地散去。
那时我们这些买不到票的孩子,就羡慕起跑片子的人来。跑片子的人是大孩子,我们在电影院的门口看到他坐在摩托车的后边,一溜烟地冲到电影院入口处的台阶下,然后那大孩子迅速从摩托车两边的皮袋子里掏出两三本片子,抱在怀里,像脚底抹了油似的在电影院的楼上楼下跑着,那个严肃和旁若无人的劲儿,就觉得自己的个子真的比别人高出了一截。
电影就要开演了,眼看着这家电影院买不到了电影票,我就和院里的几个孩子飞也似的向等待接片的下一家电影院赶去。赶到这家电影院时更是人山人海,售票口还剩几张票没有售出,早有最年轻有力的人在那里铁一样地堵着,一层一层的,于是就有人受不了龇牙咧嘴地喊叫着。无望中,我们也实在是厌倦了这样的场面,一个个失败的样子,就像身上所有的零部件都松动了,悻悻地往回走去。
这样的结果我们是不甘心的,看不上电影,我们就去看电视,我们知道这一片唯一放电视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一家企业的院子里,那里放电视是不会要票的。电视不大,木制的外壳看上去很旧。我们去了的时候电视已演得差不多了。院子里看电视的人站得满满的,由前向后地扩大,没有人说话和走动。
电视常常要耍脾气,演着演着画面就失踪了,雪花点子一片,就像电视台下班了一样。这时就有人出来调台,转转天线,动动按钮,让人觉得他有满肚子的学问。一阵,电视里模模糊糊地有画面出现了,扭曲的脸又恢复到了正常的位置。我们就又盯紧了电视画面不放。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买冰棍
母亲给了我一角钱,我想要去买两只冰棍,一只给自己吃,另一只给年事已高但身体尚且硬朗的太姥姥吃。
正是午后,天气炎热得让人跺脚,买冰棍吃就成为了渴望。开始我在宿舍院子的门口寻找卖冰棍的,从街的一端望向街的另一端,发现没有,便到离家四五百米的地方去找,那里是一家电影院,平日里卖冰棍的就在固定的地方支着摊子。可那天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吧,人家的冰棍早已卖完回家歇晌去了。我有些沮丧,但又不甘心,就沿街试着往更远的地方去找。
带着暑热,汗水从我的脖颈上流下来。走了一段路后,我真的买到了两只冰棍。当我买好了冰棍向回走的时候,我把两只清凉的冰棍分开,一手拿着一只。我想好了,右手的这只是自己吃的,左手的这只是留给太姥姥的。我边往回走,边在嘴里抿着自己的那一只。
当我吃着自己的那只冰棍快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左手上的冰棍已经开始融化了,包冰棍的纸随着融化的冰棍脱落在了地上。我急了,三口两口把右手上的冰棍吃完,之后,便沿着墙根有阴凉的地方急走。可是有阴凉的地方的温度也低不到哪里,冰棍继续融化着。我委屈地含着泪水,用右手接着化下来的冰棍,向家的方向跑了起来。可是当我跑回家的时候,冰棍化得只剩下大拇指头那么大了。我高高地把冰棍举起来让太姥姥快吃,太姥姥怜惜地看着我,让我吃,我不吃,太姥姥便嗔怪而夸张地一口把冰棍吃进了嘴里,还用晋北方言溺爱地唠叨着。
我喜欢太姥姥。八十多岁的人了,一双在旧社会裹了的小脚在院子中进进出出,不需要人来侍候。眼睛不行了,还固执地戴上一副花镜,给我们拆拆洗洗、缝缝补补,并且起早贪黑地在锅台边转来转去,呵护和照料着我们兄妹三人的一日三餐。那时的饭食粗糙,我们吃什么太姥姥也吃什么,绝没有任何一点简单的要求。左邻右舍没有人不夸赞这位面慈心善的老人的。因此,我想给她吃上一口好吃点的东西,可是那天我给太姥姥买的冰棍几乎都化掉了,两手粘糊糊的,也不知太姥姥看见了没有。
这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一个孩子深爱着他的亲人,却没有能力去爱,直到今天,这个孩子都会常常有些隐痛地想起这件事来。
——以沈阳市和平区既有锅炉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