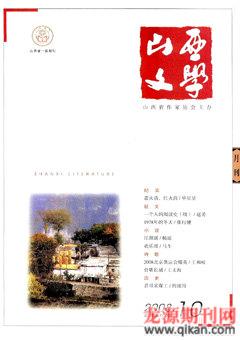什么样的可能性使得小说如此迷人(同期评论)
陈克海
先说两句题外话。有一回临近放假,杨遥问我这么长的时间不同家待在太原干吗,我说能干吗。他就提议,找个女子一起过冬吧。我说,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他却推脱开了,说是小地方的人没文化不好,而且又不能一起说说理想和文学。这让我着实惊讶了一下。事实上我是羞于谈文学的,何况是和女人。一则所知甚少,二则觉得没什么可谈的。然而自信的杨遥不一样。我记得有回他来太原玩,居然和一个朋友抵足而眠,谈论小说之类一直到凌晨两三点。
毫无疑问,对于小说的真诚和理想的执著,肯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杨遥对世界的看法,这话反过来说同样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小地方小人物没有兴趣。恰恰相反,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以此为参照,写尽平凡人物的酸辛。早年的《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二弟的碉堡》就是如此,《江湖谣》也不例外。
他冷眼旁观,看见心肠貌似冷酷的斜眼青年,农妇,脱衣舞女,乞讨者,恶棍,甚至是作为执法者的警察,凡是能被眼睛扫描到的地方,几乎都多多少少以一种冷峻的风格呈现在了他的笔下。这就是杨遥的短篇小说《江湖谣》里出现的一些人物类型。内容和主题并不能彰显他的全部,但这些关键词至少可以表明他的兴趣所在。无论是题目的暗示,还是气氛的渲染,江湖这个世界已经若隐若现。就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杨遥肯定会写一个混混的生活。或者叛逆,或者与众不同。读完开头的近千字,还想当然地认为确实就是如此。一个被老师惩罚的学生钟飞在午后的阳光下任由自己的鼻血流淌。作者颇具耐心,为了形容那种惊心动魄的程度,还描写了血液渗透进黄土里的效果。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钟飞即便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强盗,肯定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至少我的阅读期待就是这样。可紧接着读下去,发现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会出现什么大起大伏的情节,那种开头对江湖的向往情节好像突然淡化了。作者又花了近两千字的篇幅交待了钟飞父母的一切,两个字可以概括:悲惨。都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了,都到了悲惨世界了,这个貌似混混的钟飞应该破罐子破摔了吧,可是没有。他虽然长相丑陋,但心灵手巧,什么技术都是一学就会。他自力更生,改造房屋,然后把多下的房间出租给别人。这个时候作者写道:
“钟飞的第二个房客是河北人,第一个是外乡,第二个却是外省了。我们兴奋地想,钟飞的第三个房客似乎会是外国人。……钟飞说他上完初中就不上了,他也要去闯江湖,做老张那样的人。我们都很羡慕。有人说:‘再找个像老张老婆那样的女人,一起闯江湖,更过瘾。钟飞不说话,但大家更兴奋了,隐隐觉得老婆很重要。”
看看,铺排了这么多,终于要写到钟飞闯荡江湖了,而且还写到了女人。我也很兴奋,迫不及待地往下读。然而作者却把时间拨快了,“日子飞快,青春的成长仿佛是一日间的事情。我上完高中,上了大学,那些不上学的同学好多已经结了婚,我假期回来的时候,见到他们领着自己漂亮或不漂亮的妻子一副幸福的样子。还有的怀里已经抱上孩子,小小的婴儿在爸爸怀里怎么看都像一个玩具。钟飞还在跑江湖,偶尔能见到他,他的脸上过早地写满了沧桑,仿佛时光从他身上硬硬抽去一截。”这个时候,作者笔下的江湖显然与我们想象当中的江湖相去甚远,或者说,从一开始,因为带着莫名其妙的错误期待,误以为作者会写出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故事,或者说是令人心碎的成年童话。然而不是。杨遥用短短几千字的篇幅重新描写了一个正统的江湖,辛酸的江湖,小人物的江湖。写小人物,并非杨遥的创举,古今中外,不乏其人,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莫泊桑。同样是写小人物常态的感情和淳朴的天性,但杨遥偏重于渲染其内心的骚动不安,或者说因为体验的不同,他赋予了小人物一个欲望过剩的时代背景。
有关钟飞跑庙会的具体细节,故事里面的“我”还随着钟飞转了一圈。这个“我”似乎是个文学青年,值得玩味,学历应该是大学本科,同情钟飞,又好打抱不平。一个例证是,“我”因生计逼迫,想起了鲁迅的《在酒楼上》。这个细节出现在小说里,无疑具有某种隆重和向经典致意的况味。人们在小说中感叹现实,而后人又用它来感慨,温暖自己。但凡文学青年,大概都有一种江湖纠结,这可能跟其苍白羸弱的体质有关。在跟随钟飞赶庙会的时候,两个人还谈了很多话,大部分都是围绕旁边跳脱衣舞的姑娘。那个时候我还在以鄙陋浅薄的心理妄加揣度,钟飞和“我”那么津津有味地看着她们,肯定只是因为性的匮乏。除了性还能有什么引起两个大男人的关注?之前一再交待两个人都没有结婚,都找不下合适的女人,这不终于说到关键点上了吗?然而,不全是。钟飞的一席话令人大吃一惊,在谈到脱衣舞女为什么不跑时,他说:
“‘谁跑得了?平时不允许出去,一旦上街,就有人跟着。再说,她们没有身份证,没有钱,跑出来好人们谁敢收留这些不明不白的女人?还不是跑出狼群又落入虎口。”
“‘不瞒你说,我已经跟这个班到过好多地方了。也向相关部门举报过,可他们只是被赶走或被罚几个款,根本没人认真查。”
至此,钟飞显然具有了不凡的品性。他的一本正经,令人讶异,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大义凛然。他自己虽然是个弱者,但到最后却火烧脱衣舞女的场子,目的只是希望把事情搞大,能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这大概是钟飞作为江湖中人干的大事之一。
作为一个短篇,《江湖谣》承载的东西足够多,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也不少。也许作者的目的就是想为真正的江湖正名吧,我们见惯了想象当中的江湖,习惯了大人物的呼风唤雨,而他,杨遥,却以近乎笨拙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即便是跑江湖的人当中也存在着小人物,他们的生活也有血有肉,同样值得关注。
事实上,我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想象理解我心中的江湖。我生活在南方,也见过同龄人混江湖的事,那些劣迹斑斑的青年,大多家境一般,但至少也说得上衣食无忧,而且长相不俗,身边不乏早熟的女人和马仔。他们游手好闲,寻花问柳,逞勇斗狠,拉帮结派,讲究江湖义气,为人处事相当聪明,然而,缺乏的就是一种对人对物的理解和同情。或者说,他们的心胸远没有博大到对无关痛痒的人也会满怀感情。而在杨遥的这篇《江湖谣》里,起初,他用放任自流的鼻血逗引着人的好奇心,尽情为钟飞这个小混混的出场煽风点火。我以为钟飞会跟我想象的那些孩子一样,必将掀起一番风雨,可是等到多年后,这个眯眼、一事无成、卖圈套的常客干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暗中火烧歌舞场。这不免要让人怀疑作者是在故作夸张故弄玄虚,我们怀了多少期待,可最终却如其在小说中表述的那样:“夏天的午后异常漫长,我没有想到钟飞做的活儿是这样无趣。”不光是钟飞做的活儿如此,钟飞这个本来似乎很有意味的人,至此也成了一个困苦的同情对象。跑江湖多年,却没有找到一个能过日子的女人。家境衰败,事业(如果可以用这么一个庞大而空洞的词来形容的话)不如意,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他仍然
同情比他活得更辛苦的人。这就是钟飞,他的眯眼最后在“我”看来,仿佛也具有了独眼大侠的伟岸形象。
在创作谈中,杨遥就表露了他之所以要写这样一些人物的看法,他认为小说就是要尽可能展现迷人的可能性,最要紧的是人物的命运,是灵魂,而灵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在常常被漠视的卑微人物身上闪闪发光;无一例外,他笔下的主人公很少有大奸大恶之徒,然而这些被习以为常的世间百态在他的笔下得到放大,凸显,那些被忽略的情感部分重又得到擦拭,变得光芒四射。在一个人人只关心自我道德虚无的时代,杨遥祭起自己的大旗,初看未免寒碜,甚至不无套话连篇的嫌疑,但,等到真正静下心来,才发现,他的这种近乎笨拙的努力,他的单纯的期望,无疑是美的是好的是善的;他试图唤醒,企图把一些正在被丢失掉的东西重新推到世人的面前,让我们铭记。
然而,杨遥的风格并非固定在一个枝头,从他发表的六十多个中短篇就能看出力求改变自己的努力,部分短篇称得上富丽堂皇,而最重要的是,他使我们诧异,他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就像真的在开一个天大的玩笑,这次他在《广场上的狐狸精》里就给男人提出了一个难题:把一个绝色美女放在广场上。正如作者所坦言的那样,写的是男人的欲望。男人的欲望千千万万,他写的就是男人的好色。这类似于一个梦想,或者说,他嘲弄了那些对于美色当前的男人畏畏缩缩止步不前的尴尬模样。这倒不是说他鼓励人们尽情占有,而是在一个绝色美女横陈在广场上“谁愿意要我,带我回家”的时候,人们却只晓得围观,无人勇于下手。可以想见,他刻画的仍然是看客,只不过这次是一群。富有反讽意味的是,只有等到凌晨,等得众人眼光迷离,这一切却被一个推着平板车的老头儿匆忙中卷走了。当然,作者把这个结局给含混化了。也许事情并不是这样。比方说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那个绝色美女是个残疾人,她只不过是想逃离老头儿的掌心。
我不知道男人的欲望是不是都是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杨遥只是通过虚构的手段夸大某些部分,让人看到人性最为黑暗的一面。他就是要以这样一种蓄谋已久的夸张,把男人瞪圆的眼睛浮肿的面容呈露给世人看,逼近众生。问题是,他描写的是男人的欲望吗?在我的理解当中,身为男人,他就具有了霸气、正直、勇武有力之类的美好性格,比如女人的希望,“你还像不像男人啊?”就足以证明。我想,杨遥写的无非是一群好色之徒的欲望。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群小人物的看客心理。他在一个无所事事的黄昏,把一种暧昧和混乱的道德选择扔在众人面前,无论怎样,似乎都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