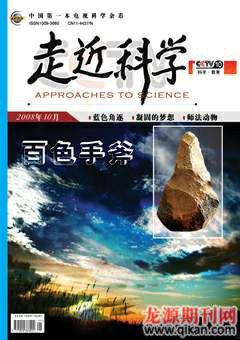青春无悔
重 访
1938年的一天清晨,日军兵临武汉,惊恐万分的人们拖家带口涌出城外向南方逃去。与众不同的是,一个10岁的男孩却被一个高大的男人带领着逆人流北上。
这个小男孩名叫陈祖涛,带他离家的男人是他的亲叔叔陈俊(图1)。

(1)回忆青春往事,陈祖涛淡定从容,无悔无怨
由于日军已经占领郑州黄河大桥,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放弃了乘坐火车,改坐最原始的牛车,一路风餐露宿、艰难跋涉,终于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此时陈祖涛才知道,叔叔之所以历经艰辛把他带到延安,是为了去见他的父亲——陈昌浩。
对于小祖涛来说,父亲陈昌浩完全是一个陌生人。陈祖涛出生前夕,陈昌浩远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工作,始终没有时间回武汉的家中探望,一直跟随母亲长大的小祖涛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直到1937年,陈昌浩才有机会回家,但只待了3天。这次延安之行才让这对父子重逢。
陈祖涛(陈昌浩之子):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后来去延安见父亲,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到延安以后,陈祖涛面对陌生的父亲有些无所适从。不过他在延安保育学校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并且认识了新的小伙伴。
陈祖涛:我在那里认识了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彭德怀的侄儿,还有好多干部子弟。
在这些小伙伴中,陈祖涛和刘允斌、刘爱琴兄妹非常要好。3个孩子每天形影不离,延河岸边、黄土高坡到处都留下他们欢乐的笑声。然而这样快乐的日子只过了一年,1939年7月的一天,陈祖涛突然发现朝夕相伴的好伙伴不见了踪影。
陈祖涛:当时很吃惊,我找刘少奇伯伯问过,才知道刘允斌,刘爱琴到苏联去了。他们怎么不带我去?
事有凑巧,就在刘允斌,刘爱琴离开延安后没有几天,周恩来因坠马受伤,要到苏联治疗。8月,一个炎热的傍晚,父亲陈昌浩告诉陈祖涛,准备带他随同周恩来一起坐飞机去苏联。这个消息让陈祖涛兴奋不已。
陈祖涛:离开延安的前一天,父亲跟我说,明天有大飞机就带你去苏联,如果小飞机坐不下,以后再去。第二天来的是一个大飞机,当然高兴了。
就这样,小祖涛坐上飞机飞往心中的天堂。
到了苏联,陈祖涛见到了刘允斌、刘爱琴,还有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虎、高岗的儿子高毅,5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被送进了距离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陈祖涛在这里度过了他难忘的青春岁月。
陈祖涛:当时我还碰到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瞿秋白的女儿独伊,蔡和森的女儿蔡转。
通过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保存的影像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当年的幸福生活。
陈祖涛:儿童院有音乐组,蔡转喜欢音乐。我参加木匠组,用刨子、凿子打制板凳,学习木匠活。
蔡转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的女儿,蔡和森牺牲后,党中央送她来到苏联。
蔡转:我一到苏联,就对钢琴很感兴趣,就自己去摸,会弹一点。当时听到的都是那时候苏联流行的歌曲,以后就组织我们学习音乐(图2)。

(2)蔡转(左)在文艺演出中弹琴
蔡转在儿童院学会弹奏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后来在中国广泛传唱的《喀秋莎》,这首歌曲给蔡转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可是没过多久,流行的音符突然改变了。
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战争使这首歌变成了现实。
陈祖涛:上面把我们撤退,每个小孩一个小背包,里面装了生活必需品。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儿童院一下子失去了强大支持,被转到苏联红十字会管理。苏联红十字会竭尽所能,也难以给儿童院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这使原本不愁吃穿的孩子们一下子要面对生存的考验。
陈祖涛:老师提出一个口号:自救。我们自己种土豆,我是吃土豆长大的。
生活条件的急转直下,让孩子们不得不想办法度过难关。
蔡转:陈祖涛是我们的班长,那时候每个班都有一块园地,种包菜、胡萝卜。他很能干,带领我们班种的菜最好。一种菜,食堂就有菜吃了。
这种近乎残酷的生存考验一直持续到1945年。这年5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同样在5月,17岁的陈祖涛读完了十年级的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苏联工科类院校的最高学府——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图3)。

(3)陈祖涛和苏联同学在一起
陈祖涛: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属于半军半民性质,有坦克系、仪器系、大炮系,我考取了机械系,是民用的。那所学校很严格,不收外国人,就是苏联的少数民族也不收。但我凭着好成绩考上了。
蔡转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音乐,报考了莫斯科斯大林第二国立医学院。
蔡转:我觉得祖国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我选择了学医,治病救人。
1947年,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许多中国孩子考上大学,大家四处分散,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为联络感情,“苏联中国留学生会”在莫斯科成立了。自小就是孩子头的陈祖涛和刘允斌以及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一同被选为负责人。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苏联中国留学生会”成为中国留苏学生了解国内局势、交流互助的重要组织。
由于战争刚刚结束,苏联国内的物资十分匮乏。上了大学的中国孩子们只能靠学校提供的少量奖学金生活。
陈祖涛:一年级的时候,我一个月的奖学金是370卢布,五年级才达到400多卢布。当时集市贸易土豆价格是1公斤75卢布,也就是说,一年级时1个月的奖学金只够买2公斤多一点的土豆。
1947年,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蔡畅,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时路过莫斯科,看到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状况,心酸不已。她第二年再次路过莫斯科时又去看望这些留学生。这次,蔡畅有备而来。
陈祖涛:她给我们带来一批金首饰和金条。
但是,如何把这些金子变成卢布,却成了头疼的问题。当时二战刚刚结束,苏联政府对金融控制非常严格,要么去国家指定的机构兑换,要么去黑市兑换。大家商量决定,这件事由陈祖涛负责。
陈祖涛:当时我们有一条很清楚:不能上黑市去换钱,被抓到以后要蹲监狱的。但到官方机构,比如银行去换,很便宜。所以就找一种相当于当铺的商店,我就带着第一批金子去换卢布。
陈祖涛把第一次兑换来的卢布分给大家,大家很快就花光了,陈祖涛只得再次去换。
?陈祖涛:大概过了一个月,我第二次去了,便衣警察马上把我抓起来了。一个外国留学生有这么多金子,肯定有问题。把我抓到莫斯科民警总部,审问我哪里来的金子?
陈祖涛说出了事情的原委,警察核实情况后放了他。用金子换来的有限卢布要支撑这么一个大家庭总是显得捉襟见肘。但这些乐观的年轻人却从嘴里省下一部分钱,买了一件和温饱没有关系的奢侈品。
蔡转:我们的手风琴就是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买的。大家聚在一起实在想唱歌,也没有一件乐器伴奏,陈祖涛和黄健他们就在好像跳蚤市场那样的地方,买了一个旧的手风琴回来。大家特别高兴啊,聚起来就有音乐了。
1951年2月,陈祖涛以优异的成绩从苏联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提前毕业。23岁的他在离开祖国12年后第一次回到了北京。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陈祖涛和一同回国的赵施格在新中国进行了2个月的游历,看到了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
1951年正是国民经济恢复的关键一年,陈祖涛报效祖国的热情日益高涨。在北京,他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一次重要谈话。
陈祖涛:周总理接见我们,他说,你们在全国都看了,你们现在想做什么工作?赵施格说他学冶金的,想搞冶金工程。周总理说,好。鞍钢正在恢复,你到鞍钢去吧。我说我学机械的,在汽车厂实习过,对汽车感兴趣。周总理说,好,你到苏联去。我国正在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你作为一汽代表去苏联,一方面实习,一方面参加全过程设计。
就这样,陈祖涛成为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名汽车工业实习生(图4)。

(4)陈祖涛(中)在苏联汽车制造厂实习
1951年9月,陈祖涛再次来到莫斯科。同年12月,苏联援建中国一汽的初步设计资料全部完成。陈祖涛带着这批珍贵的设计资料再次返回北京,并且翻译完毕。这些设计图纸和资料成为一汽建设最原始的材料。
1953年,陈祖涛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两件喜事,在莫斯科,他与美丽的俄文翻译赵淳媛相识相知,携手人生;在长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
1956年7月15日,新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下线(图5)。

(5)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下线
第一辆汽车下线使一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然而庆功仪式上,却没有出现陈祖涛的身影。此时,他正远在东德为汽车厂的材料设备而奔波。材料解决后,陈祖涛又主持设计并组建“红旗”轿车、军用越野车两个生产基地。
由于在一汽建设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具有突出的专业技能,在中央提出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的设想后,陈祖涛成为二汽建设5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可是,正当陈祖涛在湖北十堰的建设工地拼命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封来自一汽的电报使他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陈祖涛:一汽的造反派要我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老同志怕我有什么意外,都劝我不要回去。我说,我是小八路,红小鬼出身,历史没有任何问题,我怕什么?就走了。
陈祖涛过于简单的想法,使他一脚迈进了命运的深渊。“造反派”给他扣上所谓的“苏修特务”的帽子,却又拿不出证据,于是将他押送到吉林桦甸县劳动改造(图6)。

(6)面对磨难,陈祖涛夫妇依然乐观
陈祖涛:生活很艰苦,我和我爱人、我9岁的孩子和我的岳母,一家4口挤住在一间快要垮塌的草房子里。农民很通情达理,他们见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就说,你别下地,冬天下地冷得很呀!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木匠。我想起我小时候在苏联学过木匠活。他们说,你就当木匠吧。我就拜屯里的一个老木匠为师,买了一套工具,每天背着一个工具箱,跟师傅一起盖房子,打板凳。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1967年,有生以来未曾见过几面的父亲因为不堪煎熬离开了人世。父亲的怅然离去,成为陈祖涛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
陈祖涛:父亲死时才61岁。他统帅10万大军时,28岁,红军时期他的职务很高,最后因为西路军失败,他承担责任。后来在苏联待了13年,回国后就什么职务也没有了(图7)。

(7)陈祖涛与父亲的最后一张合影
1972年,机械部和二汽派出的工作组找到了他,请他重回二汽工作。对于组织上的安排,陈祖涛并不情愿,但为了能见到母亲,他答应先回武汉看一看。
没想到,刚刚回到武汉,街上的一幕景象深深地刺伤了陈祖涛。
陈祖涛: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了一辆二汽生产的越野车,开都开不动。我们二汽怎么出这么蹩脚的车子!我一看就有股气,我得回二汽!得回到汽车行业。从此以后我就在二汽卖命地干活。
陈祖涛重新回到二汽,苦干拼命干。有一天,正在车间里检查工作的陈祖涛突然昏倒了。
陈祖涛:由于疲劳过度,“文化大革命”留给我的后遗症复发了。我的手脚不能动了,话不能讲了。
同事们急忙把陈祖涛送到医疗条件较好的武汉市同济医院。没想到,同济医院接收他的医生竟然是他多年没见面的儿时伙伴。
蔡转:突然见到他了,可是他变成了这样一个人,让人很伤心。之前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文化大革命”中找不到他。结果一见面呢,他是作为一个病人来的。我当面没有哭,背后哭了,他病得这么重。
同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国的蔡转,这时候已经是神经科方面的专家。与老同学20年后的再次见面令蔡转十分伤心,她无法相信眼前这个病人就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班长。她与同样从事神经科研究的丈夫刘希民一起,对陈祖涛进行治疗。
蔡转:刘希民是我们科的主任,也是我的丈夫。神经系统的疾病有很多是可以复发的,亏得对陈祖涛治疗还是很有效。
脑神经疾病当时在国内没有先例,经过蔡转夫妇一年多的精心治疗,陈祖涛奇迹般地痊愈了。
1976年,历经磨难的陈祖涛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从事他热爱的汽车事业(图8)。

(8)陈祖涛为他挚爱的汽车工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今天,已是耄耋之年的陈祖涛老人,还常常回忆起1938年的那个上午:陕北,阳光灿烂。一辆军用卡车正颠簸着在黄土地上行进。车上那个10岁的小男孩东摸摸西看看,对这个有着大轮子、跑得飞快的铁家伙充满了好奇,这是他第一次坐上汽车。这辆车把他带到了父亲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