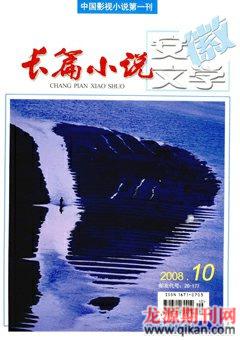马尾草
梁颖苗
那天午后,天好干净,澄明的碧蓝,映着被太阳晒暖的心情。屋后是一片茫茫的马尾草,毛茸茸的、黄澄澄的一片,在准西斜的泛韵红的阳光中,不断地摇曳、点头、微笑、招手,一波又一波,像海浪。浮在天上的白云一片一片地从草的上空飘过,唯落下一块又一块影子于草野之上。云影与草丛重叠在一块,引诱着我。
我就在后门傻傻地看着他们。想想那一片白茫茫的凹凸中,人的生命是否像沧海中落水的蚂蚁一样,又像茫茫白雪中的一个黑点,虽依然灵动,但在一片无边无际白色中,一个小小的黑点往往却是最脆弱的,随时会被埋没、覆盖、吞噬。当一个人踏在这片冰天雪地的疆域上时,我想,一个人的肉体绝不是最重要的了,像是他脚底下辗碎的千年冰块一样,哗啦哗啦地流过,惊醒了沉睡万千年的冰原,留下了被雪漂白过的灵魂。生前,我们的心灵是美丽的,那么死后我们的灵魂也是洁白的,像西藏的雪。母亲在屋前帮我洗那件蓝色的小背心,水龙头开得哗哗地响。一群大孩子在屋后的草地上找蟋蟀,母亲不让我跟着他们去,她说她怕失去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但我还是偷偷地出门了。
我喜欢一些原始朴素的事物:野草、蟋蟀、泥土。踏在软软的马尾草丛中,我兴奋到一个无法阻达的程度,不停地用手抚摸这些和我一样高的野草,软绵绵的,酥麻麻的。拽一根下来,放入嘴里吸吮着,甜甜的草味,我不断地欢跳。在我眼中,它们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灵动、美丽、飘渺、飞翔。就是这种来自于手心的绵绵麻麻的对马尾草的感触,诱惑着我离开了那群大孩子。草的那边尽头是一条河,河沿很深,也许因为河沿的缘故,旁边的马尾草长得特高特招摇,晃头晃脑的,不断冲我招手,微笑,又似在挑逗我,赌我不敢过去,我还是抵挡不住来自手心的诱惑,潜下身子伸手了过去。
生命有时会凝固、流走,或激情,或消沉,或孤单,或混杂,或离去,或重生。我不知道,我不断地挣扎,我不断地呐喊,先是拼命,慢慢无力,最后是等待。我不知道一向温柔的河水为何变得如此冰冷凶残,我的一切言语被它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水泡泡,它们慢慢上升、上升、上升,浮出水面,透过这层像刀一样锋利冰寒的水面,我看见外面的阳光是多么的温暖,我在期待,期待意象的出现,希望的重生。冥冥之间一只大手从某个地方伸了过来,紧紧地抱住我,之后便是摆脱。
母亲说,上帝有时候也会打盹的,关照不了每一个生灵。我相信了,生命像性格变化无常的河水一样,随时会流走,奔放,也会凝固。母亲告诉我,那天,一个美丽的心灵拯救了我的生命,他是一个山村的村民。那天花红,草绿,天气格外的好,他从水里托起一个水淋淋的孩子上岸时,自己又栽进水中,人们都说见到他的时候,他很好笑,像浮在水面上的蚂蚁,皮肤白得眩眼,毛茸茸的毛发载在水中飘着,全身浮肿,上衣撕破了,皙白的上身露出两个肿肿的乳头。母亲说,我们的生命已永远不再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那颗美丽的心灵。
那村民的山村我到过,那是一九九三年的一个冬天,整整一个冬天,我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朴质、勤劳、善良、热情的村民,贫瘠、落后、封闭、野蛮的大山土地,一切的一切都构成了我童年凄美回忆的主调。一个倾角60度以上的山坡上,一位老农在犁地,人瘦骨嶙峋,牛也瘦骨嶙峋,用的居然还是我们在老电影里面才看得到的木犁。他们没有打谷机,他们是在一个大木箱里面用双手来敲落稻穗的,他们没有碾米机,他们是挑到三十里以外的河边用水力推动石磨来碾的,他们没有电灯,没有自行车,连通自行车的路都没有!寒冷的深处等待的是寂寞和霜雪,北风呼啸,落叶飘零,悄悄地,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切都在死一样的静寂中惆怅,哀悼,祷告,或离开。也许山寨吊角楼上的火炉、热瓦甫、油茶及依偎在火炉旁的人是唯一的温暖、安慰和幸福的所在吧…孩子的眼睛是两盏柔弱的灯,飘忽不定迷离无知,见是生人,咚咚咚,冻得发紫的光小脚丫子连忙跑到妈妈的身后,探出通红的小脸蛋,眼睛里的超然、安详、或忧伤……不知他们知不知道在山和雾的外面,有着一帮和他们同龄的孩子这时候还沐浴在隔着玻璃的暖气中,在由那一串串数字虚构成的梦幻魔兽世界里游弋呢!他们,一些单纯而微弱的存在,一段沉默,一声长叹,在梦样的岁月里流逝…
在路上,我会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么一些孩子,他们赤着脚,下身勒着一条松松皱皱破破脏脏的裤子,裸露着脊梁,头发像草一样荒芜,嘴里叨着烟,装一副老成的样子和旁边大人攀谈,成熟地吐着烟圈。他们都是我大山里跑出来又无家可归的孩子。在那个山村里,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妇女和几个中年男子的死去,没有隆重的葬礼,他们的生命就像一群蚂蚁一样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地来,忙忙碌碌、麻麻木木地活着,最后又像被大水淹死的蚂蚁一样乱七八糟、糊糊涂涂、横七竖八地死去,我心爱的人们啊,为何上天赋予你们美丽心灵的同时又赋予你们如此悲惨的命运呢?死人僵硬的手还想再拉一拉他们亲人的手,不瞑目的眼依旧想看看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寨子。他们也有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他们也有自己的神,但为什么他们天天都在祭拜的神连他们吃一口肉,拉一根电线的愿望都不帮他们实现呢?他们不知道神只是一种信仰,一种虔诚,一种善良,永远也不会是物质现实。而正是这一群人,在我们居住的数个月里,一天又一天,一家接一家地给我们送菜,绿绿油油的菜,枯枯瘦瘦的手;正是这一群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在我们要离开山村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拿出家里一年才可以吃上那么几餐的酸鱼酸鸭全塞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却搁在一旁,孩子们嘴角的蠕动,眼睛里流淌的渴望让我心痛,心痛直到今天还将会延续下去,这是一种滞重的痛,十几年的沉淀让我疲惫不堪。物质生活。一种社会的病态,病根早在许多年前已经埋下。我走的时候和那群孩子年纪相当,也许他们现在早已辍学,结婚,做父亲了吧?
虚无、空洞,填满了我周遭的空间。我害怕极了,从来没有过的害怕,我不知道十三年后的这个冬日我一个人还能不能撑下去,缺少了大山里特有的温存和温暖,暗夜里的孤独和寒冷趁虚而入,刺骨,透心。脆弱的躯体感染了同样虚弱的心灵,开始解析、分裂、漫延、变形、增殖、扩散、离异、分化、消亡。其实,我还是清醒的,但我一个人清醒有什么用?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一根蜡烛,我会毫无保留地燃烧自己,释放自己,为的是照亮那些心里还没拉上电线的人,更为的是在自己心中点亮一盏灯,找回归路,找到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温暖,自由、安然、宽心的感觉,这是我的归宿。
十一月的今天,我二十了。蓦然发现,二十年里,我一直是一个孤独的流浪者,走在路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影子在太阳下拉长,缩短,又拉长。秋风萧萧,繁花落尽。真想如果有来生,愿变成一根在黄昏中通向远方的电线,与山村的美丽心灵的另一根永不相交,却永远平行。又愿变成一棵树和美丽心灵的人们的那一颗默默地生,默默地长,默默地站成万千年的沧桑。昨天,去郊外摘了一些马尾草回来,插在花瓶中,怀念我那已逝去的少年时光。
责任编辑 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