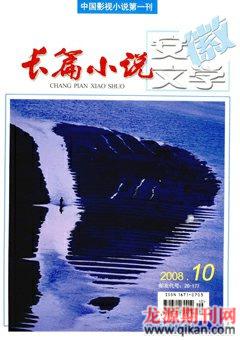继母
范光春
我的脚终于踩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站在散发着新鲜泥土气息的坟前,我脑子空白一片,继母的坟孤零零地躺卧在群山的怀抱之中,除了树木。荆棘,杂草,竟没有一个陪伴。晚风习习地吹着,不时有残枝败叶落地的声响传入耳膜。夜幕中突然传来几声鸟儿的哀叫,使清幽静穆的大山凭空增添了几分凄凉和冷漠。
没有月亮的夜晚,耳边除了呼呼的风声,四周静寂得有些可怕,或许正是这种因素感染了我,使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一滴泪悄悄溢出眼眶,接着又是一滴,又是一滴,溢出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滴,滴到嘴边,又一点一点的渗进嘴里。
淡淡的咸中略有些酸涩,恰如我此时此刻难以名状的心境。
继母是在我母亲逝世的第二年初秋来到我家的,那时我刚年满六周岁。
说起母亲,我就难免想起母亲的死。
那是1993年仲夏的一个夜晚,熟睡中的我突然被母亲的呻吟惊醒,我翻身坐起,摸索着爬到母亲身边。母亲挥舞的手一把抓住了我,她一边喘气一边断断续续的说,“娃,娃,快……快……”
我不知母亲要说什么,只感觉她抓住我的那只手在颤抖,我哭喊着:“妈——妈——你怎么了?”我凄婉哀楚的哭声在寂寥的夜空漂浮着,显得无比的悲凉与凄惶。
没有一个人回应我的哭喊,除了老鼠偷食的簌簌声以外,就是母亲的呻吟和喘息。我乘母亲松开我手的那一刹那,我跳下床拉开灯,跑进厨房为母亲端来一碗凉水。
当我把凉水端到母亲面前时,母亲的面容却吓得我惊惧的叫了起来。
我歇斯里底的叫声终于惊扰了临近一家人的好梦。当他们夫妇二人赶来时,也被母亲的模样吓得不知所措。于是女的又回去叫来了几个邻居。
母亲的瞳孔瞪得很大,嘴微微张着,左手紧紧地攥着床沿,右手把心口的内衣紧紧地揪成一团,双脚一伸一屈,好像生前曾经受过巨痛的折磨。
“看这模样是急病突然发着的症状。”双大叔一直以来都是村里公认的有见识的长者,他仔细端详了母亲的遗容后得出了这么个结论。
接下来双大叔让人去几十里外的镇上叫我父亲。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看见母亲的摸样当时便稀泥一样瘫软在地上。
母亲突然撇下我和父亲去了阴曹地府,走前来不及给我和父亲留下一句话,父亲感到异常的悲伤和沉痛,幼年的我常常看见父亲站在母亲的坟前喃喃自语,一说就是几个小时。这个情景直到继母出现才有所缓解。
继母的到来使死气沉沉的家有了生气,空气似乎也变得活跃起来。久违的笑容也挂在了父亲的脸上。
父亲重生了,然而我却依然笼罩在痛失母亲的阴影里不能自拔。我想,不管时间怎么流失,我都是我母亲邱月娥的儿子。因此,我从心眼里讨厌那个踏进我家取代母亲地位的女人——柳翠花。
于是我和继母之间,自然而然的就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凭心而论,继母待我不薄,甚至胜过己出,然而血浓于水,我心中只有我母亲,也惟有我的母亲才是母亲。
继母到我家后,并没有过几天安生日子,生活和我常让她喘不过气来。
1996年夏天过后,父亲把年满七岁的我送到就近的村小上学。从我家去学校,少说也有八九里路程,自从继母到家后,父亲又重抄旧业。家里的诸多杂活包括接送我上下学,都一概落在了继母的肩上。
父亲不在时,我对继母是敬而远之,她做什么我吃什么,她说什么,我左耳进右耳出,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历来是我行我素,不管什么时候,都一副我做什么与你无关的摸样。
登门告状的人像初潮的春水一样源源不断的向家门涌来,继母总是满脸微笑着给这个赔礼,向那个道歉,这个时候,我就躲得远远的嘻嘻偷笑。
笑够了,玩够了,我才提着书包回家,继母看见我回来了,忙放下手中的活计,笑嘻嘻地问:“娃,回来啦,今天过得开心吗?”我二话不说,把书包往她手里一塞,面无表情的说:“不开心。”心里却沸水一样嘀咕开了:你装的没事人一样啊?你就装吧,如果你敢向我父亲告我的状看我今后怎么收拾你!
父亲回家的日子是没有固定的,三五几天或者十天也说不准。反正他要把手里的活忙完告一段落才能抽空回家。
父亲回家,是这个家空气最为活跃的时候。荤菜素菜摆了满满一桌子。我低着头大口大口吃菜,这夹还没咽下那夹又来了,嘴塞得满满的不能正常咀嚼,两个腮帮子胀胀鼓鼓的像两个乒乓球。父亲见了,就搁下筷子骂:“看你那穷样,就像几辈子没吃过饭似的。你慢点吃不行吗?又没人和你抢!”父亲一骂,我就赶紧把包在嘴里的菜饭使劲往下咽,噎得我连连打嗝,继母就忙放了碗过来给我捶背。
继母说:“吃饭,别吵孩子,噎着咋办?”
我冲继母扮个怪相,继母“扑哧”一笑,嘴里的饭菜就喷到了桌上。
我从厨房盛来一大碗饭,把桌上杂七杂八的菜一个劲儿地往碗里夹,父亲见了,一瞪眼,伸手欲抢我的碗,被继母档了回去。我也看父亲一眼,就低了头慢慢吃饭。
这时父亲已经吃完饭坐到一边喝茶去了,我猛扒了几口饭在嘴里,又突然吐了出来,然后把碗往继母面前一推,说:“我吃不下去了,你帮我吃了。”
父亲听见了,走过来对准我的脸就是一巴掌。
“鬼娃子,你吃不下了还舀这么多干啥?下顿热了再吃,谁也不是你喂的狗。“
父亲说完,把饭碗重重的往我面前一推。
我又把饭碗往继母面前一推:“不吃,不吃。我就要你帮我吃。” 我捂着被打的半边脸,仍旧不依不饶地喊着。
继母挡住父亲伸过来的手,依然笑嘻嘻地说:“就让我帮孩子吃了吧,孩子的东西,有啥脏的呢?“
“那就把上面的那一层倒掉,吃下面的。”父亲说。
“不能倒,不能倒。全吃,全吃!”我拍着手叫起来,最后还特意补上一句,“不然,我以后不叫你妈。”
这一招果然灵,父亲不哼声了。继母就端着我吃过的饭,大口大口的吃起来。边吃边说:“只要咱娃高兴,吃啥都行。”
每当此时,我就得意的冲父亲笑笑,然后把两手插进裤兜,嘴里吹着口哨,摇头晃脑的往门外走去。
在我心中,继母不管对我再好,她不过是父亲的女人,现在是,永远都是。
继母初到我家来时,曾有人说继母是不会下蛋的鸡,哪想在我快满十岁时,继母的肚子却大了起来。
一年以后,继母给我生了个乖巧玲珑的小妹妹。
大婶说:“有了自己的孩子,待人家的还会像当初一样好吗?”
大伯说:“强娃子这下可要遭罪了。”
我不知这些风言风语不知是否传到了继母的耳朵里,可她对我的态度却一点也没改变。
在父亲看来,她似乎比以前更疼我了,我却不以为然。相反,每每看见她抱着妹妹的脸蛋亲了又亲,满脸还洋溢着温情的笑容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还是自己的孩子亲啊。”我嘀咕着,心里有一种又酸又涩的感觉,她原来对我的好都是为了做给父亲看的。
人就是怪,心里一旦失去平衡,就会无端生发出很多事情来。
那一天,我突然捂着肚子大叫起来,假装肚子疼。继母见我在床上乱滚的样子,急忙松开了牵着妹子的手。
继母轻轻地给我揉着肚子,妹子趴在床沿,奶声奶气地叫着:“哥,哥,你疼吗?”
“我疼有什么要紧啊,只要你不疼就没事的呀。我的亲娘啊——如果你在,你会让儿子疼大半天不问不管吗?”
“孩子,孩子,你骂吧,想怎样骂就怎样骂,是我没照看好你。”继母哽咽着说。
“我不要你打火罐,不要你打火罐。我要找我爸去。”看见继母为我找火罐去了,我跳下床就往外飞跑。
夜色降临了。到处黑压压的一片。我躲在村外的玉米地里。继母的呼喊从不远的地方传了过来:“强娃——回家来,强娃——”
我坐在玉米地里一动不动,任凭那声音响起落下,落下响起。月亮高悬空中时,呼喊声终于消失在水银般的月光里。
我想这一夜,继母一定彻夜难眠。
我躺在玉米地里,随手掰下一根玉米杆,放在嘴里无聊地咀嚼着,一股散发着鲜草清香的甘甜就慢慢渗进了嘴里,使我周身都甜润清爽起来。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钻进了云层,四周漆黑一片。乌云小山一样在我头顶滚滚涌动,风刮起来了,不猛,却冷飕飕的,我抵不过寒冷的侵袭,爬起来便向村里跑去。
我贼一样潜回家,把耳朵贴在继母的门缝上。屋里的一切声响便非常清晰的进入我的耳朵。
继母在啜泣。
我幸灾乐祸地溜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
早晨起来时,看见继母一脸疲惫地从外面回来,乍见到我,不觉吃了一惊,旋即脸上露出了笑容。
“原来娃在家啊?这就好,这就好……”
继母进卧室去了,我以为她一定补瞌睡去了,无聊地向地上啐了一口痰:“真没劲!”
我咕哝着,抬起脚对着门槛狠狠地踹了几下。
我懊恼地躺在床上,一脸的沮丧。全没有了刚进屋时的那种快意。
“强娃,强娃,起来吃饭了。”朦胧中,我听见有人呼喊。睁眼一看,是继母。
继母笑嘻嘻地站在床前,手里端着一碗荷包蛋。接过继母手里的碗,我突然有了一种歉疚感。心里想以后对继母好一些吧。
可是这个念头我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给打破了。
第二天下午放学回家,我正和继母、妹子吃饭,一个拄着拐杖的独腿男人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来人,继母显得很慌乱,她手足无措地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
我听见继母语无伦次的对那男人说:“你……你……怎么来了?你还活着?”
比起继母的慌张来,那男人倒是很平静。他放下拐杖,在凳子上坐下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不该来?你是我老婆。我还活着让你很吃惊是吧?”
听到这里,我呼的一下冲到断腿男人面前,大声喊着:“你给我出去,这里没你的老婆!”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继母打了个哆嗦。
“小子,别给我嘴硬。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叫柳翠花,是我王富来的老婆。”
“你胡说,你胡说。她是我爸的老婆。”我一点也不示弱。
“小子,别多嘴,让她自己说是不是我王富来的老婆?”男人用拐杖狠狠地顶着我的胸口。
男人的话刚一出口,我便听见继母伤心地哭了起来。
小妹也助阵似的号啕起来。我赶紧拉着妹子进了卧室。
身后,听见那男人在说:“哟,看不出,挪了窝,还真下蛋了。”
夜幕降临了,那男人还赖着不走。非要继母跟他回石子坳不可。于是,继母进屋来安慰了我和妹子几句,就随那男人回石子坳去了。
继母走后的第二天中午,父亲回家来了。他在家呆了三天,直到继母从石子坳回来。
继母从石子坳回来的第四天,又去了石子坳一次。听父亲说,继母是回去和王富来办离婚手续的。
她有男人,为什么跑到我家来?我心里老大一个疑问。然而这个疑问又不便与父亲说起,但我很想知道着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偷听了村里大婶大伯的谈话,我才知道了原委。
说起来,继母的命真的很苦。
她二十岁那一年,为了给大哥换亲,父母便把她从椿树集嫁到了石子坳的王家。王富来一表人才,但品性却不怎么好,仗着自己长着一副白嫩嫩的脸蛋,四处勾搭女人,柳翠花看在眼里,却敢怒不敢言。结婚两年,因从未怀上,婆婆不满,常指桑骂槐。不久,婆母去世了,王富来更没心思呆在家里,就随打工人流去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城市。一去三年杳无音讯。后来听人说,因贪色惹下大祸丢了性命。
柳翠花听了,既无悲哀也无喜,就一个人过起了日子。婆母死后的第三年,经邻村胡婆婆撮合,就提着随身衣物住到我家来了。
没曾想,王富来命大,阎王爷只要了他一条腿。
话又说回来,虽说阎王爷是要了他一条腿,却让王富来经受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而且不得不重新选择人生。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了石子坳。
大凡人都一个样,硬要在穷困潦倒、失意落魄、走投无路时,才会想起某个人的好处来。理性者如此,感性者更是如此。
王富来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柳翠花已经再嫁,不仅生了个可爱的女儿,而且对父亲的感情还那么深。
柳翠花对父亲的深情平息了我对她的怨恨,我开始不把她看成是父亲的女人了。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她和王富来已经一刀两断,堂堂正正地是我父亲的老婆了,可是为什么却和王富来藕断丝连,三五天或者一个礼拜,她就要回一次石子坳,明里说是帮王富来料理打点家务,暗中却和王富来做和父亲常做的那种事,以至于妹子掉在河里淹死了她当时都不知道。
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原谅她的地方。
家里没了妹子,那个家就更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接下来,我读高中,上大学。学校离家越来越远,我的心也离家越来越远。虽然,父亲常念叨我,要我抽空回家看看,却被我以学习忙为借口推掉了。
而我也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父亲,但一想起妹子的惨死,一想起继母和那个断腿男人有染,我的心就忍不住一阵绞痛。尽管父亲体谅继母的苦衷,说她那样做是出于无奈是情不得已,可我永远不能原谅她,所以,大学期间,我一直没有回过一次家。
妹子一死,继母悲伤过度,身体大不如前,精神也恍惚起来,父亲终日陪伴在她左右,仍不能抹去她心中的阴影。和妹子在世时相比,继母像变了个人,寡言少语,抑郁呆滞。常产生幻觉,看见妹子和我向她走来。这种幻觉日复一日的折磨着她,使她无法承受这椎心泣血的心灵之痛,终于有一天,乘父亲不注意的时候,她从妹子掉进河的地方跳了下去。
父亲是在继母失踪后的几个小时让人到镇上打学校电话找到我的。
父亲说,继母病得很严重,希望我看在昔日她对我的种种好处上,尽早回家一趟。
我说,不回去!但是最后,父亲的那句“想想她昔日对你的种种好”触动了我,于是我向学校请了假,就急忙登上了返渝的列车。
没想还是迟了。
我只看见了衰老孤独老泪纵横的父亲。
我的心碎了。
我跪在继母的坟前,用手刨着地下坚硬的泥土,我想用这双让继母操碎了心的儿子的手,为继母的坟茔添一捧土,以慰继母的在天之灵,也慰自己的良心。
责任编辑黄艳秋